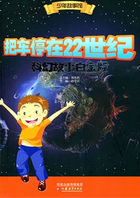觉得胸前它贴着我的地方有点发热,还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我把蝉托在手里,看着它一点点变得活灵活现——它的眼睛有了光亮,如两粒润泽的黑珍珠;翅膀的颜色在渐渐地变淡,变淡,直淡成了真正的蝉翼的灰白色。同时,也慢慢地薄了起来,有了透亮的、丝般的纹路,有了飞翔的资质与渴望。
我没想到梧桐巷也变成了一条商业街。
梧桐巷不长,非常逼仄,大人站在路中间两臂展开,差不多都能摸到两边房子的墙壁,而且巷子曲里八拐、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十分幽静。我喜欢梧桐巷是因为在巷子的尽头,真的有一棵梧桐树。树很大,也很老了,可能有一百多岁了。夏天的时候,在树下开辟出一大片浓浓的荫凉;秋天,会有小船一样的树叶飘下来,周围缀了一圈的梧桐子——前不久,我还带着边边在树下捡了好多梧桐子,这会,整条巷子全变了样。
一家家的民居都变成了店铺,门口挑着各色的旗幡,有的门口还支了个小摊,或是摆上个博物架,把店里的商品展示出来,路面就越发显得狭小,人多的时候,只能侧着身子走路。
这让我有点遗憾,我喜欢这条巷子原来的样子。
还好,走到巷子尽头的梧桐树下,终于清静了一些。树下的这家店是卖木雕的,看看里面顾客不多,我就走了进去。
墙上的木雕挂得琳琅满目,有风景的,也有人物的、动物的,还有一些小挂件。
一个男人坐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木块和细碎的刨木花间埋头刻着什么,店里三三两两的人来,看过后又三三两两地走,他也不招揽生意。
我看见那些小挂件中有一只蝉,和我的有点像,就拿来比较。
“你的在哪儿买的?”他终于抬起了头,问。
“不是买的,是我爸爸刻的。”我有点得意地说。
他走了过来,说:“我能看看吗?”
我把蝉拿下来,递给他。他仔细地看着。
他看蝉的时候,我在看他。
我第一眼就看见了他下颏的那个月牙形的疤,虽然他留了浓密的胡子,但那个疤并没有完全被遮住。不过他的睫毛好像没有记忆中的那么长那么密了,可能是脸更黑更饱满了的缘故。
我知道不能叫他“小大人”了,他现在是个留胡子的真正的大人。
而且,这个“大人”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一样,脸上也是不干净的,那个时候因为踩了我的“机关”摔倒在地上脸上沾了好多“沙吉”,现在则是木屑。
忍不住,我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他不解地望着我。
我指指他的脸,说:“木屑。”
他没去擦,只盯我看,眼神幽远、飘忽,若有所思……
然后,他也笑了起来,抬起胳膊蹭了蹭脸。他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角有了几条浅浅的纹。
“刻得不错。”他说,然后把蝉还给我。
我把蝉戴好,转身走了。
“沙吉。”走到门口,他叫了一声。
原来,他也认出了我。可我并没有太吃惊,好像这是很寻常的事,好像我们一直联系着而且昨天还刚刚见了面。
我回过头。
他摆了摆手说:“常来玩哦。”
可回家的路上,我越想又越觉得这事不寻常起来。
那么多年过去了——确切地说七年过去了,那么多人走了,可“小大人”来了,留了胡子,变成“大人”来了——现在应该叫他“大人”了。而且,偏偏就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城,偏偏就在梧桐树下开了家卖木雕的店,偏偏我就走了进去并认出了他,(当然,偏偏他也认出了我)——想到这里,我心里开始有点疙疙瘩瘩的。他最初见到我时我才六岁,现在我十三岁了,我的变化应该很大,最最重要的是,我变漂亮了,他没有看出来吗?他凭什么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呢?就算认出来了,也应该惊讶地说一句:“哎呀,沙吉!真是沙吉吗?长这么漂亮了!我都不敢认了。”
想到这里,我简直有点愤怒了。他不是叫我“常来玩”吗?我现在就去“玩”,我要弄弄清楚!
当我再次出现在“大人”面前时,他依然没有惊讶,好像料定我马上就会去“玩”似的。
他坐在一块木板上,也丢给我一块木板,说:“坐吧。”
我就坐在木板上,靠着墙,和他聊天。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作旧的地板上,并随着外面树影的摇动,游移不定地晃来晃去。
一直都是我在说话,真想不通我怎么会有那么多话可说。我早已把刚才的“愤怒”忘得干干净净,说的只是这些年来我攒下的故事和从我身边走过的人。
我从六岁时遇到他的那天说起——当然没有告诉他“沙吉”这个名字其实是他给我取的,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我说了我的父母和他们给我的蝉;说了我为什么到这座小城来并且待了这么久;说了云婆婆、“那个人”,还有边边;说了水、井、妖门和腰门、白猫,还有染红了天的大火;说了青榴、兔子嘴巴、闹鬼的藏书楼、漂亮女人,还有青榴的养父养母;说了巧巧、哥、木秋千,甚至信使、白蝴蝶和一次次飞走的大鸟;说了木木客栈、铜锣、苇林姐和一片惊心动魄的河灯……
我发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对谁说过这么多话,我觉得他是可信赖的,并令人感到亲切。我什么都想对他说,也觉得什么都可以说,不用有丝毫的遮掩、保留、躲闪、防范……我不知道这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从何而来。
他一直安静地听着,只偶尔提些问题。阳光不动声色地一点点往上移,照亮了他的眼睛。那是一双幽深、沉静、柔和、坚定的眼睛,阳光像是醉在了里面,留恋着久久不去。
这么长的时间,竟没有一个顾客进来,让我能说得畅畅快快。
不知说了多久,我停下来的时候,他眯起眼睛看着我,终于说道:“我明白了,沙吉,你就是这样长大的,并且,变漂亮的。”
我笑了。他总算说出了这句话。
“就是你的笑让我认出了你。”他看着我,轻轻地说。
“我笑起来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说不好,”他困惑地皱了皱眉,“但是很特别,和别的女孩不一样。无论你变得怎样,只要你一笑,我就知道,这个女孩是沙吉。”
他这样说我应该是很开心的,尽管他没有说明白我的笑是怎样的。可没来由的,我却突然心慌意乱起来。我的身体像是受到了某种暗示,这种暗示来自一个神秘的、空灵的地方,我预感到,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发生。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且,我开始觉得浑身不舒服,有一个地方在隐隐作痛,我不能确定是胃、肚子还是腰。这种痛是陌生的,宿命的,毫无经验的。我甚至不能确定是痛是胀还是酸,或者兼而有之。
我不清楚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它让我从刚才的侃侃而谈变得不知所措、心神不宁、疑神疑鬼。
天色暗了一些,门口来来往往的游客也少了。时间不早了吧,我该走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沾在裙子上的木屑,跟他告别。
他点点头,依旧是那句话:“常来玩哦。”
“沙吉。”走到门口时,又听见他在叫。
声音不大,却有些变调,压抑着震惊和慌乱。
我心里一惊,回过头来。顺着他的眼光,我看见了——
在我刚才坐过的那块木板上,有一团指甲盖大小的红。
淡黄色光滑、细腻的木板上,那红犹如一片飘落的花瓣,醒目、羞赧,又带着几分喜气。
轰地一下,周围的空气像是被点着了,蹿起了火苗,我被烤得浑身滚烫,连气都有点透不过来了。
我明白了怎么回事,前不久巧巧才经历过。
那天,巧巧半是兴奋半是羞怯地告诉我她怎么怎么啦,还悄悄掏出一包“东西”给我看。她的笑容迷蒙、诱人;她的肤色白皙透亮,闪着细瓷一般温润的光;她的眼睛清澈而又妩媚,这一刻的巧巧好漂亮哦,我看得都呆掉了。
但马上,又不安起来,我比巧巧还大两个月呢!我怎么……
“哎呀,没事的,”巧巧搂着我的肩安慰道,“很快很快就会……你等着吧。”
果然是很快很快,可为什么是这一刻,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在这个“大人”面前,尽管他对我来说是亲切的、熟稔的,可他毕竟是个男“大人”呀!好丢人哦,丢人丢到外婆家去了,怎么办呢……我窘得要哭了。
“这个年龄的女孩子都是大大咧咧的,”他轻笑了一声,用见怪不怪的语气说道,“我妹妹也一样,快回吧,还好你今天穿对了裙子。”
他有妹妹吗?临时编来安慰我的吧。不过,真是像他说的,我今天碰巧穿了条红花裙子,不幸中的万幸,不然就更惨了。
现在,快逃吧!
我一口气跑到商店买好“东西”,又到公厕把自己打理好,才松了口气。
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可我还不想回家,也不觉得饿。我在深巷密屋中闲闲地逛着。我本来打算好好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可脑子空空的,什么念头也进不去;又好像装了太多东西,塞得满满的,密不透风……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时傻笑两声。惹得别人像看神经病一样盯着我看,有一只狗还回过头来,不怀好意地打量了我两眼。
可是,我统统不在乎,这一刻我好开心哦,有一种非常轻捷的感觉,轻捷得似乎可以腾空而起,飞舞起来。
我抬头看了看天,飘着晚霞的天幕下,飞过一群倦归的鸟儿。而且,我好像还听到了鸟鸣声。
可仔细听听,又不像是鸟鸣,“叽——”是知了叫。而且……而且,是从我身上发出的。
我停下来,低着头,把自己审视了一遍——难道是,我的蝉?
不可能,它不会叫,就算它会飞它也不会叫,它是只哑蝉。
可是,这会儿,它真的有点异样。
觉得胸前它贴着我的地方有点发热,还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我把蝉托在手里,看着它一点点变得活灵活现——它的眼睛有了光亮,如两粒润泽的黑珍珠;翅膀的颜色在渐渐地变淡,变淡,直淡成了真正的蝉翼的灰白色。同时,也慢慢地薄了起来,有了透亮的、丝般的纹路,有了飞翔的资质与渴望。
终于,它在我的掌心里,在我的注视下,有了生命的灵性。
我的蝉——复活了。
复活的蝉理所当然是要飞翔的,于是它飞了起来。
它仍然挂在我的脖子上,它通过红丝带传达给了我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攥着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跑了起来。
记忆深处启开了一扇门,可仍然隔着一层纱,朦朦胧胧的,我似乎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一个女孩被一只蝉引领着——但不甚明晰,觉得又遥远,又模糊。
它一直带着我跑,很快就发觉,它是带着我往家里跑。
于是,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看见了,一个穿着红花裙的女孩脖子上拴着一只飞翔的蝉,一路奔跑着。人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跟男孩一样贪玩的女孩。没有人知道她今天遇到了一个人,一个怎样的人;也没有人知道她现在是大姑娘了,就在刚才,她迈入了青春的门槛,走进了人生最缤纷的日子;更没有人知道这一路的奔跑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在等待着她。
终于,跑到了北边街,跑进了圆拱门,跑过了木木客栈,远远地,看见腰门边一个人萧瑟地伫立在黄昏里。
我站住了,低头一看,蝉安静地、一动不动地垂在我胸前,好像它前一秒钟根本没有出神入化地飞翔过——它依然是一件根雕。
再抬头看那身影时,心里一惊:是,难道是……不,不可能,那身影比我记忆中的要瘦许多,矮许多……而且,她、她拄着拐杖,一条腿的膝盖以下是空的,这就更不可能了。可是,她的眉眼分明又是……虽然她比留在我记忆中的形象老了许多;虽然黄昏的风吹乱了她的头发;虽然沉暗的天色让她含着泪的笑容模糊不清……而且,她已扔掉了拐杖,嘴里喃喃地叫“沙吉,沙吉”,颤抖着冲我张开了双臂……
她就要倒下去了!
“妈妈!”
我哭喊着,扑上去,一把抱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