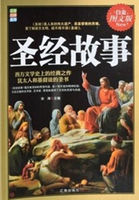佛教与任何宗教一样,在产生之初,面临传教布道的问题。为了聚集更多的信众,佛陀及其继承者在传法布道上往往用精美的语言、生动的故事来吸引民众。佛陀从鹿野苑初次传法开始,采取的是口头布教的形式,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他身后。在传教过程中文学性的语言不仅有利于吸引信众,也有利于布道者记忆佛法。
一、翻译事业的开始
佛典输入前中国古代也有翻译:一为以今翻古,一为以内翻外。以今翻古即以现在的语言去翻译古书中的语言,如太史公《史记》之译《尚书》;以内翻外者即以华语翻译异族之语,典型者如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鄂君译《越人歌》。越语原文如下:
滥兮汴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译为楚言如下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佛教文学的兴起肇始于佛经之翻译,这是中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自从有了翻译之经典,佛教与文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佛经以它精美的语言、奇特的想象吸引了中国文人,使佛教的影响渗透到中土文学创制中。佛教文学输入以后,中土文学在音韵上、故事题材上、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的都受到佛教文学的影响。
中国最早的翻译事业的开始,究竟起于何时,我们已难以确切知道,这一点和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形颇为相似。有关这一点,已在上一章中述及,此不赘述。学界有人以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图经》为真,认为这是中国人最早接触佛典之始,即使此事属实,但此期尚处于口授阶段,未见有译本。汉明帝永平八年(65)答楚王英诏里,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外来的名词,可见当时佛教的典籍已为人所知,但有无佛经译出还不得而知。另有学者以相传永平十年(67)摄摩腾、竺法兰所译《四十二章经》为中国佛经翻译之始,但《四十二章经》只是编集佛教的精语格言,并不是翻译的书;其句法全学《老子》及《孝经》,只是一种提要式的译述;其文体也总是牺牲外来文学的特色以迁就本土的习惯。考其译语,不似东汉时所译,而且该经在《出三藏记集》及《综理众经目录》中均不见记载,恐本经乃是出于东晋时代的一部伪经,因此也不宜将它作为佛经翻译的开始。
可考的最早译者为汉末桓灵时代(公元147年以后)的安世高、支谶、安玄、康巨、严佛调等。晚汉以后有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等。下文将逐一介绍。
二、佛典翻译的代表及译文风格
佛典翻译的代表首推安世高。安为安息(伊朗)人,本名清,为安息太子。后汉桓帝建和初年由安息辗转至洛阳,译《安般守意经》等。安世高的汉译佛典,贵本尚质,他很纯粹地译述出他所专精的一切,能将原本意义比较正确地传达出来,在翻译术语的过程中他常用中国固有的概念去比附,如以“无”译“空”,以“无为”译“涅槃”,这是早期佛教依附于道教在佛典翻译中的反映。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称安译:“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然而不倦焉。”安译比较重视原文,有些地方为顺从原本结构,不免重复、颠倒;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如“受”译为“痛”,“正命”译为“直业治”等)之病。但总的说来,比较偏于直译,措辞恰当,“道而不烦,全本巧妙”(道安)。当代著名佛教学者吕澂先生推崇安世高为“佛经汉译的创始人”,郭朋先生则说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译师”。安世高译文与佛教文学有关的《转法轮经》,叙述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度化曾伴随自己的五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以后《佛本行经》里的一个重要篇章,它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到佛的文学故事。
支谶为月支人,后汉灵帝间译出《道行般若经》等十余部经典。支译的特点是力求保存原意,许多地方多用音译,“审得本旨,了不加饰”。支敏度称“凡所出经,类多深义,贵尚实中,不存文饰”。译文虽有滞涩感,“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此外支曜、康巨也于此时来到洛阳,宣传佛教,所译皆小品,译文特点也是弃文存质,这应该是汉时翻译经典的整体情形。盖此时佛教初入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学尚未深刻交汇,外来僧人精通华语者亦少,故所译少修饰,尚质朴。
到了三国的时候,主要的译者有支谦、康僧会、维只难、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国人。维只难是天竺人,黄初三年(222)到武昌,与竺将炎合译《昙钵经》(今名《法句经》),用四言、五言的诗体,来装载新输入的辞藻,像“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带给当时诗坛一种清新的哲理诗的空气。《高僧传》卷一称其:“未善汉言,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
康僧会是吴国著名的佛教徒,也于赤乌十年(247)来到建业,孙权为他建造了建初寺,他译了《六度集经》和《旧杂譬喻经》。这两本经中故事较多,文学性较强,如《六度集经》中的很多故事流传很广,对后来的文人创制影响巨大,其中的“瞎子摸象”故事,就被苏东坡演绎为著名的《日喻说》,生发出“扣盘扪烛”之典故;《旧杂譬喻经》中也有很多譬喻故事,其中的“多智王佯狂免祸”就被刘宋时的袁粲改编为《妙德先生传》。三国众多译家中支谦译经甚多,影响很大,其中以《阿弥陀经》、《维摩诘经》、《法句经》、《瑞应本起经》为最重要。支谦,月支人,支谶再传弟子,汉献帝末避乱入吴,精通华梵,故所译殊鲜“格格不入”之弊。他反对前人译经过于质朴的风格,主张文质调和,畅达经意,开创了一代新的译风。首创会译之法,对后代译事产生了一定影响。《高僧传》称:“谦辞旨文雅,曲得圣义。”
西晋的时候,竺法护是最重要的译者。竺本月支人,世居敦煌。西晋武帝时发愿求经,尝赴西域,带来许多梵经,译为汉文。《高僧传》说:“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聂承远、道真父子二人,此二人精通梵文。“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竺法护译文弘达欣畅,雍容清雅,所译《杂譬喻经》、《六度集经》皆妙得文体,文义允正。
但翻译的最伟大时代还在公元317年以后。这时候是五胡乱华,南北分朝,民生凋敝到极点的时候,然佛教徒却以更勇猛的愿力,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活动着。许多佛教徒持着“殉教”的精神,在宣传,在讲道,在翻译。从晋室南渡(公元318年)起到隋灭陈的(公元589年)二百七十多年间,据《开元释教录》所记载,南北二朝译经者凡96人,所译经共1087部3437卷。在这九十几个翻译家里,最重要者为道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诸人。这一时期的译经活动改变了最初的口授形式,胡僧来华和华人西行使得精通梵汉的译者得以出现,大规模译场的建立也使佛教翻译更加专业和科学,译经水平大大提高。这一时期对译经贡献最大的当属道安和鸠摩罗什。道安本是华人,也不通外语,但他是译经的卓越组织者和翻译文体的厘定者,“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另一重要人物是鸠摩罗什,罗什生于龟兹,9岁随母历游印度,遍礼名师。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坚遣吕光挟而归,滞于凉州。后姚兴讨光灭后凉,迎什至长安。罗什不仅在翻译内容上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般若经》,而且由于他本人“深通梵语,兼通汉言”,在翻译文体上也一改过去朴拙尚质的文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其译文无不宏丽畅达,语意显明,文字优美,为译界一流宗匠。所译《金刚》、《法华》、《弥陀》、《维摩》诸经,深得文人喜爱。
总体来看,西晋前翻译文风尚质,译文呆滞;晋室南渡后的翻译文风开始趋雅,译文渐趋精美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