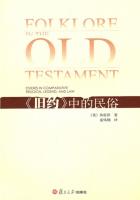清代嘉道以降,朴学隆盛,而佛法浸衰,虽有彭绍升、汪缙、罗有高等名流为之鼓吹,亦如爝火微光,禁不住野马之吹嘘。朴学主将戴震曾与彭绍升反复辩难,断言自己的学问“与足下之道截然殊致”,“不惟其实与老释绝远,即貌亦绝远,不能假托”。咸同以来,外忧内患,国势颓唐,佛教的圈子也笼罩着末法气象。诗僧敬安以为“迩来秋末,宗风寥落,有不忍言者”,“嘉道而还,禅河渐涸,法幢将摧,咸同之际,鱼山辍梵,狮座蒙尘”,揭示出当时佛学的境况。然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涌动,佛学亦渐渐兴起,为近代思想里的一股“伏流”。佛陀的教诲本是异域绝学,经千年汰洗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晚清中西文化的碰撞之中,佛学被视为传统文化的“精思妙理”,成为抵御或融释泰西哲思的重要资源,一些士人相信“此理一明,导欧美而归净士,易如反掌”。杨文会是晚清居士佛教兴起的关键人物。1897年,他创置金陵刻经处,开讲祗洹精舍,“以英文贯通华梵”,一时精英荟萃,“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教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时如苏曼殊、欧阳竟无、谭嗣同、梅光羲、释仁山、太虚等僧、俗名流,都亲炙其学,影响深远。这一时期的佛教徒们以复兴佛教为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一些诗僧则把家国之难的痛感与佛教文化的邃远熔铸于诗文之中,融新贯旧,形成新颖的创作面貌。其中最为特出的是敬安寄禅和苏曼殊的文学创作。
一、敬安寄禅的诗
敬安禅师(1851-1913),字寄禅,俗姓黄,名读山,湖南湘潭人。家世务农,7岁丧母,11岁丧父,孤苦无依。敬安少时牧牛会雨,在村塾前避雨,听人读唐诗“少孤为客早”句,心有所感,不觉泪下。17岁之年,一日见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落,感而大哭,遂投湘阴法华寺,剃度出家。光绪三年(1877)秋,他到宁波阿育王寺拜佛舍利,燃二指供佛,此后自号“八指头陀”。后漫游江南,有《嚼梅吟》印行。33岁以后驻锡南岳,前后居湖南凡18年之久。此其间得长沙麓山寺的笠云禅师传法授记,住持沩仰祖庭密印寺,卓锡三年,宗风重振。50岁之年,主持宁波天童寺,百废俱举。光绪三十四年(1908),敬安禅师在宁波成立僧教育会,被推为会长。他为“保教扶宗,兴立学校”的事务上下奔走,在僧教育会下附设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各一所,为现代僧侣教育之嚆矢。民国元年(1912)四月,敬安禅师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次年元月,示寂于北京法源寺。
敬安闻诗落泪,睹桃而泣,有着敏锐善感的心地。据说,他识字不多,湖南名士杨度强迫他著录诗篇,他竟然十字九误,汗下淋漓。偶赋诗至“壶”字而不省,遂画一“壶”形代字,传为笑谈。然他作诗若有天赋,先在仁瑞寺,受维那精一和尚启发,留心诗学。21岁,于岳阳楼澄神跌坐,下视湖光,一碧万顷,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豁然神悟。归而述于宿儒郭菊荪,郭氏认为他生有夙慧,“语有神助”,授以《唐诗三百首》,劝他学诗。敬安以读书无多,但锲而不舍,潜研默咏,吟咏不缀。在湘时期,与王闿运、叶德辉、邓辅纶、陈三立等往还,诗思大进。光绪十一年(1885)夏,与王闿运、王先谦等名士开“碧湖吟社”,九月与赴王闿运、郭嵩涛等召集的“碧浪湖重阳会”。他广泛接触当代名士,诗名噪于海内。
清季湖南一带,“诗学大盛,高谈格调,鄙视宋明。汉魏三唐,自成风气。”钱基博以为,“近代诗派大别为三宗”,王闿运、邓辅纶为汉魏六朝派,樊增祥、易顺鼎为中晚唐派,郑孝胥、陈三立、陈衍等为宋诗派。其中,王闿运、邓辅纶、易顺鼎等皆为湖湘人氏,而“方民国之肇造也,一时言文章宿儒,首推湘潭王闿运云”。敬安寄禅与王闿运为同里且相交莫逆,受他们的影响,其诗风亦濡染复古倾向。光绪十三年(1887),王闿运序敬安诗,说他“颇癖于诗,自然高澹,五律绝似贾岛、姚合,比寒山为工”,次年又以为:“余初序之,引贾岛以比,意以为不过唐诗僧之诗耳,既隔一年,复有续作乃骎骎欲过慧休,余序未为知言,亟刊前序,更为论定,亦见进步之速也。”可见敬安的诗学进路及其努力的方向。光绪十四年,叶德辉亦作序说:“其诗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后,所交多海内闻人,诗格骀宕,不主故常,骎骎乎有与邓、王犄角之意。”敬安的诗由中晚唐入手,但与学习温、李的樊增祥、易顺鼎有所不同,他近于姚、贾,工于研炼,有苦吟之风,进而上溯六朝,融液禅思,自成面目,跻身于清季旧派诗人的代表。
然而敬安并非闭门枯禅的衲子、袖手空谈的诗僧,他还以一个爱国护教的宗教改革家的面目出现于近代史上。他留下的近两千首瑰丽诗篇,不仅记录着一个僧侣的心灵体验,一个诗人写景的咏物才情,也闪耀着一个宗教家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和爱国热忱。他的诗歌可以分为即事抒怀、写景咏物和摹写宗教体验等几方面的内容。
敬安生逢离乱之世,其诗篇即事述怀,堪称诗史。他自述:“甲申法夷犯台湾,官军屡为开花炮所挫,电报至宁波,余方卧病延庆寺,心火内焚,唇舌焦烂,三昼夜不眠,思御炮法不得,出见敌人,欲以徒手奋击死之。”其一腔热血,不输千古男儿。他的即事述怀之作数量众多。首先是吟咏时事。1887年,郑州河决,他在诗里述其惨状:“浊浪排空倒山岳,须臾沦没七十城,蛟龙吐雾蔽天黑,不闻哭声闻水声。”甚且悲慨道:“时事艰难乃如此,余独何心惜一死,舍身愿入洪流中,抗涛速使河成功。”表达了他内心的极度哀痛与宗教家的兼济情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死难,他写下《记事十八韵》;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敬安又赋诗道:“天上玉楼传诏夜,人间金币议和年。哀时哭友无穷泪,夜雨江南应未眠。”在这个举国不眠之夜,国家兴亡之秋,兴国上下,同仇敌忾,连僧人也不能置之度外。1905年江淮洪水泛滥,他又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五古《江北水灾》:
死者随波涛,生者何所栖?相携走泥泞,路滑行步迟。饥来欲乞食,四顾无人炊。儿乳母怀中,母病抱儿啼。仓卒骨肉恩,生死终乖离。不如卖儿去,瘵此须臾饥。男儿三斗谷,女儿五千赀;几日粮又绝,中肠如雷鸣。霜落百草枯,风凋木叶稀。掘草草无根,剥树树无皮。饥啮衣中棉,棉尽寒无衣。冻饿死路隅,无人收其尸。伤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灾?
在敬安沾满血泪的笔下,水灾过后满目疮痍、尸横蔽野的凄惨景象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他并非只是一个旁观者,这是他饱含着同体大悲的慈忍之心,以写实的笔墨实录下的触目惊心的诗章。这种题材自杜甫三吏三别以来,虽然屡见不鲜,但却很少能达到这样逼真而动人的艺术效果。除吟咏时事一类外,敬安的咏怀之作也往往运用深情的笔触描摹这个生灵涂炭的世界。如《咏怀诗十首》之四道:“步出城西门,高坟何累累。年深坟土裂,白骨委蒿莱。坟傍哭者谁,云是白骨儿。生既为死泣,死亦待生悲。哀哉亿千劫,无有泪绝时。”纯用白描,直写生命的悲悯与苦难,而以情深语切为胜。他的《感事》诗则把个人和民族的命动绾结在一起,他在诗里这样写道:“吾侪亦何事,涕泪忽难收。鸮獍真成孽,江河欲倒流。可怜豪侠气,虚作杝人尤,郁郁夜难寐,西风月满楼。”在这个沧海横流的世界,生天成佛已经不是僧侣最后的期望,唤醒国魂,重整山河成为他心头不能释怀的使命和责任。这使得敬安的怀古或赠人之作也往往充满着悲怆之情,映现出热血男儿的爱国热忱。如他在《谒岳武穆祠有感》、《谒岳武忠公墓》、《九日过屈子祠》等怀古题材的诗篇里,表达了自己“风雨湖山犹感恨,往来樵牧亦凄凉”的悲怆情怀。他还通过与今人的酬答来写时事,如他吊唁已故的将军说:“哀时心未已,看剑泪沾巾。忍看长城坏,难留大树春。”赠答驰骋缰场的折足将军说:“折足将军勇且豪,牛庄一战阵云高。前军己报元戎死,犹自单刀越贼壕”,但最后却以“身满枪痕无战功”结束,表达了郁结的愤闷与悲怆。《奉寄杨皙子孝廉远适日本》则尤为沉郁顿挫:“借问吾乡杨皙子,一身去国归何时?故山猿鹤余清怨,大海波涛动远思。独抱沉忧向穷发,可堪时局似残棋。秋风莫上田横岛,落日中原涕泪垂。”时局如棋,已成残局,江山故国如日落日原,真是令人有不堪回首的伤感。
敬安笔下有两幅笔墨,即事述怀之作往往苍凉悲壮,有杜甫之风;写景状物之诗,则清秀明隽,警策工稳,颇近晚唐诗人的情趣。如《暮秋偕诸子登衡阳紫云峰》一首:“紫云最高处,飞锡共登临。秋老山容瘦,天寒木叶深。西风孤鸿唳,流水道人心。坐久林塘晚,寥寥钟梵音。”又如《暮游玉泉寺》:“夕阳林谷暝,众鸟亦知还。凉月一渠水,残云数点山。偶随寒磬入,欲共老僧闲。夜久群动息,轻烟澹碧鬟。”这是一个僧人的游踪,寒山枯木,西风孤鸿,老僧寒磬,一派萧瑟景象,带有姚合、贾岛一派诗歌的作风。这些诗往往属对工整,形容萧散,大多是苦吟而成的作品。但他也有灵机一动的兴到之作。杨度记他“游天童山,作《白梅诗》,亦云灵机偶动,率尔而成。然诗诗格律严谨,乃由苦吟所得,虽云慧业,亦以工力胜者也。”所谓“以工力胜者”,显然是指近于姚、贾的写景之作,而他的咏梅诗却大抵是“灵机偶动”的作品。录其数首如下:
了与人境绝,寒山也自荣。孤烟淡将夕,微月照还明。空际若无影,香中如有情。素心正宜此,聊用慰平生。
一觉繁华梦,性留淡泊身。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冷入孤禅境,清如遗世人。却从烟水际,独自养其真。
人间春似海,寂寞爱山家。孤屿淡相倚,高枝寒更花。本来无色相,何处着横斜?不识东风意,寻春路转差。
这些诗不着色相而生意涌动,被认为是独擅千古的作品。关于梅的吟咏,既是一种托物抒情的象征性创作方法,又是诗人人格精神的对象化。敬安以梅花的风姿,展示了自己的佛教信仰和审美理想,寄托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人格向往和佛教精神。梅花生于“山家”,它的出场是与“人境”、“繁华”和“人间”相对而言的。敬安不只把梅花置于冬雪的背景之上,而且把它植于一种超绝世俗的空境之中。夺目开放的梅,掩映在孤烟微月之间,显得“空际若无影,香中如有情”;它噙着雪花,孤立于寒冬之中,给人以“冷入孤禅境,清如遗世人”之感;它斜立孤屿之上,迎风盛开,宛如图画,这不禁使得诗人质问:“本来无色相,何处着横斜?”与其说梅生于雪境,不若说它生于空境之中;与其说它生于空境,不若说梅原来就是禅者空寂的胸襟里的一抹亮色。敬安以空旷的禅境为底色,赋予梅花以空灵飘逸的神韵。远离繁华世俗的梅花,高标独立,浓淡相宜,具有一种禅者的品格,它在空际有无之间横斜旁逸,空灵剔透,韵味十足。钱基博说:“其诗大抵清空灵妙,音旨湛远,以视顺鼎,一清一艳,有人间天上之别。”就是指他的这一类诗篇。
敬安的弟子太虚大师以花来总结八指头陀一生的因缘:“梦兰而生,睹桃而悟,伴梅而终。以花为因缘,以花为觉悟,以花为寄托,以花为庄严”,而梅花是伴他一生的最爱。敬安最初刊行的诗稿曰《嚼梅吟》,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吟咏梅花的作品,留下了许多写梅的名句,如“寒江水不流,鱼嚼梅花影”,“传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梅花在冬天里凌寒绽放,傲立于风雪之中。它象喻着敬安寄禅的高洁的人格,在那个世纪末的寒冬里,它勇敢地绽放,经霜历雪,却越发灿烂。从梅花身上可以看到敬安寄禅孤独超俗的人格精神和暗香浮动的人生风度。
作为禅僧,敬安的一些述理的禅诗往往生动有趣,不流于枯槁。他主持沩仰祖庭,故多有咏颂沩山的偈颂,如《沩山水牯牛颂》写道:“识得沩山牯,林间任自然。身毛亦将白,鼻孔也曾穿。牧笛斜阳里,闲情野水边。一犁微雨足,不负祖翁田。”这里咏颂的是禅门公案,沩山上堂开示说:“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意味着佛性不生不灭,不因俗谛流转而湮灭。而怀海作《沩山牯牛》道尽了人生真谛:“放出沩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体现了禅者觉悟后,任运随缘,洒脱无碍的境界。这个典故流传很广,宋时梁山廓庵和尚作《十牛图颂》,用牧牛隐喻修心的过程,大畅玄风。敬安的吟咏以沩山牯牛的公案开篇,颔联毛将白、鼻亦穿指牧心的过程,颈联以牧童和牯牛对举,呈现出一种人牛两忘、能所共泯的精神意趣,最后一联以牛犁田的生活图画,写出返本还源,耕作自家宝藏的禅宗旨趣。通篇写牛,通篇写心,笔触闲逸,处处透露出禅者的闲情逸志。
他的《色空无碍颂》写道:“树枯自回春,心空岂滞境。灵溪虽湛然,不拒花枝影。”禅不是生命的凋萎,而是枯木枝头摇曳的生意,不是生命的断灭,而是空境里透显出来的生命意趣。禅是清澈的,不是混浊的,如生命的溪流,滔滔汩汩,清澈见底,流过春天,落满繁花锦簇的春色。禅以澄心为上,心镜与大千世界的美丽花影共生共在,不容任何一方缺席。敬安以形象语言来说明“色空无碍”的道理,心源污浊,美丽的也变成了肮脏的,心体唯空,万法就能在心镜里映现出他的本来面目。“色空无碍”实际上构成了诗僧文学创作的基本理据。它首先拒斥那些沉空断灭之论,直面鸢飞鱼跃的世界,它承认心与物相生无碍,绝尘的心镜与本真的世界相映成趣,泯绝对待,构成禅者的独特的审美观照方式。在风格上,这种脱俗的澄明的精神意趣必然指向潇洒绝俗的禅的艺术境界。敬安的咏物诗之所以具有优美绝伦的境界,正是基于他对禅理的深切解悟。
二、苏曼殊诗里情与禅
在清季,敬安寄禅与苏曼殊都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不同程度地倾向于维新和革命运动。然在当时,敬安与王闿运、易顺鼎等旧派诗人过从甚密,其诗歌更多体现出古典诗学与禅学的熏陶。而罗曼殊与柳亚子等结社唱和,属于南社一派,在他身上更为显著地体现着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的巨大裂变。
苏曼殊(1884-1918),学名元瑛(亦作玄瑛),字子谷,法号曼殊,广东香山人。他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苏曼殊幼年寓居广东,备尝家庭和人世的冷漠,有“身世难言之恫”,故12岁随长寿寺赞初和尚剃度出家,受具足戒,嗣曹洞宗衣钵。15岁,苏曼殊赴日本求学,当他去养母家时,与日本姑娘菊子一见钟情,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致使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于惠州再次出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苏曼殊工诗善画,通晓日、英、梵等多种文字,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柳亚子辑其遗著为《苏曼殊全集》。苏曼殊是近代文化史上的奇人,他游走于东瀛华夏,出入红尘紫陌,时僧时俗,缱绻心情与故国沧桑在其诗文中重重叠叠,印成满襟的“脂痕”与“泪痕”。他以自己的初恋故事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其诗风“清艳明隽”,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苏曼殊是一个以红尘作佛事的“情僧”,也是一个以笔砚写情歌的浪漫诗人。他说自己“生天成佛我何能,幽梦无凭恨不胜,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其诗作现存约百首,多数为七绝,内容多是感怀之作,诗风幽怨凄恻,弥漫着自伤身世的无奈与感叹,禅与情所构成的内在张力赋予其诗歌以惊艳之美。
情与禅代表着心灵感觉的两种向度,前者是非理性的情绪的弥漫与爆发,后者是精神的摄聚、宁静与升华,两者一张一弛,构成心灵律动的不同节奏。世俗的情爱原本是诗歌创作与生俱来的动力,而禅心要使之归于幻灭和空寂。当这两种生命的强力发生碰撞的刹那,却能迸出特殊的美感。传统的僧诗创作或趋于淡泊一路,或抒写纯粹的世俗情怀,即使那些偶尔以绮语为诗者,也不过是随手拈来,点缀禅寂而已。而苏曼殊的感怀之作有着禅的空灵萧疏,弥漫着缠绵悱恻的真情与生死永隔的痛感。因为有情,所以有禅,情在禅中,如盐入水,使其诗歌在空门与家国、无情与有情、萧疏与顽艳之间构成张驰合度的艺术张力,这种内在的紧张与舒解,使其诗歌表现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呈现出深挚而隽永的艺术风貌。
生命死恋、家国之痛与空门禅心之间的冲撞构成其诗歌表层的紧张关系。这里的家国之痛包含着家和国两重内容。
一层是“国”与空门的紧张。苏曼殊是倾向革命一派的南社诗人,他的笔下既有家庭身世的飘零之感,也有救国图存的正义感。其《以诗并画留别汤国祯》写道:“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潇潇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僧人的生活并没有让他的热血冷却,在国家存亡之秋,他的诗歌涌动着让人血脉沸腾的力量。他有一首咏郑成功的诗这样说:“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松青夕照边。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郑成功和苏曼殊一样有着日本籍的母亲,同样的血缘传统无疑让苏曼殊深感共鸣。当他拜谒郑成功墓碑时,想起英雄逝去,神州陆沉,禁不住泪流潸然。在这个身著袈裟的僧人的襟怀之中,国破家亡的悲愤和爱国热情愈发表现出沉郁的力度。曼殊的诗歌有时也把美人的意象与家国之痛凝结在一起,如《为玉鸾女弟绘扇》写道:“日暮有佳人,独立潇湘浦,疏柳尽含烟,似怜亡国苦。”这则完全是楚骚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了。
一层是“家”与空门的紧张。幼年失怙使苏曼殊失却了“家”的温存。他饱受主母的欺凌,东渡日本投靠养母何合氏,也并未给他太多的慰藉。他在《本事诗》里写道:“丈室番茶手自煎,语深香冷泪潸然,生身阿母无情甚,为向摩耶问夙缘。”其实,他或许并不知晓自己的“生身阿母”是谁,不论是养母何合氏、还是生母何合若子,一切总归于“无情”,他只能向佛典里寻找母爱的踪迹。在“家”的层面上,他的生死爱恋与僧人身份构成了更为严峻的冲突,构成其精神上的深刻困惑。爱情是苏曼殊诗歌中最为绚烂的主题,他在《本事诗》里说:“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这是一种奇妙意象。僧衣上的脂痕与泪痕如樱花瓣瓣,袈裟的朴素无疑强化了艳若樱花的世俗爱情,两者形成色彩强烈的对比,使这种情愫有着“销魂”的艺术感觉。他的《无题》诗写道:“罗幙春残欲暮天,四山风雨总缠绵,分明化石心难定,多谢云娘十幅笺。”在春残薄暮的时节里,爱恋的心如风雨般让人心悸,连化石般的禅心也不觉忐忑不安:倒底是应当在古庙青灯里一心向佛,还是在云娘的痴情里缱绻缠绵?他的诗作出回答说:“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悟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美人和面壁成空的禅悦之间的冲突最终以“负人”结束,这在他的诗篇里凝结成无法排谴的悲凉。这种生死爱恋、家国之痛与空门禅心之间的层层冲突赋予他的诗歌以摇曳生姿的艺术魅力。
家国之痛与空门禅心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本源,是有情与无情之间的碰撞与对比,这构苏罗曼殊诗歌的深层紧张关系。苏曼殊的少数诗章也呈现出一种无心是道的洒脱。他说:“海天空阔九皋深,飞下松阴听鼓琴。明日飘然又何处,白云与尔共无心。”白云是禅宗习用的隐喻语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行云流水寄托着禅者随缘任运的生命状态,它的质地深植于“无心是道”的大自在与大解脱。有心者深陷计较得失之间,而无心则扫除尘垢,直呈本心,践履生命深蕴的常、乐、我、净。作为禅者,苏曼殊被这种无心合道的境界所启发和感召,但其灵光乍现的禅悟深植于对人间有情的体味之上。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他对女子的感触是敏锐而细腻的,体态轻盈,肌肤若雪,而且怀春思慕,深情款款,散发着成熟的味道。然而诗人笔锋一转,以一钵“无情泪”消解深情。但若是“无情”,因何“有泪”?若是“无情”,又缘何“有恨”?泪水无疑是有情的象征,而欲语不能的深深的惆怅与伤感则构成弥漫诗境的旋律。然而,泪水盛在禅者的衣钵之里,一腔幽恨束缚于这领袈裟之内,这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悲剧意象。
他的诗歌之钵里盛满泪水,这是僧与俗、无情与有情之间的激烈冲突的象征。这种悲剧性的冲突是构成其诗歌之美的源泉。苏曼殊写道:“棠梨无限忆秋千,杨柳腰肢最可怜,纵使有情还有泪,漫说人海说人天。”他用艳丽的笔触记下了他在爱恋与禅寂、有情与无情之间的挣扎。他笔下的情人是美丽而骨感的,但是不论是泪痕还是脂痕,都不用提了,红尘往世俱往矣,人天眼目是佛心。他选择了无情,也选择了泪水,他选择了向人天的忏悔,却遗忘不了人海之中的缠绵缱绻。他在《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里写道:“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又曰:“小楼春尽雨丝丝,孤负添香对语时。宝镜有尘难见面,妆台红粉画谁眉。”狂笑与痛哭,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悲与欢郁积在胸如冰火两重天,爆发成这瑰丽的诗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的悲愤与痛觉,让这个孤僧如此久久不能释怀!宝镜有尘与妆台红粉也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六祖慧能著名的偈语说:“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然而诗人的明镜台上却惹满尘埃。诗人从其中并未体味到禅的智慧,而是怀念着那位曾在红粉妆台前画眉的女子。禅在诗中成为他点缀深情的底色,映现出他色彩绮艳的生死爱恋。禅心的空寂原本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曼殊的有情之花盛开于无情的深渊之上,爱恋的泪水堕落在空寂的深渊之中。深渊里没有滋润,也没有回声,只能让人生出无限的怅惘来。
萧疏与绮艳之间的融合构成其诗歌风格上的新颖面貌。苏曼殊的诗里含着一种萧疏洒脱的情怀,如《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写道:“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又如《淀江道中口占》说:“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种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写西湖风光,白云寒梅,潭影疏钟,优美宜人;写淀江道中的农村景致,旷野与微烟,村落与桃花,萧散自然,逗漏着诗人的悠然情怀。作者在写这种萧疏景致时,不忘在其中点缀上红艳如火的寒梅,一树灿然的桃花,白里透红,疏中带密,萧疏的景色与情怀因这些绮艳的点缀而倍觉动人。再如他著名的《本事诗》写道:“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苏轼《定风波》词有云:“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里化用了苏词的意境,表现出和苏轼一样的清旷襟怀。但结合前文,我们知道,他的破钵里盛满的是爱恋的眼泪,他袈裟上的樱花原本是“脂痕”与“泪痕”晕染的色彩,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这种萧疏洒脱之后,有着多少绮艳而伤感的味道。毫无疑问,苏曼殊诗里的萧疏意味,是衲僧诗风的本色格调,烙上了他对禅寂的体验,而他的多情使得这种萧疏更添上一抹绮艳色彩,两种不同的美熔于一炉,便他的诗别具风韵。他在一首小诗这样写禅:“来醉金茎露,胭脂画牡丹。落花深一尺,不用带蒲团。”如来拈花,是一种空灵的禅,而落花做成的蒲团,则展现出一种旖旎情思。蒲团象征着僧人生活的萧散寂寞的生活,落花的绚烂与凋萎、生与死却构成这种生活的质地,更何况这些“金茎”与“牡丹”,原本是用“胭脂”晕染成的。其实,这里的“胭脂”和“落花”不过是儿女情思的一种隐喻罢了。他写给调筝人的诗里说:“乍听骊歌似有情,危弦远道客魂惊。何心描画闲金粉,枯木寒山满故城。”他用“金粉”描绘出来的图画,却只是“枯木寒山”。调筝人的“有情”曾让诗人心怀悸动,但是回想起来,诗人的怀抱之中却只留下这一襟沧桑。人世的沧桑感与寒枯景致构成了萧瑟情调的两种图式,深情款款的“骊歌”与浓墨重彩的“金粉”是构成这两种图式的质地。这种情感的深度和隐喻意义,使他的诗蒙上了如梦如幻的意境。
苏曼殊在《寄调筝人》里说自己“生憎花发柳含烟,东海飘零二十年。忏尽情禅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经眠。”憎花憎柳,是一种旖旎暇思。而诗人阅尽沧桑、忏尽情禅,却在这大好春光里,成为琵琶湖畔枕经而眠的一衲子。他的睡眠真的如是安详吗?他在这组诗里这样诉说:“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那正黄昏。”其实在看似萧疏的生活里,诗人的内心却时时悸动,他眷恋美人唇上的味道,不禁泪痕满面,他有时倚着孤窗直到黄昏日落,感觉到思念真的可以摧人衰老。苏曼殊诗里的旖旎情怀是一种比语言的绮丽更为深刻的绮美。他把衲子情怀与儿女情长融而为一,把萧疏与绮丽糅为一章,这赋予了他的诗以销魂蚀骨的艺术美感。
中国诗学里有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禅门诗偈里也有绮语寄禅的传统,但是苏曼殊对家国与爱情的眷恋,表现的只能是一种现代意识,一种现代民族主义和婚恋自由精神兴起后的文化心理,现代的家国意识与古典的禅心发生碰撞,使他的情爱与诗学便别具一种深刻内涵和清新况味。苏曼殊的诗歌创作受到李商隐和龚自珍的影响甚深,他有李商隐的深情与绮丽,有龚自珍的萧散与沉郁。南社诗人高旭说:“曼殊诗其哀在心,其艳在骨,而笔下犹有奇趣,定庵一流人也。”他的诗之所以具有超越俗流的真境界,亦不外乎“其哀在心,其艳在骨”的深刻情愫。当家国之痛与空门禅心相互冲撞,当多情与无情之间相互碰击,当萧疏与绮艳之间相互融液,在其诗歌中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紧张和奇趣。这种“奇趣”无疑深化了他的诗歌在情感方面的表现力,使其哀艳之笔获得了巨大的摄服人心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