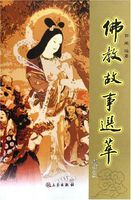一、词与佛禅的结合
佛禅与词的结合是一个不太被研究者注意的话题。就结合的广度和深度比,远不如诗与禅结合得密切;就作品的数量看,也不能望禅诗之项背;但从文学形式上来说,他为词坛提供了一个新的样式,为禅宗文学又拓展了一方领地。
词与禅从理论上讲有许多相契之处。禅家有不打妄语之说,主张真心直说,本心回归;词家有缘情而发之处,主张感动兴发。二者均是抛开政治层面,本心真实情感的抒发。禅讲悟境,喜澄潭布影、宝月流辉的清景,赏竹影扫阶、月穿潭底的自然,倡水月相忘、能所俱泯的圆融;词亦言境,词家有身外之境——风雨山川花鸟之一切相皆是,有身内之境——风雨山川花鸟发于中而不自觉,身内身外,融合为一,亦以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去留无迹,水月镜象为上。禅宗基于本心的发明,破执的需要,有冷暖自知的禅悟境界,绕路说禅的不说破原则,不滞不黏的色空观念;词求境界的需要,审美以深美宏约、要眇宜修为上,以去留无迹、清空无碍为上,以藏而不露、幽微含蓄为上。尽管两者有不少相通之处,然而“诗言志,词缘情”,缘情性无疑是词与禅结合的一道障碍。尤其是词发展的初起,“词为艳科”的属性与佛门戒条相违背,势必使许多释子望而却步。因而释子填词者极为少见,《词品》卷二言:“唐宋衲子诗,尽有佳句,而填词可传者仅数首。”即便是文人禅词,可传者也不在多数。《听秋声馆词话》卷五,载《沤尘集》附邵葆祺有情禅词数阙,如《好事近》云:
曲项旧琵琶,记得玉盘珠落。又见玉人纤手,压当场弦索。一声水调暮江秋,秋鬓已非昨。剩有青衫余泪,为胆娘抛却。
此词与传统小词在主题、设色上别无二致,并不能显现词中之禅气,为一时戏称而已,况且如果真的在词中寓禅的话,也不符合词之本色,“词之最忌者有道学气,有书本气,有禅和子气”。禅家对情的戒备,词家对禅气的防范,使得看似本该顺利结合的两家如终没能如禅诗般发展壮大。
二、佛禅词萌芽阶段
关于佛禅词的诞生,一般多忽视前期佛禅与词的结合,较多关注的是苏轼与黄庭坚的创作,大有将东坡封为“禅词”鼻祖之势。近来已经有论者注意到,较苏轼同时稍前的王安石已有大量创作禅词的情况,此论仍疏于对北宋前期以及唐五代词,尤其是敦煌词的考察。如翦伯象即认为禅词的自觉创作阶段是在北宋中叶,翦文说:“即便唐人某些词作在某种程度上隐含着一定的禅味,但我们仍然认为,这种禅味并不是作者自觉自为的结果,这样的词也不能算作是正宗的禅词。”此论已经注意到了唐人某些词作中蕴含禅味,但否认这种禅味是作者自觉自为的结果,并以此来否定唐五代禅词的诞生却是不合理的。用创作的有无意识性来作为衡量标准,有其合理的一面。日本加定哲定即认为:“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作者把自身对佛教的体验或理解,运用文学的技巧、形式等表达出来的作品。是作者有意识地从事文学创作。”禅门诗偈中固然有诗僧有意识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写的禅诗,但也有许多禅师只是借着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禅悟,他们并非刻意从事文学创作或追求文学上的成就。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留传下的不一定是优秀的作品,而这部分并非刻意之作却往往是佛教文学中的精品。因而衡量佛禅文学的标准应有二:一是创作的有无意识性,二是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把此标准移之于佛禅词的创作,则既要看禅词创作的意识性,又要兼顾禅词的数量、质量。
从禅词的发展情况来看,唐五代禅词在技巧上是幼稚的,韵味上也乏善可陈,但以为唐五代的禅词不是自觉自为的结果似有不当。唐词中神秀的《五更转》,敦煌词中的《维摩五更转》、《无相五更转》、《禅门十二时》、《圣教十二时》、《学道十二时》等都是通俗的佛曲、佛赞,创作目的和动机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适应民众或僧徒的知识水平,以喜闻乐见的方式阐扬佛(禅)门宗旨,属自觉有意识的行为。从数量上来看,敦煌词中佛禅词的比例极大,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就讲到“佛子之赞颂”这一题材。考敦煌词,亦知确实存在大量佛曲,如《五更转》、《十二时》等,其他诸如咏禅寺、僧人、水月、观音,赞羡佛境等题材也占了很大比例。据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统计,在任二北先生《敦煌曲初探》所收录的545首词中,有关佛教的就占了298首。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一书中据任二北先生新出的《敦煌歌词总集》所收1200余首统计,显示佛教文学约占四分之三。如此众多的佛禅词作绝不是几个人的偶发行为,而是众多作家有意识创作的结果。
如前所述,分析禅词的创作情况,除了看创作的自觉与否,还要看作品本身的质量,具体到禅词来说就是是否有禅味。唐五代一些佛禅题材的作品虽然不少,但真正具有禅味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几乎都是劝恶扬善的宣传,语言质俚,缺乏词的空灵境界和禅的哲理趣味。但披沙拣金,仍有质量较高的作品。如无名氏的《浣溪沙》:
五两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行。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满眼风波多闪灼,看山恰似走来迎。他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这首词由舟行岸移这一现象引出“幻觉成真”的道理,情景融合,禅韵十足。此词对北宋前期词家林逋即产生了影响,林和靖词《长相思》曰:“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两岸青山相对迎”一句即脱胎于无名氏《浣溪沙》“看山恰似走来迎”。释德诚的一组《拨棹歌》也是较成功的作品,共39首,以钓鱼为题材,通过水天一色的圆融境界展示了“静不须禅动即禅”的动静一如、体用不二以及“不计功程便得休”的随缘任运等。尤其是其二:“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黄山谷的《诉衷情》即点化此首而成。全词虽讲禅理却不枯燥,是非常成功的作品,对后世禅词的影响也非常大。其他诸如《五更转》等禅词,虽然语言质俚,但从民间词的角度定位,仍不失为上乘之作。
综上所述,佛禅词在唐末五代已肇其端,佛门中有意识地创作通俗的禅词以阐扬宗旨。但从艺术的层次来看则缺少词的要眇宜修,其提高要待后来的北宋一朝。
三、佛禅词发展阶段
北宋一代,倡三教融合,除宋徽宗演过一场短暂的以道代佛的“闹剧”外,历代君主对佛禅基本都是持支持态度。即使对佛教的发展需要限制时,也是通过减少度牒,抬高剃度门槛,以僧尼的自然死亡来减员的舒缓手段进行调节。终宋一朝,尽管佛教的势力有时也很大,也曾有过裁汰僧尼之事,但终未曾发生过像前代“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赵宋一朝在立国之初,为了防止武人专权,对文人礼遇有加,“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文人士大夫物质上极大满足,为他们的参佛觅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熙宁、元祐党争,庆元党禁也把一部分士大夫的视野从官场驱向丛林。加之宋代临济、云门大兴,参禅之风颇盛,上至皇室,下至一般官员,与禅僧多有交往,甚至许多文人士大夫被禅史列为法嗣。如驸马李遵勗、英公夏竦为谷隐禅师法嗣,文公杨亿为广慧琏禅师法嗣,俱属南岳下十世临济宗。著名文人苏轼为东林总禅师法嗣,黄庭坚为黄龙心禅师法嗣,苏辙为上蓝顺禅师法嗣。其中东坡之于佛印了元、参寥子、惠洪觉范,山谷之于悟新禅师、法秀禅师的交往,在文坛中传为佳话。禅宗的大盛与参禅之风的流行,为这一时期禅词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一)张王示范
潘阆《酒泉子》曰:“长忆钱塘,临水傍山三百寺。僧房携杖遍曾游,闲话觉忘忧。栴檀楼阁云霞畔,钟梵清霄彻天汉。别来遥礼祗焚香,便恐是西方。”这首词从末句来看,主要表达的还是净土思想,不过词中所写的钱塘寺庙之繁荣兴盛,栴檀楼阁之云蒸霞蔚,钟声梵音之响彻云霄,可为佛禅词发展的征兆。另一首《酒泉子》曰:“长忆孤山,山在湖心如黛簇。僧房四面向湖开。轻棹去还来。芰荷香喷连云阁。阁上清声檐下铎。别来尘土污人衣。空役梦魂飞。”以僧房湖光山色的秀美,僧寺梵音的清声悠韵,揭开了士大夫禅词写作的大帷幕。
真正首先扛起禅词大旗的不是居士,不是禅僧,而是紫阳真人张伯端。张伯端字平叔,号紫阳,浙江临海人。他是北宋道教的代表人物,被尊为道教南宗的宗祖。恰恰是这位道教的代表人物,一口气写了12首《西江月》禅词,另外还有一首《满庭芳》牧牛词,禅道杂用。张伯端虽为道教中人,但对禅宗的思想还是极有见地的,雍正帝在编《御选语录》时就曾把他的《悟真篇》选入,因而这位道教南宗宗祖有禅词的写作也就不难理解。这组《西江月》大多是表达禅宗思想,如:“妄想不须强灭,真如何必希求。本源自性佛齐修。迷悟岂拘先后。悟则刹那成佛,迷则万劫沦流。若能一念契真修。灭尽恒沙罪垢。”实证的见地,不是由见闻觉知、妄想分别所能得知的,灭妄求真皆为分别意识,而佛法本来就是真妄不二,即妄即真;如永嘉禅师所言:“不除妄想不求真。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佛法一切现成,求妄求真,起心动念,皆是本心迷失。此词强调排除他力,直契自心,表达南宗禅悟即为佛,迷即众生,一超真入的简捷明快家风。再如:“本自无生无灭,强将生灭区分。只如罪福亦何根,妙体何曾增损。我有一轮明镜,从来只为蒙分。今朝磨莹照乾坤,万象超然难隐。”以尘垢镜明为喻,表达人人本性自足,自握摩尼宝珠的思想。复如:“我性入诸佛性,诸方佛性皆然。亭亭蟾影照寒泉,一月千潭普现。小则毫分莫识,大时遍满三千。高低不约信方圆,说甚短长深浅。”“一月千潭普现”用永嘉玄觉《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表达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大小不二,方圆不二,长短不二,佛与众生不二的不二思想。然而张伯端毕竟是道教中人,即使在以玄门说宗门时,也会杂用道教术语,如:“丹是色身至宝,炼成变化无穷。更于性上究真宗。决了死生妙用。不待他身后世,现前获福神通。自从龙虎着斯功。尔后谁能继踵。”
张伯端虽然是北宋第一个大量写作禅词的作家,并且其词作为数亦不少,水平也颇高,但碍于其道家身份,在僧俗两界影响甚微。继张伯端后王安石也创作了一批禅词,由于荆公官至宰相,精通内外典,礼遇文人,结交禅僧,故而荆公的示范作用为禅词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荆公禅词有《望江南》四首,前三首分写皈依佛、法、众,第四首总写“三宝共住持”。《诉衷情》五首,其中三首与禅宗有关,另外还有《雨霖铃》(孜孜矻矻)、《南乡子》(嗟见世间人)各一首,共10首左右,占了全部词作的三分之一。荆公禅词主要是表达佛禅之理和颂扬古德,在写作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量以禅典入词,从某种意义上讲,开苏轼“以诗为词”的先河。如《雨霖铃》:“孜孜矻矻。向无明里、强作窠窟。浮名浮利何济,堪留恋处,轮回仓猝。幸有明空妙觉,可弹指超出。缘底事、抛了全潮,认一浮沤作瀛渤。本源自性天真佛。只些些、妄想中埋没。贪他眼花阳羡,谁信这、本来无物。一旦茫然,终被阎罗老子相屈。便纵有、千种机筹,怎免伊唐突。”“无明”、“妄想”、“浮沤”、“眼花阳羡”皆为佛语佛典,“本来无物”化用六祖慧能《坛经》中“本来无一物”的传法偈,“本源自性天真佛”一句更是取自玄学的《永嘉证道歌》(另一首《南乡子》中“幻化空身即法身”也是取自《证道歌》)。举一隅即知荆公对禅宗典籍非常熟悉,禅语、禅典信手拈来,驾轻就熟。
(二)苏门开拓
自荆公禅词一出,禅词迅速发展,北宋中期,在苏轼的带领下,迎来了“苏门词人”禅词创作的丰收。苏轼及其门人处新旧党争之际,立论与旧党多相龃龉,与新党亦有不合,因而随着新旧党的上下台在名利场中颠沛流离。官宦生涯的反复无常,使他们看透浮名,倾心佛禅,正如苏辙《渔家傲》所云:“七十余年真一梦。朝来寿斝儿孙奉。忧患已空无复痛。心不动。此间自有千钧重。早岁文章供世用,中年禅味疑天纵。石塔成时无一缝。”尤其是苏轼,早年即浸染佛教,仕宦生涯又浮沉不定,一生中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因远贬南荒险些客死海南,禅宗视一切“如梦、如幻”的思想无疑是他精神上解脱的法宝。东坡正是在人生如梦的感慨中创作了大量禅词,如:“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华发萧萧,对荒园搔首。”“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釭。歌舞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逄逄。”“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除人生如梦的感慨外,东坡还有大量禅理、禅趣词,如《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如梦令》(自净方能净彼)、《临江仙》(四大从来都遍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此外还有反言显正的戏谑词,如《南歌子》(师唱谁家曲),开启禅词戏谑词的先河。综观苏轼禅词理趣可分以下几类:一是人生无常之感叹,《心经》中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金刚经》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前举人生如梦的喟叹之词即是对四大皆空的体认。二是随缘任运的处世观,如前举“莫听穿林打叶声”一首,另一首《定风波》能反映出其任运思想,其《定风波》序云:“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苏轼来看,只要能做到“尘心消尽道心”,则“江南与江北,何处不堪行。”三是对禅宗本自具足的体认,如《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这两首词以洗浴来说禅,游戏三昧,正言若反。第一首词意在破除心中垢净、清浊之妄分;第二首意在告诉世人本心清净的道理,若能明白本性的清明,则又何分净垢?
东坡以下,苏门词人禅词创作繁盛,黄庭坚全面继承了东坡禅词的方方面面,甚至有超过乃师的气派。《点绛唇》慨叹世事如梦,“世情梦幻,复作如斯观。”《醉落魄》一组无心于事,潇洒闲适,游戏世间。《诉衷情》点化船子德诚“千尺丝纶”,直逼原作。《南歌子》“万里沧江月”写庖丁杀牛,以“直要人牛无际,是休时”喻功位齐泯的禅悟。《渔家傲》一组颂禅门古德及公案,“万水千山来此土”一首敷衍达摩来华,遇梁武帝,后一苇渡江,面壁九年,一花五叶的传法故事。“三十年来无孔窍”一首演绎灵云志勤见桃花而悟道的故事。“忆昔药山生一虎”颂船子和尚付法夹山善会,得鳞覆水而逝的传奇故事。“百丈峰头开古镜”一首写古灵神赞禅师得法于百丈后回报原师的事迹。李之仪《减字木兰花》:“触涂是碍,一任浮沉何必改。有个人人,自说居尘不染尘。谩夸千手,千物执持都是有。气候融怡,还取青天白日时。”《减字木兰花》:“莫非魔境,强向中间谈独醒。一叶才飞,便觉年华太半归。醉云可矣,认著依前还不是。虚过今春,有愧斜川得意人。”两首词都表达了对人生尘累的厌倦,力图放下执持做个无依道人。第一首“还取青天白日时”仿佛李习之参药山“云在青天水在瓶”之偈,一切现成,各住其位。第二首“认著依前还不是”则彼此不分,今昔俱忘,唯愿做个无尘世之累的斜川“闲人”。
其他如晁补之《满庭芳》:“归去来兮,名山何处,梦中庐阜嵯峨。二林深处,幽士往来多。自画远公莲社,教儿诵、李白长歌。如重到,丹崖翠户,琼草秀金坡。生绡,双幅上,诸贤中屦,文彩天梭。社中客,禅心古井无波。我似渊明逃社,怡颜盼、百尺庭柯。牛闲放,溪童任懒,吾已废鞭蓑。”追慕远公、渊明,表达了对闲散寂静生活的向往。陈师道《满庭芳》:“闽岭先春,琅函联璧,帝所分落人间。绮窗纤手,一缕破双团。云里游龙舞凤,香雾起、飞月轮边。华堂静,松风竹雪,金鼎沸湲潺。门阑。车马动,扶黄籍白,小袖高鬟。渐胸里轮囷,肺腑生寒。唤起谪仙醉倒,翻湖海、倾泻涛澜。笙歌散,风帘月幕,禅榻鬓丝斑。”此词以绮艳繁华起,以人散夜静结。末句在青丝白发的瞬变中悟得禅家世事如梦、万法皆空之妙理。
四、佛禅词繁荣阶段
佛禅与词的结合至南宋达到繁荣阶段,不独野居山林的隐逸之士喜谈佛禅,即使刚正立国、抗敌杀贼的将领也时有禅语。如南渡词人中李光、张孝祥、张元斡、辛弃疾等皆有禅词之作。盖南渡之后主和已成为“国是”,抗战派屡被倾轧,纵有一用也是败多胜少,政治的失意使逃禅之人增多,此与北宋熙宁党争时士大夫谈禅之风相似。此一时期禅词作者多是抗战派将领或与其有关的士子文人。如南宋抗战派将领韩世忠,长于兵,于诗书不精,然而留下的两首词却颇有禅意。《梁溪漫志》记庄敏公评其词曰:“乃林下道人语。”张元斡《满庭芳》:“三十年来,云游行化,草鞋踏破尘沙。遍参尊宿,曾记到京华。衲子如麻似粟,谁会笑、瞿老拈花。经离乱,青山尽处,海角又天涯。今宵,闲打睡,明朝粥饭,随分僧家。把木佛烧却,除是丹霞。撞著门徒施主,蓦然个、喜舍由他。庐陵米,还知价例,毫发更无差。”此词显示出他对禅宗典籍的熟稔:其中笑瞿老用释尊拈花典,木佛烧却用丹霞烧佛典,庐陵米用青原行思庐陵米价公案。另一首《西江月》:“小阁劣容老子,北窗仍递南风。维摩丈室久空空。不与散花同梦。且作大真游戏,未甘金粟龙钟。怜君病后颊颧隆。识取小儿戏弄。”用维摩生病,诸佛探问故事。另一首《虞美人》:“菊坡九日登高路,往事知何处。陵迁谷变总成空。回首十年秋思、吹台东。”则是对世事易迁、人生空幻的慨叹。再如南宋初胡舜陟,与抗金英雄岳飞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岳飞当年在绩溪曾拜访过他,并有诗书往来。岳飞以“莫须有”罪名下狱后,胡舜陟上书为岳飞鸣冤,二劾秦桧。后吕源与胡舜陟有旧仇,向朝廷诬告胡舜陟“受金盗马”、“讪笑朝廷”,秦桧乘机挟权报复,将其下狱至死。胡氏《感皇恩》(丐祠居射村作):“乞得梦中身,归栖云水。始觉精神自家底。峭帆轻棹,时与白鸥游戏。畏途都不管,风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岁何妨尽沉醉。卧龙多事,谩说三分奇计。算来争似我,长昏睡。”此作即有感于是身如梦、人生空幻而作,当是宦海中人的真实体会、有感而发。在生存的焦虑与困惑的张力下,胡氏以禅的智慧消解了张力,那就是不如长睡做个闲人。“光景如梭,人生浮脆”,求名者为名困,逐利者为利困,在位者为官困,在野者为生困,殊不如沉醉昏睡做天地间一闲人。不过这里的昏睡并非是教人日日长睡般的懒惰,而是如大珠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境界,也就是此词中的“自家精神”。这种忘怀一切、身心俱宁的洒脱境界为南宋失意之人找到了精神的栖居地,所以词人对此种心理状态多有抒写。如“低排棹,称鸣鸾。一尊长向枕边安。夜深贪钓波间月,睡起知他几日竿。”(杨无咎《鹧鸪天》)“风波歧路,成败霎时间,你富贵,你荣华,我自关门睡。”(赵长卿《蓦山溪》)“真个先生爱睡。睡里百般滋味。转面又翻身,随意十方游戏。游戏、游戏,到了元无一事。”(朱敦儒《如梦令》)“伸脚睡,一枕日头高。不怕两衙催判事,那愁五鼓趣趋朝。此神要人消。”(吴潜《望江南》)如此这般的原因正如陆游在《桃源忆故人》中所说:“残年还我从来我,万里江湖烟舸。脱尽利名缰锁,世界元来大。”而他们所希冀的境界则如《无门关》第十九则所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南宋词坛,禅词写作最多的当属朱敦儒。朱敦儒字希真,是继王、苏、黄之后作禅词又一大家,其禅词数量堪称宋代之冠。朱氏词主要分禅趣词和禅理词。如抒写人生空幻之苦的有《临江仙》:“堪笑一场颠倒梦,元来恰似浮云。尘劳何事最相亲。今朝忙到夜,过腊又逢春。流水滔滔无住处,飞光忽忽西沈。世间谁是百年人。”《临江仙》:“信取虚空无一物,个中着甚商量。风头紧后白云忙。风元无去住,云自没行藏。莫听古人闲语话,终归失马亡羊。”《西江月》:“元是西都散汉,江南今日衰翁。从来颠怪更心风。做尽百般无用。屈指八旬将到,回头万事皆空。云间鸿雁草间虫。共我一般做梦。”与此相似的还有《西江月》:“廓然总是虚空。”表达本来面目回归的有:“个中须着眼,认取自家身。”“自家肠肚自端详。一齐都打碎,放出大圆光。”“表达随缘任运的有《桃源忆故人》:”谁能留得朱颜住。枉了百般辛苦。争似萧然无虑。任运随缘去。人人放着逍遥路。只怕君心不悟。弹指百年今古。有甚成亏处。“《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此外他的一组《好事近》渔父词、《减字木兰花》等也都是禅理的发挥。
除上举诸人,辛弃疾、陈瓘、吴潜、吴文英等也俱有禅词创作,基本都是以佛禅理、佛禅语入词,属佛教义理的宣讲,基本没有词的韵味。
综观宋代佛禅词的创作,基本是由文人发起参与,僧人之作相对较少,从艺术成就上来说质木无文,缺乏词的空灵之美,大多是宣扬佛禅理的小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