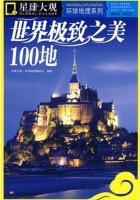片子里,夫妻俩正在为庄稼浇水,黄河离庄稼地很远很远,需要一担一担地把水挑上来,再一瓢一瓢把水浇到地里。虽然很辛苦,但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微笑。他们的笑容与密集的枣花一起,静悄悄地绽放在那片荒野地里。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默默地,默默地绽放在平凡的山谷里,我们都是平凡得,平凡得如此寂静。
几声犬吠,将这冷清的夜勾起了些些涟漪。星月汪洋,月光似纱,星光似沙,尽洒在蓝漆漆的院落里。
夜沉了,哭累的孩儿开始熟睡,细细的呼吸声,甚是平静。
村庄睡着了,这个世界是如此寂静……
眼前沟壑纵横,岭背的残雪星星点点,黄土坡上,窑洞从山顶一直码到山脚,层叠错落。
百年的石板路蜿蜒而上,窑洞与楼阁被高高的院墙围隔,仰视之,如高耸的城堡。
村庄寂静如昨,静静的风,静静的炊烟,静静的人,静静的草木……
要记得,山的那边,依然还有人在等候。
空城
我住在城里,一座大城。
大城很大,无边无际。
城的中心是一方宫阙。皇帝曾坐在高高的龙椅上,享受着子民的朝拜,天下都是他的,包括土地和财富,当然,子民的苦还是子民的,他只要锦衣玉帛、美女佳人。
炮火摧毁了帝国的美梦,这个城疮痍满目。谁在楼上振臂一吼,整个城都变了样。皇帝作古了,高高的龙椅依然还在。
红墙上的斑驳印迹湿润了历史的笔墨,其实那一切与我无关。
经过那座城,一座小城。
小城很小,仅一条街而已。
伫立于黄河岸边的城池,恍若磐石般盘踞于山巅。城墙依着崖壁蜿蜒高悬,坍塌的垛口上有几只鸟儿跳跃着,向着荒芜的城池叽喳鸣叫。人似乎都走了,只有那些坚固的石头沉淀在历史的渡口,裹着一层被风蚀后的古铜色。
冬雾下的废墟,迷离缥缈,所有的院落都被悲凉罩染着,枯槁得行将死去。一个个空荡的院落,被一把把生锈的铁锁紧扣,没了体温,没了犬吠,墙根下的荒草,汲取着土地最后的养分。草木与石墙,是这个城池最后的主人。
斜阳洒进城东头的娘娘庙里,壁画上划痕沉长,就连菩萨的眼睛都被刻上了姓名,蒲团和地面落满了灰尘,踏足而行,尘埃便像被惊扰了一般,在斜阳下四散飘扬。庙塌了又建, 菩萨倒了又立,香火燃了又灭,千年之间,士兵、商人、读书人、普通百姓都曾在这方高高的城池里默念着太平……
菩萨佑护不了永久的平安丰年,无论是宋朝的繁华,还是清末的风雪,那一切都随河流宛转而去,不再回转。
曾被奉为“铜城”的坚固堡垒,挡过炮火与硝烟,却挡不住岁月千年。
虽偶尔能漂泊到另一个地方,但我依然还生活在大城。
大城的景象很瑰丽,一年四季,风沙和雾霾时不时地飘荡在高高的楼宇间。
有时候,我在雾霾里无神地行走。城的夜被七零八落的霓虹撕碎,拥堵的车灯亮了,勾勒着我匆匆的脚步。围巾顶着下巴很温暖,白色球鞋泛着煤灰,空气稀薄,就像高空三万公里,远离了地面。
有时候,我真的像远离了地面。挤在公交车里,往往都像磁悬浮般神奇,燥热的车厢,无尽地摇晃;电脑显示屏闪烁着眼睛,客户催稿了,我却还在懒散地游离,时间还早呢,刷下微博,跟着众人愤世嫉俗,这是个啥样的世界?难道真的只是苦海无边!
如果生活真的是苦海,那我一定还在苦海里沉沦。我提着尿不湿走下大楼,我花高价从大洋彼岸买奶粉;我跑到几里外的菜市场买新鲜菜,我天不亮就起床,拨弄着一天的油盐酱醋茶;堵车堵到深夜,在月光下煮着月光晚餐,在城之郊野的蜗居里,我总在深夜里感叹:这个城市没有星光!
只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
为什么要在这里?我站在残破的城墙上不停地追问。
城的尽头,一缕炊烟滑过眼帘。
王大爷独自坐在窑洞里吃着饺子,他是那座城里,我唯一遇见的人。
每天他都要赶着羊群,从倒塌的县衙走过,城隙间的草林是他的牧场,砖墙上的垛口是他的休憩地。他是这个城的统治者,他坐在高高的城墙上,凝望着四野,一支烟,燃烧着他所有的寂寞。
娘娘庙里,他匍着身子,求着雨露。梦里,雨下了一夜,檐下的水缸满了,南坡的菜地湿了,一垄一垄的鲜绿,是那样的明艳。那个梦,他做了一辈子;娘娘庙,他求了一辈子;
岭上的羊肠小道,他担着水,走了一辈子……
他递给我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黄泥沉在杯里,水里满是黄土坡的味道。
那座城,繁华在他的记忆里。槐花树下,炊烟飘散着,孩童奔跑着,牛羊穿梭着……他说:“那时候人多啊,北门卖饼子的也多,那饼子很好吃,很好吃。”
曾经的城,被一张饼子温暖着;如今的城,空荡荡的,只剩下一片人去楼空后的无边落寞。
他孤独地守着空城,他的儿孙和其他的居民一样,早已搬离了这里。他的家黑而小,陈设凌乱简陋。
“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我不禁要问。
王大爷似乎并不理会我的疑问。
他踱步到院外,指着岭背的那个坟场,平静地说:“我老伴和我的爹娘,都在这里!”
那座小城,经由千年的轮回,只化作了一团黄泥,没了生机。
空城空了,他的子民也都和我一样,四散天涯。
而我在的大城,千年过往,夜如白昼。
谁在用撕心裂肺的声音,高喊着他的独白: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里失去。
空城,太落寞;大城,太漂泊。
到如今,我还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城。
伫立于黄河岸边的城池,恍若磐石般盘踞于山巅。
一棵光秃秃的酸枣树,孤独地伫立在荒原之上,群山在它的身后,绵长悠远。
斜阳洒进城东头的娘娘庙里,壁画上划痕沉长。
老去的村庄
百年剃头店的最后时光
有着传统意味的村庄,正在慢慢老去。
就像岭南那处叫做石塘的村子,被称作“千家村”,当年也算得上是繁极一时。从残存的古堡和老宅来看,这样庞大的村落,在百年前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而今,成片的老宅院被现代楼阁分割得七零八落,很多华美的府邸正慢慢坍塌成废墟。就连繁华一时的三角街,大都人去楼空,空留下几间残破的老屋,祖先营造的古老巷陌,已是风雨飘摇,没有了温度。
这里安静寂寥,偌大的村庄,不管是新巷子还是老弄堂,除了几个玩耍的孩童和行动迟缓的老人,基本上也无其他行人。
见到那个剃头师傅时,他正孤零零地坐在剃头店的板凳上,低头抽着烟。那间剃头店,怀旧的味道很吸引人:老式推子,折叠剃刀,铁制理发椅,斑驳的大镜片……
说起来,多年前的故乡,也有一间和这间几乎一样的剃头店。小时候,经常会被母亲连骗带哄地拽进故乡的那间剃头店。剃头的是个消瘦的中年男子,因为右腿有点残疾,不懂事的我们都偷偷地叫他张瘸子。在我的记忆里,他每天忙着为别人剃头刮须,自己的头发浓密杂乱,却不见怎么打理。
没有哪个小孩不讨厌理发的,我也一样,不喜欢长时间坐在那里听任摆布,最令人心烦的就是被按在瓷盆里洗头的那一刻,满脸都是那香得发呕的肥皂沫。黑漆漆的剃头店里,一盏枯黄的白炽灯被风撂起又撂下,忽闪忽闪的,手推子嚓嚓作响,发丝落了一地。当屋外传来伙伴们的嬉闹声时,我就再也坐不住了。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头顶被死死按住,无法动弹。我委屈无奈地呆坐在铁椅上,眼角似乎瞥见张瘸子那得意的笑……
张瘸子的笑容连同那间剃头店一起,早已是梦里那张发黄的书签,只有在记忆被风吹起的时候,才会偶尔从册页里滑落。而这里,在岭南的一个村落里,那一间旧旧的剃头店,像极了儿时光顾过的那一间。只是剃头店里没有了儿时的闹热,没有了顾客,也没有吵闹不停、趴上窗台向内张望的小伙伴,店内一片清冷,一片漆黑,只有剃头师傅手上的香烟飘散着一层蓝幽幽的光。
见我们在店里徘徊张望,老师傅只是抬头笑笑,也未过多言语。等我们上前打招呼,老爷子便随和地和我们攀谈起来。
“我今年八十了,从十七岁开始学剃头,到现在有六十多年啦!”老师傅说,那时候家里穷,早早地就跟着师傅学习剃头,学剃头也不容易,烧水、打扫卫生、苦练基本功……经过一些年的磨砺,出师之后就继承了师傅的剃头店。
“几十年了,我家的店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现在生意虽然很不好,但我也老了,也做不动别的事情了!”说到这儿,老师傅很是感慨。
在店里待了好一会儿,依然没有顾客光临,村里老人越来越少,而老式剃头店完全不能满足年轻人的需求,所以,那些充满怀旧气息的剃头店大多已凋敝零落,令人怀念。
和老爷子攀谈了一会儿,随行的朋友决定在这里剃个头,老师傅当即就忙开了。待朋友往那高铁椅上一靠,只听陈旧的椅子嘎吱一声响,一块白底蓝花的围布就套了上去。老师傅随意地摆弄着发丝,用梳子把头发拢在一起,再用手夹住,手推子便咔嚓作响,头发纷落如雨……
头剃好后,还要刮鬓角、修面,这些步骤倒是常见,最让我吃惊的是,老师傅还要给朋友剃眼角毛,当八旬的老爷子拿着刮刀抵着朋友的眼睛时,我还是有点肝儿颤。
“我们村小孩的满月头都是我剃的,别人都不敢剃的噢!”看出我们的担心后,老师傅自豪地说,“我现在眼不花、耳不聋的,手上功夫一样地溜!”
的确,老师傅的动作很是麻利,速度也完全不输年轻小伙子。修完脸后,朋友朝镜子里静静地看了一下,那张脸神采奕奕,果真清爽了不少。
老师傅忙完后,又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抽着烟,和工作中的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他开始佝偻着身体,面无表情地坐在幽暗的时光里,静静地发呆。总有一天,理发椅静止了,剃刀也布满了锈斑,“5元”字样下方的镜子里,空无一人……
他和他的剃头店一起,正在时光里孤独地老去。
苍老的巷子深处,绿色的藤蔓郁郁葱葱。
老师傅的精气神很足,工作速度也完全不输年轻小伙子。
一只老猫,警惕地看着来往的路人,荒废的宅门上写着“岁月更新福满门”的期待,只是岁月年年更新,村庄却越来越凋敝。
入孝巷的老阿婆
谈及客家围屋,很多人的脑海里就会闪出或圆或方的大土屋。但是,我到访过的灵溪大围,却是极为普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同样都是围挡而居,但它仅仅只是村庄房屋的外围再圈起一道围墙。整道围墙呈长方形,有三座围门,围门上建有围楼,用于放哨和议事。沿围墙内侧走廊建有房屋,由此把三座围门和围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犹如一座城池。
先人精心垒起的小小城池,想必,也曾护佑过村庄百年的平安。
经由岁月的侵袭,围墙的内部已是凌乱不堪:几座新房打乱了土墙瓦房整齐划一的布局,而很多老宅又被遗弃,残垣断壁,杂草丛生。
村庄虽然破败不堪,但身临其境的感觉很是奇特。经由高大的麻石垒起的围门而入,有一种闯入秘境的感觉,对于密闭的空间,人似乎总有一种奇特的探索欲。的确,从清朝到现代的时光混搭:土墙、混凝土、雕花木门、铝合金窗,以及前方那寂静无人的街巷,都让我们越发地感到新鲜。
一群老人,正在西边的巷口游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有的在扫地,有的在哄孩子,有的只是呆呆地坐着,低头看着脚下的土地。看到外乡人突然闯入,他们没有惊愕,没有笑容,没有任何表情。围墙中的村庄,似乎是孤傲、沉闷的,就像电影中侠客们行走的江湖,那寂静的、看似平淡的路途,无数人都在其间沉闷地行走。
村里的每一条巷陌,或许都是他们这一辈子难以走出的江湖;闲散着的每一个人,也或许都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村中唯一和我们有过交流的,是祖祠旁住着的冯阿婆。
当我们走入村子正中的入孝巷时,听到脚步声的冯阿婆拿着杯子扶门远望,向我们微笑着,巷口的那只黄色大猫也出神地向我们张望。我喜欢记录这样的画面,那一抹浅浅的笑容,那一张善良的脸庞,远胜过一切美艳的雪山和夕阳。
冯阿婆热情地招呼着我们,泡上一杯茶,扯上几句家常。冯阿婆很健谈,好在我约莫能懂几句客家话。就在那昏暗的老宅里,一台座钟,一张八仙桌,一把竹椅,几面斑驳的土墙……一缕阳光正穿过亮瓦,照耀在墙壁上的相框上,相框里有阿婆的子子孙孙,精心摆放的照片重叠着思念和孤单。
冯阿婆和大多数村庄的老人一样,生育了一群儿女,但依然留守在孤寂的村庄。老伴去世后,她就一个人守着这幢毫无生机的老宅,拾着春夏秋冬不变的寂寥。但是,老人却丝毫不提孤单和落寞,她只是诉说着孩子过年回来,给她买的衣服,给她的零花钱,给她的微不足道的好。得知我们来自北京,她又叨念起在北京学过理发的孙儿,说他的聪明和能干。
她的心里,自己的孤单或许微不足道,儿孙们的幸福安康才是她心底最美的团圆。
带着她的诉说,我们转过身去,走出了入孝巷。回头望去,那只大黄猫追老鼠去了,不见了行踪,而冯阿婆正端坐在入孝巷的拱楼下,孤单无声。
她和她的巷子一起,正在时光里孤独地老去。
听到脚步声,正在喝水的冯阿婆便扶门远探,巷口的那只黄色大猫也出神地向我们张望着。
冯阿婆正端坐在入孝巷的拱楼下,孤单无声。她和她的巷子一起,正在时光里孤独地老去。
界上巫师
不知是从哪儿看到过那幅画:一匹白马,穿梭在云雾中;一树桃花,映红了漫天的云霞。总惦记着画里的那个地方,它的名字叫丁家界。
不知为什么我会如些迷恋这样的村庄,有时候仅仅因为一张照片,有时候也仅仅只是朋友的一句描述,我就会疯狂地向往着诗意中的那些地方,无论路途如何艰辛,我自顾自地、执拗地行走在每一个醉人的村庄里。
丁家界的覃大伯,也是一个执拗的人,他在山顶的宅子里执拗地生活着。平日,除了邻家弟弟三两口人之外,仅有一只大狗相伴。
那日见到他,他穿得很是奇特,头戴“日月”字样的四佛头冠,身穿黑色白领斜襟上衣,再围上一条花条布拼接的围裙,坐在堂屋的正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他身后的八仙桌上,堆放着菩萨像、油灯、令牌、铜铃、符版……早就听说覃大伯会巫术,今日见着这些玄幻的场面,倒也十分新奇。
他慢慢地给我讲述他的信仰,我听得云里雾里,倒是他自刻的符版,我觉得还有些美感。其中有一道符是祈求财运的,正面图案是人和马,反面是几个看不懂的文字,他给我特别解说了图案的含义:以前山中匪患横行,古人为避开劫难,主人就会来求这道符,祈求出入平安、财源顺畅。
早就听说过湘西的巫术很邪乎,而这离湘西不远的小村庄,想必巫术也是传自一系的。覃大伯的土家巫术和道术有点相似,或许覃大伯只是用他体会的玄理美化装饰着自己的信仰而已,灵不灵验,那些都要时光来验证。
不过,覃大伯很认真地一再强调,他十来岁时就跟着一位老巫师学巫术,他还能在烧得通红的铁块上走路,还说可以教我。听到这里,我立刻摇摇头,以示抗拒,这个,一般人还真是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