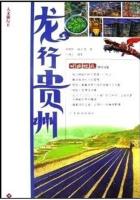我和小伙伴也连忙加入到采茶的队伍中。虽没采过茶,但也知道一定要采芽尖尖,所以,我小心翼翼地、一枚枚一颗颗地细心采摘着。只是一上午过去了,小竹篮还露着底呢。一旁的小伙伴没耐心了,提着竹篮就跑进林子里玩去了。
那天的太阳很大,虽是春天,却也晒得叫人喘不过气来。中午了,又饿又渴,我便去泉眼边捧了点水喝,看见几位阿姨在吃茶叶蛋,才想起来,忘了带吃的了。我忙提着竹篮进林子去找小伙伴,一不小心被树根绊了一跤,茶叶散落了一地,顿时万分委屈,有种想哭的感觉,但还是强忍着,又小心翼翼地、一枚枚一颗颗地捡起茶叶来。身后响起了小伙伴的呼唤声,回过头,只见他捧着一捧黄灿灿的小野果向我走来。那顿午餐,就是那些野果和几朵映山红,外加一些茶苞。
又煎熬了半个下午,手发黑发痒,我实在对这种枯燥的运动坚持不下去了。乡亲们大多还在继续战斗,我和小伙伴却灰头土脸地走向了茶场的工作坊。
茶场的工作坊很长,从大门往里,两边都是锅灶,炒茶的工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经过长长的走廊,就到了收茶的地方,我把竹篮往收茶的老大爷面前放了放,老大爷面无表情地拿了过去,先是看了看茶叶的好坏,连篮子一起过了秤后,再把茶叶倒在一边,又称了称空篮子,而后冷冰冰地告诉我:“两斤,一块钱!”
当我接过皱巴巴的一块钱时,心里那叫一个喜悦啊。不过,我有点疑惑,感觉走了一圈后,茶叶多了不少。在下山的路上,小伙伴悄悄地告诉我,称茶之前,他从茶堆里给我偷了一把茶叶……我愣了一下,许久都没缓过神来。他笑笑,若无其事地从我眼前跑开了。他的名字叫阳,他的笑很狡黠,却又很温暖。
又累又饿地回到了村子里,母亲焦急地站在村口寻我。见到我之后,她先是一顿责备,而后又是几丝关切。黄昏下,当我默默地往母亲的手里塞着一块钱时,母亲的眼睛泛着泪光。母亲把那张皱巴巴的钱摊开,放在我的掌心上,好久都没说一句话。
家乡的茶园开满花,二十年来,开开落落,无人问津。我们都离开了故乡,离开得那么久远。故乡也在沉默中慢慢变化,那些关于故乡的一切,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就如同那处茶园一样,已经长满了野草,面目全非,陌生得不像从前,我也无心去分辨。
当青丝变成白发,故乡是那样的孤独。我们注定了要与故乡分离,生活在别处。现在与故乡的联系,或许只是一张汇款单,也或许是过年那几天短暂的重逢。
家乡的茶园开满花,零落的花瓣已无处安放。
每个清晨,故乡的山岭都是如此缥缈。
那迷蒙的山脊之上,有我儿时最向往的乐园,它的名字叫仙姑台。
听着仙姑台传说长大的我们,不会再把传说诉于下一代,仙姑台只会更加寂静落寞。
透过破败的门框,还能依稀看到制茶作坊最初的样子,长长的走廊,长长的旧时光。
茶园彻底被抛弃了,草木疯长,完全没有了茶园的模样。走入其间,在那一缕阳光下,零落的茶花散发着熟悉的清香。
淡淡香雪海
冷了,暖了,暖了,冷了,秋锁重楼,皖南的菊花开了,沿着坡地起起伏伏,白晃晃的如同层层叠叠的雪。
几年前,岳父得知我喜欢拍点片子,就向我絮念着故乡的风景:“那菊花啊,就像雪一样,白白的,落满了房前屋后……”我被这样的描述所吸引,念想着,念想着那推开木格窗涌入的菊花雪,念想着那粉墙黛瓦上升起的徽州月。
当念想的风景就在眼前,便迫不及待地奔向了菊花园。这儿的菊花一般都种在茶园里,一行绿茶一行白菊,一行绿茶再一行白菊……圆圆圈圈,从山顶一直弥漫到山谷。叔叔婶婶们一大早便忙开了,迎着朝阳,采撷着沾满露水的鲜菊。打小我也是劳动好手,见到如此美妙的农活,二话不说,背起竹篮就加入到采菊大军的行列中。
露水浸润过的菊花温润洁净,用手轻轻地掬采,几声清脆的声响后,手掌里已蓄满了花雪。满溢的露水顺着花雪滴落,水珠儿回环浸润,掌心变得白皙光洁。而后,再轻轻地将掬得有些温热的花朵向后一甩,雪片便从指缝间滑落,悄无声息地撒向了竹篮。那日的天很静,阳光将远方的树染成淡黄色,错杂的光树下,村庄横陈隐现。南坡的花瓣漫天卷起,一双双皱巴巴的手在雪色中舞动,左肩背起的竹篮深深浅浅,风掠过衣袖,衣袖间若有似无地沾满了香雪。
大家的速度都很快,只几个钟头的光景,一筐筐,一箩箩,满满当当的雪堆挤满了上山的泥土路。泥土路上,时不时地晃过几个村民,岳父和叔叔们笑着与他们打着招呼,年纪大点的,大多还认得岳父,年纪尚轻的,基本与岳父算是陌生人。岳父一般会问:“你爸是哪个呀?”对方答道:“某某某。”岳父想不起来,就会再问:“你爷爷咧?”这问题的时间跨度还真够久远的,有小年轻一下子想不起爷爷的名号来,愣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吐出来几个字:“某某某!”岳父像恍然大悟似的说:“噢,你别说,那小子还真有点像他爷!”离开故乡几十年,偶尔返乡成了岳父回味旧梦、感慨时光最好的旅行。这个深秋的季节,岳父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花田里重逢,心情似乎也都格外明媚,当我拿着相机轻数一、二、三的时候,他们沟壑纵横的笑脸绽放得如同朵朵花雪,有些动人,有些明艳。
一上午体验式的劳作,虽不甚劳累,但小腰还是有点吃紧。而叔叔他们却是十分辛苦的,躬着腰从早采到晚,没得歇息。尤其是冷空气光临、菊花全面开放时,无论是下雨落雪还是结冰,都必须要全面抢收,多耽搁一天,菊花就会全部泥烂,损失巨大。听叔叔他们说,打霜结冰的时候采菊花最是难受:迎着山间刺骨的寒风,握着冷冷的菊花冰,全身不停地瑟瑟发抖……白天采完菊花,晚上就得抓紧时间烘干。晒的菊花色彩不美,一般都采用烘干的方式。用慢火细细烘烤,隔几小时翻动一次,烘烤的时间一般都需要十多个小时,所以,菊花盛放的旺期,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彻夜无眠。
入夜了,坐在粉墙黛瓦的老屋里,沏一杯花雪,黄的蕊,白的瓣,闻暗香浮动,笑靥在水的柔波里慢慢舒展。身后条桌上的老座钟正咔嚓、咔嚓、咔嚓……响着,当、当当当……的报时声一如当年洪亮。妻子小美就出生在这座老房里,关于故乡,小美只有两个印象:被母亲绑在凳子上独自孤单地玩耍,奶奶去世时轻声的呼唤……小美离开故乡时还不到六岁,对这里已没了记忆。
叔叔喝了点酒,摇晃着指着中堂上悬挂的国画说:“那幅画是《隐居图》呢,我当时就不想当什么官,其实也好累的!但都要选我,我也没办法的呢!”我看了看那幅画,白净净的一幅山水国画,还真题着“隐居图”三个字。我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认同,这下叔叔更来劲了,眉飞色舞地讲起了那些已讲过无数遍的小辉煌,说得神乎其神,但也知足安命。最后虽然没听出来叔叔当了什么官,不是村长,好像也不是主任,但是说真的,那幅国画还真是雅致,相比起别人家中堂的花花绿绿,叔叔的审美有点超凡脱俗了。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家的中堂,换来换去,不是松鹤延年图,就是花花绿绿的观音菩萨画像。聊着聊着,叔叔就被婶婶喊去劳作了。“晚上是睡不了了,今天采的菊花露水多,得烤上十六个小时!”说着说着,叔叔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就走了。
天微亮,炊烟升腾,头顶上飘散着淡淡的菊香。礼堂外集满了人,收菊花的市场开放了。睡眼惺忪的叔叔婶婶提着两大袋菊花挤了进去,不大会儿,便称完重验完货了。叔叔淡淡地说:“今天的菊花降价了,原先能卖到六十的好菊花,现在只卖到五十三了。”比起毫不在乎的叔叔,一旁的婶婶倒是有点小失落。岳父安慰了几句,叔叔笑着说:“没什么了,行情说变就变的,菊花一多,价格自然会降点!”叔叔说得很坦然,不带一丝遗憾。此时,晨光正掠过周遭的山峦,南坡雾散了,陌上雪色点点。
北方的冬天已然深沉,忽地又想起深秋的徽州,想起那漫山的菊花雪,是否就在今夜,最后一瓣花朵正悄然凋谢,叔叔担着花雪从高大的马头墙下走过,他回头笑着,诉说着今年的收成。或许那里就是我们向往的桃源,有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好幻梦;而对他们来说,那里只是一块生存的土地,繁衍生息,悲喜静然。
艳丽的花朵看多了,就更钟情于山水间那素白的香雪,就像身处霓虹闪烁的城市,待久了,腻了,累了,多数人就开始怀恋起乡野的悠然雅致来。满园白菊,素雅馨香,淡到极致。淡极,始知花更艳;淡极,方能心素如简。
皖南的菊花开了,沿着坡地起起伏伏,白晃晃的如同层层叠叠的雪。
一双双皱巴巴的手在雪色中舞动,左肩背起的竹篮深深浅浅,风掠过衣袖,衣袖间若有似无地沾满了香雪。
将掬得有些温热的花朵向后一甩,雪片便从指缝间滑落,悄无声息地撒向了竹篮。
漫天的花雪海里,总会碰到采菊的童子,那些懂事的徽州孩子在菊花的香气中成长,采菊是他们谋生的第一课。
徽式老宅里,菊香荡漾,身后条桌上的老座钟正咔嚓、咔嚓、咔嚓……响着。
叔叔担着花雪从高大的马头墙下走过,他边走边向我诉说着今年的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