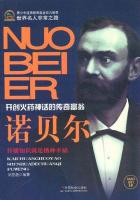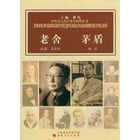元朝的汉化不如清、不如辽和金,甚至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五胡王朝”。蒙元“汉化迟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而言。第一,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的是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困难。第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相对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治国选择。第三,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是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不过,彻底的汉化也未必是件好事,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历史往往充满了悖论。辽、金的汉化程度远甚于蒙元,但他们的许多帝王在“无为”中失去了进取,走向了极尽浮华的生活,儒家传统治国思想中“中庸”的辩证关系,要想准确把握和恰当处理也不太容易。只有既保持一颗积极进取,竞争向上的心态,有少数民族之勇敢、刚强性格,又有儒家“中庸和谐”的协调能力,才能延长国祚,在稳定中求发展。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对“隋富唐强”局面的形成过程中,汉族与“胡族”文化融合的积极意义有如此论断:“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可惜,在缺少积极、有效约束机制下的专制时代,要想让帝王保持“胡”、“汉”文化如此恰切的融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元顺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其他元帝相比,元顺帝很喜欢儒家文化,但他没有辩证地处理好“外王”与“内圣”的关系,没有能处理好“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处世”与“入世”的关系。在改革面临挫折或面对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时,他没有能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去处理,而是走向了消极避世,忘记了自己是身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帝王,自甘沦落为荒诞另类的帝王。他在执政后期,“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国内政治腐败日甚一日,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加剧,最终导致元帝国的分崩离析。
荒淫无道的晚年
据史书记载,元顺帝的私生活是极其奢华糜烂的,这与他继位之初大力推行“旧政更化”的“政绩”似乎联系不到一起。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将两个看似对立的角色由他一个人来扮演。执政之始的顺帝,在治国方面与名相脱脱组合在一起,刷新政治,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有生气、有志气、有文气的年轻皇帝形象;执政中期、尤其是脱脱被贬死以后的他与另外两位丞相哈麻、搠思监等奸臣混在一起,完全变成了一个荒淫无度、昏庸无能、自取丧国之辱的昏君。
元顺帝的私生活被后世责难、有违帝王治国之道者,主要表现在他沉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如热衷于机械制造、歌乐声色等,不以国事为重,所谓“怠于政事,荒于游宴”。虽然其中不免有被夸大的成分,但他精于设计而拙于戡乱,精于嬉戏而疏于谨严,确实应对元帝国的灭亡付有重大的责任。
元顺帝至正年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据《元史·顺帝纪》记载,元顺帝是一位出色的机械制造专家,他热衷于为封建统治者所不齿的“淫巧奇技”的研制。据说,他自制了一种叫“宫漏”的报时装置,报时准确、外观华美。这种宫漏高约六、七尺,宽约三、四尺,装在精美的木匣子里,水在其中流动。宫漏上面刻有西方三圣殿,腰边雕刻玉女捧腰刻筹,到时间就浮水上升。左右各列一个金甲的神仙,一个悬钟,一个悬钲,夜里这两个神仙按更而音,狮凤会在左右飞翔舞动,一刻不差。东西分别有日月宫,刻有六个飞仙。逢遇子午时分,六个飞仙便度过仙桥,到达三圣殿,子午时分一过又退回去。这个宫漏报时非常准确,不差分毫,史书说“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鲜有”。这种报时装置实际上就是在水运浑仪一类天文仪器的基础上设计的自动报时器。这种宫漏的科技含量很高,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曾进献七宝灯漏给元世祖。
另据《元氏掖庭记》记载,元顺帝还制造了一种叫“五云车”的交通工具,该车设计精巧、复杂,内部陈设高贵、舒适,外部装饰雍容、奢华。车内共分为五个包箱,元顺帝坐在中间,另外四个由嫔妃们乘坐。顺帝经常乘坐这辆车子出游,到了晚上,这辆车还装有照明设备,“不用灯烛”。
正是由于元顺帝“心灵手巧”,匠心独运,屡有佳作问世,大臣们也阿谀奉承他为“鲁班天子”。有了大家的“赏识”,又有极高的兴趣,元顺帝常常陶醉于此。他亲手为近臣刻削屋宇的模型,做得巧夺天工,精致无比,然后让这些近臣依照模型建造房子。模型上因为镶嵌了许多珍奇的宝石,内侍们便打起了坏注意,他们哄顺帝说:“这屋宇比不上某某家精美。”于是顺帝便随手将模型毁弃了重做,内侍趁机从模型上抠下这些珠宝占为己用。从房屋、龙船、宫漏到五云车,大都是顺帝“自画屋样”、“自制其样”,这些无不充分地展现了他在工艺学等方面造诣之深。
坐稳江山的顺帝生活也是穷奢极欲,他喜欢工程机械设计和木工制作,所以,一些宫苑竟然由他自己设计。他设计造了清宁殿,殿前建有两座水晶园殿,耸立于水中,外用玻璃装饰,阳光照射,光影回彩,宛如人间仙境。有诗赞美到:“水晶殿宇晚风多,窄窄轻衫试越罗。闲倚银屏望牛女,月宫仙子近秋河。”内苑里使用的是他亲手设计、制造的龙舟,据史书记载,这艘船首尾长达120尺,宽20余尺,船的前部设计有瓦帘栅、穿廊、两暖阁,后半部分则有吾殿楼子。龙船形如巨龙,前后有两个爪子,船体和殿宇装饰以五彩金妆。船上配备有24名水手,个个穿着紫色衣衫,带有金荔枝带,裹四带头巾,分列于龙船两边,手里拿着篙划动龙船。龙舟一移动的时候,龙首及口眼爪尾都可以活动,活灵活现。若非具有卓越的艺术才智,如此巨大、复杂的船只是很难以完成的。元顺帝经常乘龙船来往于后宫至前营山下的湖泊里,嬉戏游欢,乐而忘返。顺帝曾高兴地说:“难怪隋炀帝不惜凿运河,游江都,乐而忘返啊!”
元顺帝还热衷于舞蹈、嬉戏。元朝宫廷乐舞甚是盛行,这些乐舞既用于正规的祭礼场合,也用于宫廷的宴饮游乐活动。元顺帝晚年懈于政事,想尽各种办法享受纵欲。他制造的龙船就是用来游乐的。他选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16人,特为编舞,组成元宫中极为有名的十六天摩舞。晚年,元顺帝又宠幸蕃僧,他曾在京城里组织108人的番僧搞了名为“游皇城”的活动,每次动用数万人,劳民伤财,伤风败俗。
由于元顺帝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汉文化水平,养成了较好的文化心态,所以他对诸多文学艺术形式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他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都非常喜欢宋徽宗的书画,虽然他们都知道徽宗沉溺于书画,沦为阶下囚、丧了国,但二人的兴趣不减。至元元年(1335年)元顺帝看到宋徽宗的画,禁不止赞叹,言语中流留羡慕之情。翰林学士库库在旁说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顺帝问何事?库库说:“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省也。”库库的批评,看似苛刻,实际上很中肯。可惜作为人君的元顺帝虽然已迷于其中,却不能自醒,重蹈了前代君主的覆辙。
元顺帝最饱受人们指摘和批评的是他的“荒淫”和“纵欲”。元顺帝的荒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身边奸臣的教唆。康里人、右丞相哈麻善献媚以取悦皇上。他就给顺帝引荐了一个西天番僧入宫,教他学习所谓的“运气术”,哈麻的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睦儿亦引荐西天番僧伽磷真教顺帝学习一种名为“演揲儿”法(意“大喜乐”之意)的房中术,说什么此法可以“使人身之气或消或胀,或伸或缩”,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其实是在引导顺帝沉溺淫乐。顺帝从中获得了不少乐趣,身陷其中,天天在宫中演习、修炼。后来,他们又推荐西天番僧伽玺真给顺帝教授“双修法”,其实也就是男女交媾的不同姿式。顺帝乐在其中,下诏以西天番僧为司徒,以伽玺真为大元国师。他们的子弟众多,选取良家女子入宫修习秘术,每个子弟赐给他们宫女三四个作为供养。
顺帝的一个弟弟叫八郎,也受了密戒,与秃鲁帖木儿勾结在一起,凑成十“倚纳”。他们引进公卿贵族家的命妇和街坊良家女子到宫里,以供修炼之用。顺帝和十倚纳鲜廉寡耻,人伦丧尽,男女杂处,整日在宫中裸体淫乐,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尽管有人类学家或宗教学者在研究早期人类的知识和信仰时,认为集体裸戏不过是特定时代的特定行为,不能用后世儒家人伦道德和仁义廉耻来加以批评。比如,有人就认为,元顺帝君臣不避人言,在宫中淫戏,与当时一些宗教的教规、经义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一些宗教中的经文、绘画以及雕刻中都表现了性欲的成分。在元顺帝之前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都也都大力提倡多种宗教形式。但生活在14世纪初的元顺帝在已经汉化近百年的元廷统治中心——大都,修此“淫秽”之事,却真切地体现他统治者阶层的荒淫与无耻,反映了他们已经腐烂透顶,不可救药了。这种“淫乱行为”给元帝国带来的巨大消极影响必须受到鞭挞。
顺帝等元最高统治者阶层在醉生梦死的糜烂中生活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却在日益加剧,各地反抗的烽火愈烧愈旺。在元统治的不足百年里,各种反抗斗争不断,据江南地区就200余起,后期更趋频繁。1340年(至元六年),在战火和灾害双重袭击下的山东、河北地区,就发生了300余起农民反抗事件。1345年(至正五年),黄河又在今河南开封东北40公里处决口,大部的村庄、田地和农民被水淹没。数十万饥民涌向街头,迅速演变成为反抗元朝统治不息的力量。黄河决口,天亡元廷。如果不修黄河,洪水肆虐百姓,肯定会引发难民潮;如果修复黄河,工程艰巨,耗资惊人,与国与民都不堪其重。元顺帝还是下定决心,治理黄河。他被迫于至正十年(1350年)改变钞法,次年任用贾鲁治河。钞法变更,导致物价上涨;修河时紧工迫,官吏乘机对百姓敲诈勒索,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和韩山童等为首的多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导致了元朝的最终灭亡。
至正通行宝钞印钞版
1368年正月,在徐达率北伐军平定山东的凯旋歌声中,朱元璋在应天就皇帝位,定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是为明太祖。一个新的王朝,就此诞生。
1368年二月,明朝大将徐达回师河南,兵锋直指汴梁、洛阳,直到此时,元朝内部的军阀内战仍在继续。当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军攻陷通州。椐《庚申外史》所记,一部分大臣再三劝说顺帝死守京城,以待援军。顺帝不同意,说夜间观测天象,大元气数已尽,应当让位于朱元璋。当晚,元顺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八月,徐达率兵进入大都。
逃往漠北的元顺帝屯兵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以示可战。朱元璋曾遣使遗书,对其晓以利害,目的在于招降。元顺帝作《答明主》一诗,令使者带给朱元璋。诗曰:“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归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这首诗的文采如何暂且不论,内容却写得不卑不亢,自认元朝气数已尽,又自诩大元的皇恩浩荡;既高兴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转表达了自己禅让的诚意。这种态度恐怕在历代帝王之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知叱咤风云、纵横一世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看到后世儿孙的如此场景,是该哀其不争,还是该对这种“广阔胸襟”的“谦谦君子之风”而感到一丝自豪呢?
明廷认为妥欢贴睦尔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退居漠北,是为“顺天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逃到草原上的这位颇具豪气的元顺帝在明军接连不断地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终于,1370年(明洪武三年)5月23日,他怀着悲愤和郁闷,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去世。
寿命仅五十载的妥欢贴睦尔的一生大喜大悲,地狱和天堂般的滋味他一一品尝。经历了饥寒交迫,他知道了锦衣玉食的来之不易;经历了流放屈辱,他知道了发号施令的无上威力。他身上流的是草原民族的鲜血,骨子里又渗透了汉族儒家的伦理,他拥有草原民族的洒脱与汉族大儒的闲情雅致。不幸的是,他丧失了草原民族勇猛顽强、锐意进取、一往无前的气概;他玷污了儒家文化中审时度势、知耻后勇的兴乱兴衰的精髓。“旧政更化”没有一如既往地推行,遇到困难就一味退缩,甚至面对挫折反而得过且过,放纵、麻醉自己,整日过着荒淫无道的生活。元顺帝的另类生活,他的悲剧人生,既与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也是草原游牧文化控驭中国时出现的异化和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