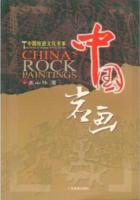《长江七号》是不是喜剧呢?这问题其实不只是对一部电影的提问,因为《长江七号》不是普通一出电影。它的意义因此也不在于有多少好笑或到底好不好笑,而是在全球华人的脖子都伸长以后,它能否提供大众期待已久的满足。譬如它有多少经典对白(如广告术语)可给观众“过口瘾”(即口头临摹)?它有哪些犹如嘉年华的恶搞大场面,让观众High翻天?它有多少“感动位”(也就是梦想成真),把观众从残酷的现实带到人间天上?
大众对《长江七号》的“诉求”如此清晰——不管是知道为什么或完全不自觉,如果一年只看一部“港产片”,它就是很多人的必然选择,因为电影的灵魂人物叫周星驰。所以,当《长江七号》首映场翌日在《明报》刊出该片第一篇影评《当周星驰不再好笑,他还是周星驰吗?》,一看到这标题我便觉得“错矣!”,皆因笑料只是糖衣,大众在周星驰电影中寻找的,其实是权力。
经典对白是把对权力的追求诉诸语言上。语言表现权力,粗口便是例子。只是粗口再粗,试图用它来伤人者首先出拳自伤——真能做到×人家的娘亲,又何须动口不动手?——是无力感促使人们把语言化作性器官来代替真枪实弹。
周星驰的成功(和对港产片的“贡献”),是把大众对命运的不满转(软)化成阿Q精神。明知人家孔武有力自己是绣花枕头,于是来一招转移视线,手中无枪却把两根手指说成弹无虚发。这种被称为“无厘头”的韦小宝神功,讲求的不是大智慧而是小聪明。
小聪明不一定能令所有人埋单,但起码会让自己感觉良好。你一定注意到周星驰已有多部电影都是贺岁片。过年需要周星驰,一般都说是他的戏够开心热闹,我则觉得除了气氛,它还给人带来“希望”,由将片中对白琅琅上口到觉得自己也变“聪明”了开始。
恶搞是搞破坏,其实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片场、球场、上海滩都是权力分配不能混淆之地,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接二连三用“无厘头”手法(或“特异功能”)推翻了它们的权力架构而封王。过程中渲染的不是典型英雄片的“苦练”,却是把被有权势的人逼害放大到像早期荷里活卡通片的猫捕雀一样。观众乐在其中,也是因为周星驰(与同伴们)愈被变态地虐待糟践,自己愈是能够感受“精神和肉体什么都能承受”的权力感。“恶搞”,遂变成不是真对施虐者进行反抗,而是将受虐“提升”为享受:在被虐中接受自己的“命运”,从而体会到自虐的快感。哪怕是与饿狗同抢一盒饭,或高声唱出“屎,我系一笃屎”,全是把憎恨自己变成celebration-唯有在周星驰的电影中,自觉精神或物质贫穷的人才能把对自我形象低落的愤懑变成参加欢乐派对。既能“苦中作乐”,当然不再是没有“(权)力量”。
“出人头地”是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肯定。周星驰的电影不会否认这一点。但他也深深明白“一个人的站上去是千万人倒下来”的事实。所以,他不会像李小龙在《死亡游戏》中把电影胶卷用在一层楼一层楼地打上去,他选择以“自有神助”来实现发达和抱得美人归——这是一种看不见失败者,也不会刺激到任何人的无力感的“成功方程式”。但也因为没有实在的一种本事,他不可能像李小龙般以功夫征服全球。因此周星驰给中国人加油打气,很大程度上是“镜象效应”——你看到你想看见的自己。
2008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