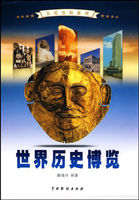高宗武是作为外交界的一匹“黑马”引起人们的注目的。他是浙江温州人,少年即赴日本留学,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有人夸他那一口东京话说得比日本人还地道。对于日本风俗民情朝野大势,了如指掌。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就为国内的一些著名报刊撰写稿件,差不多每投必中,在研究日本问题的学术圈子中,已小有名气。
像他这样学有所长的人,回国后自然成了抢手人物。1931年《中央日报》首先伸出手来,高薪聘他为特约记者,中央政治学校也聘请他,让这位年仅26岁的法学士成了该校最年轻的教授,进入了学者名流之列。才气纵横的高宗武也愈发以中日问题研究专家自诩,文章满天纷飞,评头论足,妙笔生花。
高宗武在讲坛、报刊上大出风头之际,正是汪精卫执掌行政院、兼外交部长之时,这段日子很不好过,“1.28”淞沪之战枪声刚刚停息,热河、长城一带又打了起来,日本人撒泼放刁,搞得汪精卫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白天他打起精神,显得从容不迫,一回家则锁眉皱额,一副愁态,躺在沙发上捂着肝区呻吟。
陈璧君将药递上,关心地问:
“是不是肝病又发了?”
汪精卫痛苦地点点头:
“看过医生了,建议我去青岛疗养一阵子。你看,我现在走得开吗?国家多事,分身乏术。”
陈璧君数落着:
“蒋介石也太不像话,钻到牯岭看风凉,留你在家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落个卖国的名声。听公博讲,前几天开中政会,张继将你骂个狗血喷头,批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是卖国条约。你为什么不说明一下,那也是老蒋的主张。”
汪精卫辩解说:
“张继是个粗人,不必理他。至于那两份协定,倒确是蒋介石的意思。但这我是赞同的,因此,我不能推卸责任,要为他分谤。”
“所以你还要公开声明宣布于天下?”陈璧君讽刺说。
“这,我已经做了。”汪精卫为这种自承罪名的勇气自己感动自己。他轻声吟到前几天发出的电文:
“倘因此而遭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离隙,弟必奋以当其冲。”
“这样,卖国的罪名你就一人承担了?”陈璧君又气又急。
“一人承担又有何惧。”汪精卫态度激昂起来,“现在国际形势险恶至极,我已明白了,国联根本没有力量,英法诸强更是不愿意帮助中国,美国是孤立主义,苏俄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还在内部捣乱。蒋介石去江西剿共,我在这里应付日本人,正是安内攘外国策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他顿了顿,又劝道:
“前几年你随我颠沛流离,受尽委曲。委曲吃苦倒在其次。身在江湖,心在庙堂,赋闲之苦,不是我辈胸怀大志者所能忍受。我不在其位,难道没有人谋其政?我不卖国,也有人卖国啊。再说是为爱国才卖国。”
汪精卫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出理由,但他这番话倒真的说服了陈璧君,她刚才劝汪精卫,不是劝他赋闲摔官印,只是提醒他不要给别人当枪使,替蒋介石背黑锅。她转而关心地说:
“我只是担心你太累了,应该找一个帮手。”
“我已经物色好了一个人,高宗武这个名字你可听说过?”
提起高宗武,汪精卫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他感到自己就像伯乐一样,从芸芸众生中寻出一匹千里良驹。他最早注意到这个人的名字,是见诸于报端。高宗武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知识丰富。更难得的是,他的文章中对中日问题的某些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使汪精卫大有知音之感。因此,他很快请人邀请高宗武来行政院一叙。
高宗武的学者气质立刻就给汪精卫一个好感,应对之间,得体大方,一席话终了,临别时,汪精卫挽留说:
“高先生年轻有为,值此国家用人之际,可否弃笔从政,助汪某一臂之力。”
外表清高而内多欲望的高宗武,一听此言,正中下怀,他也渴望在外交界一试身手。
“汪先生卓而不群,人望所归。宗武年轻幼稚,正需名师前辈赐教。古者弃笔从缨传为佳话,今者宗武弃笔从政,只是希望能为国家略尽绵薄,如蒙汪先生不弃,甘愿随侍左右,听凭呼唤。”
汪精卫大喜:
“先委曲你在外交部亚洲科负责,这可是最棘手也最容易干出名堂的部门,你的今后前程我会安排的。”
高宗武上任伊始,汪精卫就予以非常之信任,1934年底,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赴北平与日方代表商谈关内关外有关通邮事宜。这个问题已经闹了几年了,是个棘手活。高宗武唇枪舌剑,折冲转圜,终于达成协议,日方答应关内关外通邮一概使用南京政府发行之邮票,从而使中方避免有对伪满洲国事实上之承认的嫌疑。这件事在外交部影响很大,当时,凡中日交涉,外交部人员无不视为畏途,弱国无外交,在对方咄咄逼人气势下,据理力争谈何容易,况且“上头”又定下调子,如果昧良心,那一顶卖国帽子又有谁愿意戴上。高宗武此番谈判,就“勉为其难”这一点来讲,已经让人“欣赏”了,何况谈判的结果也算差强人意,不负所托了。
因此,有一次蒋介石从南昌行营回宁,汪精卫谈起此事,眉飞色舞地把高宗武大大夸奖一番。
“唔,这个人我也听说过,很能干是不?”他想多了解一点。
“最可贵之处是在其胆识,敢担待,敢任事,才华,魄力都属上乘之选,设若假以时日,再加磨砺,定是可造之才。”
蒋介石心中暗想:“汪精卫平日自恃才华,很少这样夸赞别人,倒是有必要见识一下了。”
汪精卫依然兴致勃勃:
“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我已打算提拔他为亚洲司司长,主持部内对日关系。”
蒋介石神经立刻绷紧,不能让此人纳入汪精卫集团中,他立刻拦住话头:
“这位高宗武还年轻吧?”
“二十六七岁,正是风华之年。”
“一个不足三十岁的年轻人,刚进入政府工作,做了外交部一名科长,也算不辱他了。汪先生看介弟的话能否考虑。”
离开汪精卫,蒋介石径直回到座落在黄埔军校的官邸,他起家于黄埔军校,住在自己的学生中间,他感到最安全,最亲切。
主持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听说蒋介石从南昌回来,早在这里等候接见。蒋见到他们,劈头就问:
“高宗武你们可熟悉?”
“略有了解,他是外交部的人。”陈立夫感到很突然,不知蒋介石何以对此人感兴趣。
“平日嘱咐你们要留意人才,可这人到现在听说不在党里,不知道你们平日发展组织都发展了什么人。”
二陈一言不发,跟蒋介石跟久了,都知道他发脾气的时候最好装聋作哑。
训了一通后,蒋介石果然消了气,他吩咐通知高宗武,他要降尊接见。
踏进蒋介石官邸,高宗武就感到身体发僵,他不是怯场的人。但这里的气氛严肃得让人窒息,平日的那份潇酒、倜傥都变成了拘谨、畏葸。
侍卫官将他领进了客厅,落座之后,他仔细地打量四周。
客厅的布置简单而庄重,一排沙发,几张硬木座椅和茶几。墙上挂的是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对联: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
这是主人有意表明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一张绘有山水的屏风,给这间宽阔的客厅增了点暖色调。
蒋介石缓缓从楼上下来,楼梯没有铺地毯,因而那有节奏的脚步声增添了主人的威严。
高宗武连忙垂手起立,按着规矩报告了自己的姓名、职务。
蒋介石点点头,示意他坐下。这里没有他与汪精卫见面时那种随意亲切、无拘无束的感觉,四周的空气有一种无形的压迫,高宗武的喉咙感到阵阵发紧。
“你是哪里人?”蒋介石明知故问,现在他对高宗武的生平已经不陌生了。
“浙江乐清”。
“唔,属温州地盘,我们都是浙江老乡。”蒋介石的口音迅速换上浙东方言。
“这是宗武的荣幸。”蒋介石一语三冬暖,高宗武顿感周围的压力减轻,室内也明亮了一些。
“与关外通邮的事是你谈判的?”
“是。”
“这很好。听说你从小在日本长大,对日本很熟悉,你可以谈一谈日本的动态与我们今后对日工作的焦点。随便说。”
这可是高宗武最擅长的话题,他的思路也随之清晰,口齿也恢复了伶俐,从日本的历史渊源,国民的心理素质,军事经济力量各个方面娓娓而述。
蒋介石在心中频频点头,他迅速作出决定,要将此人收归已用。
“很好,你谈得很好,今后应该多担待些事情,为汪先生减少压力,在汪先生手下做事,是会有出息的。”
高宗武早就明了蒋汪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聪明地回答:
“宗武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请委员长放心,我和汪先生是僚属关系,自当尽职本份。”
蒋介石十分满意这样的回答,他站起身来。
“现在国内工作的重点是在外交部,外交部的重点是在亚洲司,我准备让你管这个摊子。”
高宗武心中狂喜,从亚洲司一个科长一跃为该司主管,不啻仕途上跃进了一个台阶。他的脸上露出了感恩戴德的阿谀之色。
“宗武不才,愿为委员长分忧解困。”
蒋介石一摆手:“这是为了国家。若在平时,会有人说你太年轻。但现在时事艰辛,需才甚急,破格提拔也是需要的。”
分明是话中有话,施恩于人。蒋介石这一手不知曾打动多少人,高宗武自然也不例外。
接受过同僚的祝贺,新任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感到前程一片灿烂。晚上,回到自己的寓所,兴奋难眠,盘算着如何在外交部干出点名堂。
有人轻轻敲门,他拉开锁栓,来人闪进屋中,长揖而贺。
“恭喜宗武兄晋升之喜。”
“佛海兄,”高宗武惊喜地招呼着。
橙黄色的灯光下,来客一袭长衫,衣履飘扬,很有名士风味。
“嘘,我这是偷着出来的,今天轮我当值。看到老头子已经睡了,布雷先生又在熬夜赶文章,托他照应一下,专程来为宗武兄贺喜。”
高宗武抚掌一笑:
“人人都说天下近臣有百般威风,原来也有百般约束,比不上我等撇开公事就是自由之身。”
来人正是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他也是日本留学生,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只不过他的资格老得多,当其在政坛上出头露面的时候,高宗武还是个弱冠少年。
周佛海也是个舞文弄墨的好手,来往的人当中不乏名流学者,因此得与高宗武相识,并知此人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心中已亲近了几分。加之双方观点相似,气味相投,不禁更惺惺相惜,有了相互借重之意,来往也就日趋频繁。因此,当听到高宗武升迁的消息,立即亲身来贺。
高宗武打开酒柜,拿出一瓶日本清酒,倒入杯中,递与周佛海。
周佛海呷上一口,感慨长吁。
高宗武打趣说:
“怎么样,似曾相识,有所回味。”
“当年在日本留学,确实曾与此君为友。”周佛海打量着杯中酒回忆说:
“那时我们东京一高的学生最神气,因为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帝大’,自我感觉也特别好。经常戴顶两道白圈的制帽,披一件风衣,脚下登一双木屐,在街上大摇大摆,略略做出一点出格的事,不但警察不去管,一般人还认为可爱,真是宠儿啊。”
“那时我还小,当时也特别羡慕你们。”高宗武深以为然。“佛海兄现在也还是神气啊,亦政亦文,亦官亦儒,又是天子近臣,谁敢小觑。”
“天下人也许都作如是观,但宗武兄却不该这样讲。”
高宗武不解。
“天下人为宗武兄贺喜,乃贺有形之喜;我为宗武兄贺喜,贺的却是无形之喜。”
“这有形之喜我明白,这无形之喜又是何来?”
“宗武兄这等聪颖之人难道是装糊涂,这有形之喜自然指的是晋升之事,无形之喜则是宗武兄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在蒋汪两位先生之间游刃有余,同时得到青睐,不致于被一方宠、一方恨呀。这就保证了你仕途通达。”
周佛海说到此,长叹一口气。
“周某在此处就不如宗武兄,与汪先生积怨甚深。”
“佛海兄与汪先生有过节?”高宗武问。
“那时你还未回国,有些情况不清楚。当年广州政府时期,佛海从日本回来不久,少不更事,徒逞意气,与汪先生曾有一场笔战。”
一口气喝干杯中酒,周佛海又为自己倒上一杯,谈兴更浓。
“当年,共党猖獗,赤祸正炽,汪先生也借大旗作虎皮,大唱左派高调,周某看不下去,写了几篇文章有所规劝,未曾想惹恼了汪先生,说了周某许多坏话。”
“汪先生说些什么?”高宗武很有兴趣地追问。
“他骂周某是拆烂污,说我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真不是东西。让人家今后不要再和我周某人不来。”
高宗武心中暗笑,汪精卫这话骂得不错,因此打趣说:“汪先生话是刻薄了一点,但据宗武所知,佛海兄还是中共的元老呢。”
“这倒不错,中共的‘一全’大会,本人就厕身其间,汪先生的臂膀公博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高宗武看看手表,夜已深了,他建议说:
“佛海兄,夜深人静,难得这片刻安闲,你我不如联床夜话,听你说说这段历史。
谈兴正浓的周佛海自然赞成,他也不脱衣服,拉过一床被子,拥床而坐,细说当年。
周佛海的原籍在湖南省沅陵县信平乡窝溪村周家冲,他生于1897年5月29日,其父周夔九,系清末举人,曾入曾国藩湘军,职务为幕僚,且立有军功。周佛海十岁时,父亲就因禁止鸦片毒品,被当地士绅逼着上吊自杀。孤儿寡母,那生活顿呈江河日下之势。
周家虽衰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薄田数亩,除维持生计外,尚有余力供周佛海上学,经过四年的乡塾启蒙教育,他依仗刻苦与聪明,在国学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
命运似乎也对周佛海格外垂怜,几次机遇都恰到好处地照拂到他,15岁时,投考县立小学堂,居然侥幸以第一名考中。考试时的情景颇有戏剧性,他回忆说:
“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才15岁,在乡村一个私塾里读书,第二年民国六年,我们乡下有几个学生,都进城考了高等小学。我的消息很慢,等到考期已过,我才知道,于是请求母亲准许进城运动补考。到了城里探听,知道距发榜的日子,只有三天,绝对不能再考了。我那时非常失望,凑巧那时县政府的教育科长,是我乡下的吕鹤立先生,我便请他写了一封信给小学校长。居然得到允许了。因为这是我一生发轫的起点,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我一个表兄,当时在中学读书,送我去考,补考的只有我一个人,在窗明几净的校长室考的,国文题是《爱国说》,还有两个加法的算术。国文完了卷就做算术。算术的答案,我没有把握,凑巧这时校长不在房间,我的表兄在窗外探头探脑地向内张望,我便把算术答案给他看,他轻轻地由窗外告诉我尾数上少了一个圈,于是我把圈加上,考试就算完了。”
高宗武不禁笑了起来:
“这个圈真是值千金啊,否则你算术分数也是个圈,周佛海也就老死荒村无人识了。”
周佛海点头赞同:
“考虽考了,究竟能不能取,还是一个问题,年岁比我长,学问比我大的人有的是,名额又有限制。谁知放榜那天,我竟中了第一名。真是喜出望外。想来想去,却想不出何以考得第一的理由。总不会校长徇教育科长的情面吧?后来进了学校,听阅卷的国文老师讲,原来我当时虽在乡下私塾,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梁启超的《中国魂》,读得滥熟。我就学他的文笔,把许多新知识,新名词,以及忧时愤世的论调,装入国文试题中。”
高宗武恍然大悟:
“不错,在当时风气未开的小州县,居然出现这样的文章,难怪要独占鳌头。”
“如果说考上县小,使我走出了闭塞的山村,那么留学日本,才是我事业发展的启端。否则,我虽有相当的报负,但如果一辈子在沅陵县那个小城里,充其量也只是混个教书匠,大不了当个县太爷之类的小官僚,也算祖上积了阴德,前世烧了高香了。弄不好,也许穷困潦倒一辈子默默无闻。”
他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
“其实,我当时已近乎失望,从客观事实看,上进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实在没有,出洋?想都不敢想,即使看见县里有一两个人进了北京大学,也只是徒然羡慕,犹如隔世为人。”
周佛海至今还记得那场滂沱大雨,将他阻于对岸,望河兴叹。已经4天了,他因回家探亲而无法进城返校。殊不知,在这4天里,他一生的命运已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来,周佛海有位同班同学,也是好朋友,因他哥哥在东京上学,一年前也跟着东渡到日本。他来信说东京生活费用并不高,每年也只需万余元而已。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他建议周佛海也去东京上学。这封信在学校引起反响,校长育才急迫,决定凑钱选派几个尖子生去东京。周佛海成绩出众,又肯用功,自然是入选者。
回到学校后的周佛海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恍然如身在梦中,这种体会一生都忘不了。
“也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开始研究马克思学说的。那时年轻,有冲动,特别是俄国革命的刺激,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因此受到了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注意。1920年,那时我已考上‘京大’,暑假回国,在上海和陈独秀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会面,讨论组织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我又利用暑假回国,参加了中共一大。现在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当时也是代表,说起来我们还是湖南老乡。”
“听说陈公博也参加了?”
“他是广东代表,记得开会期间,忽然法国巡捕冲了进来,问为什么开会。大家都说是北大学生。一个中国巡捕指着公博,说他是日本人,原来公博总自信他的北京话很地道,可在别人听来,就像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解释良久,才证明他是广东人。侥幸巡捕没有搜身,在他们的口袋里,就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班房的道理。”
“那公博和你为什么都退出了中共?”
“其实公博当时对政治并没有热情,‘五·四’时,他正在北大念书,那样的一场大运动他都无动于衷,经常钻到新世界听梨花大鼓和泡澡堂子。后来他回广州,受同学谭平山影响,涉及政治,编辑《广东群报》,受到陈独秀的注意,酝酿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中共‘一大’时,由于会场上出现争论,平心而讲,在一个党初建时发生意见分岐是正常的事,但公博却看不下去,那原先的热情,顿时降到冰点。这就是他退出中共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我退出中共,则是要以后的研究中开始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产生怀疑并终至反对,我在1919年就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阶级斗争》的文章,不承认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和必要。后来我到广州,当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面也表示过这种主张。我说:共产党的任务是中国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此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抵抗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
“你这番话鲍罗廷肯定听不入耳。”高宗武说。
“何止听不入耳,简直是雷霆震怒。我当时也年轻气盛,当场顶撞起来。后来周恩来找我谈过多次,劝我回转思想。但吾心已冷,吾意已定,所以断然拒绝。到1924年9月,中共始作出决定,将我开除出党。”
其实,周佛海背离中共,既有思想理论方面的分岐,也有其他原因,经济问题即为其中之一。他从日本回国后,受戴季陶之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50元。按规定,凡是兼职的共产党员,应该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缴纳党费。他的妻子杨淑慧打起小算盘,她劝周佛海:
“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过去,我嫁给你一个穷学生,每月只能靠75元官费养活。现在日子刚宽裕一点,又要将这辛苦挣来的钱交出去,这党有什么干头,不如退了吧。”
周佛海深以为是,只不过他不能公开这一理由,只能借题发挥。
“所以汪先生因为佛海有这段加入中共的历史,才有这番令人痛苦锥心的嘲骂。”周佛海又将话题折了回来。
“以佛海兄口舌之利,自然会还以颜色。”
“就是,我也反唇相讥,回敬他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莫要和这种人共事。”
高宗武皱起眉头,批评说:
“说什么先生也是党国元勋、前辈,这样对骂似有不妥。”
“周某也深悔当年的孟浪,得罪人太重,恐汪先生不见谅于我。”
“可是据宗武观察,你们现在的关系还算融洽,佛海兄在江苏任教育厅长时,对汪先生主持的行政院及教育部的指示不是奉命唯谨吗?”
“你不知内情,蒋先生汪先生长时间的对立,必然产生深深的隔阂,佛海一向是作为蒋先生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现在蒋汪合作,佛海受命与汪先生接近,就是蒋汪合作的一种表示,否则佛海也不敢这样无所顾忌地与汪先生来往。蒋先生为人你大概也有耳闻,是最恨吃里扒外的。”
周佛海看看表,已快天明了,他边起身边接着说:
“虽然受命所为,但佛海与汪先生几次接触,反而顿生亲近之感。汪先生对国内国外形势的看法,尤令人信服,佛海也深以为然。首先在对日关系上,主张中国与日本只应为友,不应为敌,冤仇宜解不宜结,力主与日本妥协,防止战争发生,第二在国共关系上,反对围剿中共,实行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些都是精辟之论。宗武兄与汪先生有僚属之谊,当将周某这片景仰表呈于汪先生面前,则感激不尽。”
高宗武何等精明之人,这点意思当然早就清楚,因此痛快地答应:
“宗武当竭力消弥佛海兄与汪先生之间芥蒂,化干戈为玉帛。现在东方已即白,佛海兄还要赶回当值,容今后回拜府上,以谢今日之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