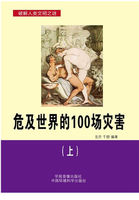蒋介石挤走了汪精卫,惹恼了一位自称侠士的陈公博。后来在汪精卫的阵营中,陈始终是汪最忠实的追随者,是汪的一条臂膀,是汪的股肱之臣。
陈公博夸赞自己:重承诺,轻生死,行侠仗义,据说他这份倔强,乃出自血统的遗传。
他的父亲陈志美,少年厕身行伍,曾与太平天国军队交过手,一刀一枪搏出了功名,官至广西提督,戴起了头品顶戴,穿上了御赐黄马褂,一名汉人武官,混到这个份上确属不容易。
但陈志美却不是大清朝的忠臣,早年在军旅,已秘密加入三合会。此会宗旨,寓有反清复明之意。陈志美自认为堂堂汉胄,不甘委为清奴。光大汉室,是他的心愿。因此,退隐后,依然联络会党,聚集力量,三山五岳的好汉,江湖上的游侠,几乎在他府上不断。
作为将门之后,陈公博念书之余,当然也驰马舞剑,打拳抡棒,虽算不上武艺超群,但意气纵横,向往的是江湖上那种义薄云天,快意恩仇的淋漓抒发。因此,还在少年,他就参加了父亲从事的秘密反清活动。后来事败而逃。流亡途中,长歌当哭,吟曰:
十年须记取,横剑跃中原。
孤愤之气,如触如摸。
就在陈公博逃亡途中,他的父亲遭到清军的追捕,陈志美被擒的一幕很具悲壮色彩。原来他看到清军的追剿部队已逼近,自己纠合的党羽势单力孤,根本不足以抗衡。为避免伤亡,将队伍全数遣散。自己严整衣冠,于龙王庙当堂正色而坐,面对清军统领朱福全,呵斥曰:“此次行动乃余个人所为。与他人无涉,不得滥杀无辜。”
陈志美被押回广州,两广总督张人骏给他定了个“斩监候”罪名,只等秋天处决。幸亏此时清廷的兵部尚书铁良早年与陈志美有杯酒之谊,才把“斩监候”改为终身监禁,关押在南海县的监狱里。
江湖义为先。陈志美孤身被擒,取义舍生之举,在当时引起多少人敬佩,陈公博听了这段故事也激动不已,热泪滂沱。但他却取其形忘其实,只追求轰动的震撼人心的表现形式,而舍弃了“义”的内涵。在他的思想行动中。留下的是那份带有浓郁江湖色彩的不分青红,不问皂白,不辨是非的“义气”,任性浮嚣,不计利害。
陈公博自然也知道自己的性格弱点,是不适宜从事政治的。因此,宣称他做梦也不想搞政治,不但对政治没有兴趣,而且素来就讨厌它。可却一生偏与政治有缘,脱不开这个圈子,为什么呢?他仍然归于自己的天性:
“谁叫我生就打抱不平的天性呢?少年时代跟着父亲闹革命,自己何尝有见地,有主张,不过看见满洲人统治了中国,故而要打抑不平罢了。1925年由美回国,何尝想从事政治,只见国民党局促一隅,一般所谓老同志的,都避义如浼,袖手不顾。故而要打抱不平罢了。对于反蒋,我何尝想两次树起大旗作急先锋,可是看见蒋先生阴鸷谲悍,要硬嘣嘣地抢领袖,故而要打抱不平罢了。”
陈公博对待汪精卫,真正够得上“义气”二字,但这却带有江湖味,“中山舰事件”中,他是同情汪精卫的,但他的思想当时并非定型,仍左右摇摆。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却又同时对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表示忧虑、不满,甚至指责、限制。他同情汪精卫,只是基于汪对他有知遇之恩:他当年去美国留学,是汪精卫通过广东政府给予信任、支持。江湖上讲究的是知恩报恩,有仇报仇。所以,“中山舰事件”一爆发,他就来到汪精卫家,出谋划策。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主动请缨,通知谭延闿和朱培德的第二军第三军,严防事态进一步扩大。
陈公博尽管未能挽回汪精卫的失势,但他对汪精卫的忠诚却没有改变,汪精卫离开广州后,蒋介石也曾拉拢过他,大致是北伐军1926年8月围攻武昌期间,他派人请来了陈公博。
“公博先生,请坐。”蒋介石亲手递来新沏的茶,态度异常客气,一般人是得不到如此“殊荣”的。
陈公博不是受宠若惊的人,他接过茶,淡淡一笑:
“蒋先生找我来,可不是专为喝茶聊天的。”
“是有一件事问问你,汪先生去国外后可有什么消息?”
“无非是琐屑之事,蒋先生如爱听,公博悉数言之。”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
“许多事也未必琐屑,据说汪先生想回国,国内也有不少人欲他回国。可是否?”
蒋介石是有这份担心,最近的政治空气对他不利,一些国民党大员和前方将领对他独断专行的作风不满,因此一股“迎汪反蒋”之风正酝酿。
“汪先生真要回来,你以为怎样?”蒋介石又追问一句。
“汪先生回来,如果于革命有益的,自然赞成他回来,于革命没有什么利益,暂时住在国外也好。”陈公博依然模棱两可地回答。可是胸中那股不平之气已悄然升起。
蒋介石明显不满意陈公博的态度,脸沉了下来。态度也有点异样。
“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如果大家都要汪先生回来,我便走开;如果大家要我不走,汪先生不能回来!”
“到底蒋先生和汪先生有什么过不去呢?”陈公博反问。
“汪先生要谋害我,你不知道吗?汪先生是国民政府主席,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我不满意,免我职好了,杀我也好了,不应该用阴谋害我。”
陈公博终于忍不住大声回答:
“蒋先生讲的还是中山舰事件,这事真是太骇人听闻了。在广州当日,没有蒋先生,汪先生一介书生,能有何作为,又如何能统一广东,汪先生要杀蒋先生,无异于自毁长城,是自杀行为。因此这事我不敢相信。但今日蒋先生又亲口对我说,又不能不令我相信。我现在要务缠身,分身乏术,惟望蒋先生解除我本兼各职,我将天涯海角去寻汪先生,落实此事。假如汪先生要杀蒋先生的话,头一个反对汪精卫的就是我;假如没有的话,我劝两位先生还是精诚合作。现在形势已经够复杂了,倘若再这样下去,前途真太悲观了。”陈公博一时太激动,声音露了凄怆,并且由激越而陡变为哽咽。
他这番话,无异表白了自己的态度,蒋介石内心中就此与陈公博划了一道界限,他草草结束了这次谈话。
从此以后,陈公博将自己与汪精卫捆扎在一起,宁汉分裂,他是汉方政府的显赫要人,是汪在政治上最坚定的支持者。“宁汉合流”后,他又作为汪精卫的代表南下广州,打出“拥护汪党”的招牌,为汪精卫夺取广东根据地卖力卖命。他创办《革命评论》,建立“改组派”,厕身军阀混战,闹得蒋介石也焦头烂额。
但是,陈公博也有彷徨的时候,蒋汪争斗,每逢相持不下或处境困难,汪精卫总是一走了之,剩下的摊子就由陈公博来收拾,他对此也有不满,特别是随着一连串的政治投机和政治冒险失败以后,他不由地感到心灰意冷和厌倦,想就此退出政治的漩涡,抽身世外。这种洁身自好的想法固不可取,较之继续官场上的那种倾轧要干净清高得多。可当他每逢下这样决心的时候,总禁不住汪精卫、陈璧君的抚慰、劝激。“为人子者孝,为人臣者忠。”他自己也长叹,送佛上西天,既然跟定了汪精卫,总不能就此一走了之吧。
1932年的元旦,蒋介石是在他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镇度过的。前几天他刚宣布下野,从石头城悄然而隐。
此番来到奉化老家,就是在静观风向,筹思对策,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出山。
蒋介石的对策依然是屡试不爽的“各个击破”,其具体办法就是“联汪抑胡”
因“廖案”而被挤走的胡汉民在政坛上消沉了几年后又不甘寂寞了,于国门几出几进,于政坛几沉几浮,于蒋介石几分几合,数个回合斗下来,却总占不了上风,最后竟因为“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软禁在汤山,国民党的老前辈沦为了“阶下囚”。
胡汉民这一怒非同小可,此次丢的面子可比五年前因廖案受嫌疑还要严重得多,内心中不禁暗暗发誓,此生绝不与蒋氏并立天下。他对蒋介石已实实在在伤透了心。
蒋介石这手也有欠审慎,胡汉民之地位声望,岂是轻易动摇的,更不能贸然采取这种粗暴的做法。因此,此事一出,在全国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国内及海外华侨纷纷来电询问事情真象或谴责蒋介石暴行,“广东王”陈济棠还乘机在广州欣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并形成了宁粤对立的局面。直到“9.18”事变,双方迫于国内舆论压力,互作让步,胡汉民才最终获释,但与蒋介石誓不两立的态度却没有丝毫改变。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掂量一番后,蒋介石觉得这文章还得在汪精卫身上做,他已经吃透此人心思,反复无常,为“权”是图,不妨先抛出诱饵,让出甜头,惑其上钩。
蒋介石是舍得下血本的,这诱饵着实吸引人,他放出风来:
“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需得一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本党中兴,非汪莫属。”这消息必定会传到汪精卫耳中,但不知汪的反应如何,最担心的就是那个精明过人的陈公博看出破绽,蒋介石不无担心。
自“中山舰事件”至今,屈指一算,已6个年头,这6年里,汪精卫酸甜苦辣,百味俱尝。1927年4月,宁汉对立,汪精卫再度出山,却很快改变政治态度,继宁方“4.12”反革命政变后,发动了“7.15”分共行动。宁汉终于合流。
蒋介石立即抓住了这一机遇,打出“联汪反桂”牌,让宋子文携其亲笔信去广州与汪联络,大施离间计,说广东的李济深是广西人,与桂系的李宗仁关系密切,血比水浓,要汪精卫设法将李济深赶出广东,形成广州汪之天下。果然,汪精卫怦然心动,蒋介石也“热心”予以配合,从日本回国后,就邀请汪、李去上海,协部将黄琪翔兵变广州,将自己的根据地拱手交汪。
其实,汪精卫这样做得不偿失,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等,或通电,或演讲,群起指责,找到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门上,要求绑架汪精卫,以出口恶气。李济深更是恨之入骨,不惜写信与一向不和的蒋介石,请求出兵讨伐。蒋介石做得也绝,居然将这信拿给了汪氏夫妇,他这不是买好,而是存心看他们的笑话。
果然,汪精卫、陈壁君一看到李济深的信,不由得愧悔万分,原本是自己的同盟者,却被蒋介石拆成了怨家对头。夫妻相对无言,惟以泪洗面。
还有让汪精卫吃惊的事,陈公博也为此恨透了蒋介石,他说:
“广州驱李之役,蒋先生是一个有力的主动人,我到上海,才知道李济深回粤打我们时,蒋先生又给了他三十万元作打倒我们的军费。唉!蒋先生太聪明,太现实了,你为着洗刷,我自然不好加以批评,但政治道德毕竟是这样的吗?”
汪精卫就这样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尽管他在这以后,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殚精竭虑,几番努力,可是与蒋介石斗的时间愈长,他就愈没有把握,愈失去信心。屡屡败北的现实,已让他有技不如人之感了。
尽管力有未逮,但心却不甘,每逢失望涌上心头,他更是满腔凄楚,心中也愈益痛恨蒋介石。大志难酬,也实在让人怅然难乐。
陈璧君却突然神彩飞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手里扬起一张报纸。
“老蒋将胡汉民囚在了汤山,广东陈济棠扯旗反蒋呢。”
汪精卫沮丧的神态一扫而光。“胡汉民也算领教了蒋介石的毒辣,想当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谁都知道那是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胡某人却前去帮腔,做了一任主席。如今还是兔死狗烹,自食苦果。”
陈璧君在旁边埋怨说:
“还提过去的不快干什么?你们俩人还不都是上了那个人的当。如今还不联合起来,以你们在党内的地位、资历,还是能够与他一争长短的。”
汪精卫点点头:
“这个我懂,刚才只是出口闷气。现在我就拟稿,你给我送出去,要尽早见报。”
写什么样的文章汪精卫都得心应手,何况这是抒积年之郁闷,吐胸中之仇结,因此谴责蒋介石的行为义形于色,口气刻薄而尖利。他骂道:
“自从民国以来,自从袁世凯以至蒋中正,彻头彻尾的只是武人专政。但是以前的武人专政,老老实实便是武人专政罢了。惟有到了蒋中正,他的武人专政却加了好些花样。”
“即以此次之事为证,蒋中正如果要问胡汉民的罪,可以在中央党部里问,可以在国民政府里问,为什么半夜三更的在私宅里大排筵席的时候,24名驳壳卫队,立刻动手,将胡汉民监押起来,拘关到汤山去?这种手段,是触犯刑法第几十几条?尤其是普通宪法第二章规定人民权利义务里头所绝对不许的。”
骂完蒋介石,他又表示与胡汉民和解,拍着胸脯讲:
“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却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抱在一起跳。”
这些话传到胡汉民耳中,他频频摇头。
“汪兆铭我知之甚深,性格反复无常,不可信之。不过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只能姑且如此。但对他手下人马,尤其是陈公博,须一律挡驾,去皮存骨,汪兆铭一人也就难掀风浪了。”
汪精卫当然不能让胡汉民“去皮存骨”,仅保留他一个光杆司令。折腾了这么多年,好容易有一个出头日子,岂能这样被别人轻易甩掉。
号称汪精卫左右手的顾孟余告诉汪精卫,蒋氏已散出口风,希望汪能出来收拾局面。
“是吗?”汪精卫抬起头来,很感兴趣地问。
“确属事实,宋子文也这样讲: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汪精卫兴奋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双手紧搓。
“汪先生,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靠中央大军阀。只要改变在野地位,与蒋介石分享天下,再从容布置,局面仍有可为。”顾孟余继续怂恿说。
“唔,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汪精卫连连点头。这样的大事,自然免不了要和陈公博商量。未料到汪精卫刚一开口,就遭到了坚决反对。
“但汪先生自认与蒋先生合作会得益吗?你们交往的历史比我长,对他的了解也比我深,但我却冒昧直言,以蒋先生与胡先生比较,后者虽说偏狭自负,但毕竟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比蒋先生那样无所不用其极,更令人担心。”
汪精卫继续劝说:
“粤方难道就比南京方面可靠吗?你要知道,他们的合作条件就是只欢迎我一个人,要去皮存骨,首先要将你公博剔除。”
陈公博激动起来:
“汪先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跟着您,您该知道我的为人。难道我仅是为了做官?如果这样,我就不反蒋了。民国15年北伐,蒋先生占领南昌,就委我以江西省政府组织部长,不能说权倾天下,也可以说借重一时。这些我都没在乎,可以说弃之如敝履。你汪先生在武汉一声招呼,公博则义无反顾,有一丝恋栈的心理吗?”
汪精卫连忙安慰:
“你的为人我很清楚,但我不能不替别人考虑,孟余、乃光他们对联蒋都很热心。”
陈公博长叹一声,不再劝阻了,如果挡了别人的官路,是会遭到怨恨的。
从此,蒋汪第三次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他们联手一致,促使孙科内阁下台。1932年1月中旬,汪蒋经过杭州烟霞洞密谈,联袂入京,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兼内政部长,并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主持政务;蒋介石则专任军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表面上似乎双驾马车,平分秋色了。
其实不然,汪精卫自从1932年进南京,就没有一天扬眉吐气的日子,守着行政院那一摊子,差不多成了蒋介石的幕僚。
汪精卫时有牢骚,蒋介石心理就更不平衡了。他听到这些怨言后,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地痛骂:
“娘希匹,还不知足,一半天下都给了他们,还以为是广东政府时期,莫不成将林子超的国府主席连带我这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帽子都一齐交给他才甘心。”
“汪先生的胃口也太大了,算一算他们的摊子也铺得不小,铁道部、实业部都肥得流油,分别归了顾孟余、陈公博,连次长也是他们的人,由曾仲鸣、郭春涛担任。行政院的秘书长是他的姻亲褚民谊;唐有壬、彭学沛、谷正纲、陈树人这些改组派成员或任外交、内政等部次长,或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和主任,真是‘冠盖满京华’,招摇过市,连我们不少的同志都看了眼馋、生气,难不成这几年南征北讨,打下来的江山让他们坐?”陈立夫在旁边不失时机地煽动着,蒋介石的肝火更旺了。
“让他们干!我们让贤!看看汪兆铭有多大能量,将这个国家治好。”
陈立夫知道这是气话,让蒋介石离开权力,无异是让鱼跳上岸。
蒋介石开始感到他把汪精卫估量低了。虽然每次斗争,他都稳操胜券,但汪精卫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兴风作浪。国内反蒋派只要一有动作,也就自然借助和抬出汪精卫“党国元老”的招牌与他抗衡。斗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不得不把他拉进来分一杯羹,这口气实在难咽。
这个机会终于在抗战爆发后被他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