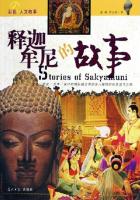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人面桃花。每每读及此诗,遗憾之余,竟是激动。
一句“人面桃花”,唐代女子无与伦比的华丽妆容宛在眼前。崔护廿八个字,记录的是一年的思念,与几个世纪的绝代风华。
唐女爱浓妆。每个清晨,女子们端坐于镜前,敷铅华、抹胭脂、描黛眉、贴花钿、覆额黄、点妆靥、勾斜红、染口脂……妆容环节极为精致繁复,妆容出来的效果,也极为艳异。日复一日,她们不厌其烦——这是自然,你若细究唐代妆容的每个环节,你会发现,唐女是古代鲜有的自私派。“女为悦己者容”,画中这一枝桃花开得清新淡雅,但崔护那一枝桃花,
我想一定艳若流霞。
字到了唐朝须重新排列,排列为“女容者,为悦己”。
那么娱人呢?聪明利落的唐女不做这样亏本的买卖,人生短暂,必先娱己。伴侣不在家中,也要精心打扮,对于唐女来说:
描眉贴花,这不是讨好谁谁谁的把戏,而是乐趣无限的游戏。所以,她们才有热情,玩出其他朝代的女子玩不出的创意。
1.铅华凝
郑史,唐朝国子博士,官至刺史,赏遍世间风光。而与相好的官妓分别,郑史劈头怀想的不是别样,竟是“最爱铅华薄薄妆”。
能让阅尽风光的郑史念念不忘,铅华妆扮出的风情我们大致可以想象。
东方女性一向追求白色肌肤,这种审美趣味终于在唐朝登峰造极。唐代女子化妆,第一步便是傅粉,但绝不是郑史所谓的“薄薄妆”,她们会用厚厚一层白色粉末覆盖整个面部,掩饰任何细微瑕疵,让脸庞如瓷器般光洁。这种稍嫌夸张的妆容方式,东瀛艺伎直到今天依然在使用,面孔的白因和服的斑斓,成为最艳丽的雪。
敷面的白色粉末,中间包含了铅、锡、铝、锌等,而最主要的成份为铅,因此这种妆粉又被称为“铅华”。远在铁血时代的战国,妇人们便开始傅粉。除了铅华,各个朝代还有自己独特的妆粉:六朝人混合米粉、胡粉,再掺入些许葵花子汁,制成“紫粉”;宋人将益母草、蚌粉、壳麝等按一定比例细细调合,制成“玉女桃花粉”;明人则是选取饱满的紫茉莉花种子,淘洗、蒸熟后制成“珍珠粉”,或是以玉簪花为主料制成“玉簪粉”……制粉方式各异,但有一点相同,那便是:这些妆粉,从配料到粉名,无一不温和。
唐人制粉却是例外,除了常规制粉材料,他们还特地掺入林林总总奇异而馥郁的西域香料,最后制得的妆粉,挑上一星半点便使人双颊生香。熙熙攘攘的长安或洛阳,傅粉女郎轻轻走过大街小巷,各种香气便在空气中碰撞。所以,唐朝遍街都是丁香一般芬芳的姑娘,但她们没有太息一般的眼光,她们不懂太息,她们个个都浓烈得让人不能遗忘。
这种奇香袭人的妆粉,名字也起得张扬,叫做“迎蝶粉”——想想也是,唐朝女子不会喜欢乖巧绵软的“桃花粉”、“玉簪粉”。
“迎蝶”二字或许不够高雅,但生机勃勃、热血贲张,有了这,谁还稀罕温良恭俭让?
2.胭脂缘
傅粉是妆容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涂抹胭脂。
涂抹胭脂,等于在脸上作画。唐朝女子对胭脂的运用,绝非工笔花鸟式的,一笔一划推敲,逐色逐寸雕琢;她们完全是泼墨山水式的做派,大开大阖,恨不能一挥手便染出一个盛唐。胭脂不是廉价玩意,但她们才不吝惜,她们把胭脂涂满面颊、涂满眼睑,甚至涂满耳朵,总之要将胭脂用个痛快,将红色进行到底。
王昌龄形容女子“芙蓉向脸两边开”,放在今日,这是艺术夸张;放在唐朝,这说的就是寻常景象。
那个时代对红妆的偏爱,从《开元天宝遗事》中关于杨贵妃的两则轶闻便可见一斑:一则记述杨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挥泪作别,恰逢天寒,泪珠瞬时结为红冰;另一则记述杨贵妃用巾帕拭汗,巾帕被汗染红,色如桃花,美艳动人。能够形成红泪与红汗,脸上涂抹了多少胭脂自不待言。而唐代诗人王建更以猎奇的口吻描写过宫女卸妆的情态——“归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里泼红泥”,卸妆能卸下一盆红泥,可见每次化妆胭脂耗费之巨。若有人对此表示舍不得,酷爱红妆的唐朝女子大概会用《古诗十九首》中的一句来回答吧:“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人生能得几回浓墨重彩?有机会的时候,请一定尽兴。
“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乃是唐代宫怨诗的代表作,暂时撇开诗中凄恻寂寥的心情,想想三千胭脂面,聚若红云,该是多么香艳的风景?但这三千胭脂面,可不是千人一面。有唐一代的创新精神,在胭脂面上发挥了个彻底:傅粉之后着重在双颊上浓妆艳抹,面色如同醉酒,这是“酒晕妆”;雪腮薄施胭脂,将面孔晕染成春日里的花瓣,这是“桃花妆”;用浅朱作底,再施以铅华,红里透粉,满面霞光潋滟,这是“飞霞妆”……花样之多,叫人啧啧称奇。
唐初开始风行红妆,但进入中晚唐之后,别的一些妆容逐渐。画中仕女眉形阔而短,这种眉形正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极为盛行的桂叶眉,也正是“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中所写的“蛾眉”。
受到追捧,比如“泪妆”——不用胭脂,仅仅在两颊或眼角涂上些许素粉,作此妆容的妇人看起来泪光盈盈、弱质芊芊,美丽却哀愁。还有一种“三白妆”,脸上不作其他修饰,仅仅涂白前额、鼻子、下巴三个部位,虽说妆容的最终效果是提升了面部的立体感,但比起华美妖冶的红妆来,难免显得凄凉单薄。
从红妆到泪妆,唐朝也从盛世走向末路:一个时代的风华,首先在女子的脸庞盛开,末了,也首先在女子的脸庞凋谢下来。
3.眉山远
唐玄宗赐给杨氏姐妹的脂粉费,每年高达百万两白银。这一数据,除了证明唐玄宗迷恋女色、挥霍无度诸如此类的道德事实之外,也证明了唐人极好浓妆。不过,在满朝红妆之中,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却是例外,独她“却嫌脂粉污颜色”,不染铅华。
但是特立独行如她,朝见至尊时也须“淡扫蛾眉”,由此可见眉妆在唐代女子妆容中所占的分量。
眉本黑色,在唐时,绿眉却是主流。万楚不无赞许地写道“眉黛夺将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将眉黛与碧绿的萱草作比;韩偓一句“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更是写尽翠眉的宛转与风流。颊红、脸白、眉翠,相映不说成趣,至少足够华丽。
而杨贵妃不愿随俗,逆翠眉潮流而动,别出心裁地用墨将眉染黑,这种做法立刻引发了“时尚地震”。今天看来,黑眉再正常不过,但放在当时,它几乎可以登上唐朝美妆杂志的年度头条。徐凝就用诗句记录了这件时尚史上的盛事:“一旦新妆抛旧样,六宫争画黑烟眉。”
唐女对眉妆的不懈追求,不但体现在眉色的创新上,更体现在眉形的层出不穷上。许多女子甚至每天换一种眉形,不厌其烦,乐在其中。唐玄宗曾命人作《十眉图》,记载了当时流行的十种眉形,分别为鸳鸯、小山、五岳、三峰、垂珠、却月、分梢、涵烟、拂云、倒晕。光是记下的便有十种之多,于史无载的更是数不胜数。
《十眉图》今已失传,徒留风雅的眉名供后世想象。而后世。画中梅下所生,正是“眉黛夺将萱草色”
中所提到的萱草。
还真有好事者据此想象,清代徐士俊就作了《十眉谣》,对十种眉形逐个写意,比如:关于小山眉,他说“春山虽小,能起云头。
双眉如许,能载闲愁。山若欲雨,眉亦应语”;关于涵烟眉,他说“汝作烟涵,侬作烟视。回身见郎旋下帘,郎欲抱,侬若烟然”;关于拂云眉,他又说“梦游高唐观,云气正当眉,晓风吹不断”。
《十眉谣》字字曼妙,想象旖旎至此,也就没人追究眉形的真相是什么了。只消跟着徐氏,在脑中勾勒如斯画面:长安月下,灯影明灭,长街上人来人往,涵烟、拂云游走,垂珠、小山争艳,无须再寻找什么温柔乡,温柔乡正卧在女子的眉间。
4.花钿醉
“腻如云母轻如粉,艳胜香黄薄胜蝉。点绿斜蒿新叶嫩,添红石竹晚花鲜。鸳鸯比翼人初贴,蛱蝶重飞样未传。况复萧郎有情思,可怜春日镜台前。”王建这首诗,即使不解其意,也深觉美丽。轻如粉,薄胜蝉,新叶嫩,晚花鲜,你以为他写的是某个“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佳人?不,他写的是花钿。
贴花钿,唐代女子最为时髦的妆容方式,妇人们将各种色泽艳美的物料,加工制成各种形状的薄片,然后把薄片粘在额头眉间,甚或两颊。这些薄片就是花钿,也被称作花子或媚子。花钿色彩缤纷,形态也从简单的圆点、水滴状、月牙状到复杂的祥云形、鸟兽形、石榴花形,不一而足。只有你想不到的花纹,没有唐女做不出的式样。而李康成诗“翠钿红袖水中央,青荷莲子杂衣香”
中的翠钿,温庭筠词“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中的黄子,都是花钿的经典款,为唐女所喜。
研究花钿的取材是件极有意思的事情。你会发现,金箔、贝壳、鱼鳞、鱼鳃骨、黑光纸、云母片、翠鸟羽毛、茶油花饼,甚至连蜻蜓的翅膀,都可以被唐代女子做成花钿。世间任何一种漂亮的颜色、美好的质感,抑或惊人的光线及氛围,她们都想裁下一角,小心翼翼地种在自己的肌肤上,成为身体的花。这是唐代女子的野心,可爱的野心。
而花钿的由来,大概是千年来最美的传说之一:南朝宋武帝时期,寿阳公主倦卧在含章殿檐下。是日天晴,风起,花落,一朵梅盈盈停于公主额前。轻抬纤手,公主不经意地拂走落梅,眉。画中间的女子眉心精致玲珑的装饰,便是唐女必不可少的化妆品——花钿;而她的唇形正是唐人甚爱的樱桃小口。哪怕唇形阔大,唐女也能用化妆术绘成小口。
心却留下了梅的烙印,洗之不去,清晰可辨。三日之后,那花痕才逐渐消失。梅花不再烙在公主的额头,却烙进了宫人的心头,众人讶异于梅花烙的美丽,纷纷模仿落梅剪裁各种小饰物贴于眉心,这,就是花钿。“梅妆”一词的源头,也就出自这里。
传说负责给我们美感,信史负责给我们答案。考察历史记载,花钿的真正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唐朝佛教盛行,佛像眉间点有白毫,妙相庄严,当时的妇人认为这是一种有福之相,贴花钿其实是对佛像的模仿;另一说唐朝多悍妇,婢妾服侍不周,正室夫人动辄施暴,常常在婢妾脸上留下伤痕,为了掩饰伤痕,婢妾们开始贴花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