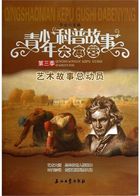“上尉拍着他的肩宽慰他说:“老兄,没事。我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事呢。不过……’我未听到接下来的话,这些已经够我动脑筋想了。
“过了两天,舒尔托少校在海边散步时,我走到他身边说:‘少校,我想对您说件事。’
“他把嘴里的雪茄烟拿在手里,问:‘斯茂,有事吗?’
我对他说:‘先生,如果给你一批珠宝,你是把珠宝交给政府呢,还是交给别人?我晓得有一个地方埋着价值五十万镑的珠宝。可我这个样子,无法把它挖出来,我准备把它交给政府,说不定会给我减刑呢。’
“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双眼紧盯着我,像是要射到我的心里,瞧一瞧我的话是真是假:‘怎么,五十万镑?’
‘是的,先生,价值五十万镑的珠宝。它的主人已经畏罪潜逃,第一个挖出他的人就是这批财宝的主人。’
“他稍微口吃地说:‘这应当给政府,交给政府。’听那口气坚决的成份不多。我晓得,少校已上了我的圈套了。
“于是我又慢吞吞地试探他:‘您说我是不是该将这事报告给总督呢?’
“‘先别这么急,要不你会后悔的。我还是想,斯茂,对我说说这事的经过吧。’
“接下来,我如实地把经过告诉了他,不过为了避免泄露藏宝的地方,我对其中部分作了删改。少校听了我的话,呆站了很久,他的嘴唇一直在微微颤抖,可以看出,他思索这事时思想波动很大。
“他对我说:‘斯茂,这事情非同小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过两天,我再对你谈这件事。’
“两天后,他带着摩斯坦上尉一起提着灯来到我的屋子。
“他说:‘斯茂,摩斯坦上尉很想听听你讲讲这事。’
“我又把原先的话复述了一遍。
“少校听了后,说:‘像是真的,怎么样?还值得冒险吧?’
“摩斯坦上尉点点头,默许了。
“少校说:‘斯茂,我想我们该这样做。我和我的朋友对这件事情认真考虑后,认为这个秘密属于你个人。对于你的财宝,你有权作任何处理。现在的问题是你的条件是什么?倘若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们可以代你办理,至少也会代你查实一下。”说这些话时,他极力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可是他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和贪婪的光泽。
“那时,我极力装出镇定,我的心里其实正在翻江倒海,我对他说:‘要说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一个,你们能帮助我和我的三个朋友恢复人身自由,然后,我们会和你们合作,把宝物的五分之一拿出来作为对你们的报答。’
“‘就五分之一,太少了,这不值得我们冒险。’少校不满意地说。
“‘你想想,每人平均能得五万英镑呢。’
“‘我们没办法答应你的条件,没法让你们逃走。’
“‘这没有什么难的,我都已经想好了。只要你们能从加尔各答或马特拉斯弄来一艘适于航行的小船,这两个地方小快艇和双桅快船多的是,再置备足够的粮食,我们再趁着夜黑上船,到达印度沿海的某个地方,就可以离开这鬼地方。’
“上校说:‘若是就你一个人,那没问题!’
‘不行。我们曾经发过誓,四个人生死都在一起。少一个都不行。’
“他对上尉说:‘你看,摩斯坦,我们尽可以相信他,斯茂对朋友多仗义呀。’
“摩斯坦说:‘这事真有些见不得人。不过干成了能改善咱们的困境。’
“少校说:‘斯茂,在我们答应你的条件之前,我们先确定一下你说的话是否当真。你干脆把藏宝的地点告诉我们,等到定期来船的时候,我顺便到那里找一下。’
“他越是着急想知道,我越是不紧不慢。我说:‘先别急。我得向我那三个朋友问问是否同意这件事,只有我们四个都同意,这事才能继续干下去。’
“‘这叫什么事呢?我们白人订的协议,和那三个黑家伙有什么关系?’上校不屑地说。
“‘黑的也好,蓝的也罢。他们既然和我已发下誓言,我就一定要遵守。’
“等到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把莫郝米特·辛格、埃波德勒·可汗和德斯特·阿克波尔也叫来了。我们再度协商,最后把这事就定下来了。我们给两位军官每人一份阿克拉城的藏宝图,并且标出了藏宝的地方,以便让舒尔托少校到印度顺利找到宝物。他找到宝箱后,先不能带走,得到罗特莱岛接我们,准备快艇和粮食把我们送出去。我原来计划少校立即赶回营地,再由摩斯坦上尉请假去阿克拉城,和我们一块平分那宝物。上尉代表他领取他俩应得的。
所有这些条件都经过我们共同发出庄重的誓言,保证共同遵守,决不背叛。我在灯下又花了一夜功夫画出两张藏宝图,两份上面签上莫郝米特·辛格、埃波德勒·可汗、德斯特·阿克波尔和我四个人的名字。
“先生们,听了我讲这些,你们厌烦了吧。琼斯先生不想让我在这儿,急着要把我送到拘留所吧。我简短地说吧,舒尔托去印度后,再没回来。没过几天,摩斯坦上尉给我们带来了一张从印度开往英国邮船的旅客名单,其中有舒尔托的名字。听说他的伯父给他留下许多遗产,所以他退伍去继承遗产了。他真是卑鄙下流,不但把我们四个人骗了,还欺骗了他的好朋友。不久,正如我们所料,摩斯坦到阿克拉城去查找,珠宝果然没有了。这个家伙把宝物全都拿走了,他一点也没有遵守我们的条件。当时,我脑海里只留下一个念头,就是要报仇,不管方式是否合法。我在那儿惟一想的就是找机会逃跑,找到舒尔托,一定要掐死它。同复仇的念头相比,阿克拉的宝物,在我心里已不显得重要了。
“我的一生曾许下不少的愿望,都尽力地去完成。但是在寻找舒尔托的几年里,我真是历尽艰难。我对你们说过,在安达曼群岛,我学到一点医药知识。一天,岛上的一个生番生了重病,只好到树林里等死,去树林干活的犯人们把他带了回来,他患了热病而卧床不起。那时正好莫顿大夫不在,我尽管知道生番性情凶狠,出于同情心,我还是精心照顾他两个月,他的病逐渐痊愈了。因为这,他对我产生了好感,很少再回树林一次,整日在我的茅屋里呆着。我向他学会了一些土话,这更加深了他对我的那份难得的感情。
“这个原始部落人就是童克,他自己有一个很大的独木船,他的驾船本领特别高。他对我忠心耿耿死心踏地。我察觉到这点后,决定要寻找机会逃跑。我准备让他把船划到一个没人看守的小码头去等着,我上船后连夜逃走。我把这个计划对他说了,嘱咐他准备好船和水,再弄一些椰子、白薯、薯蓣等东西吃。
“诚实可靠的童克,真让我感动,他果然在那天晚上把船划到码头上。很凑巧,一个平时最爱欺负我的狱卒在码头上站岗,我正苦于一直没机会揍他呢,现在老天爷把他送到我面前,让我在逃离前能报仇。当时他背朝着我,挎枪站在海岸上。当时我想用块石头砸烂他的脑袋,可身边一块也找不到。这时我猛地想起我身上有一件最锐利的武器。我趁着夜黑,摸索着解下木腿,往前猛地跳了三下,窜到他身后,猛劲朝他的脑袋砸去,几下子就把他的头骨砸得粉碎。我这木腿上的裂纹,就是我当时行动的有利见证。由于我一只脚失去重心,和他同时摔倒。等我爬起来后,他还纹丝不动。我接着就上了船,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远离了这块土地。童克把所有的财产、兵器和他的神像都搬到船上。其中有一根竹制的长矛,还有用安达曼岛的椰树叶子编成的席子。我就用这做成了桅杆和船帆。我们在海上漫无方向地漂泊。十天后,我们碰见一艘从新加坡开往吉达的客船,船上满载着马来西亚朝圣的香客,把我们救了上去,船上的人都很奇特,不久我们和大家都混熟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们能让我们安静地呆着从不追问我们的来历。
“如果准确地叙述我们的航海经历,恐怕到天亮也说不完。我们从世界的这儿流浪到那儿,就是很难漂泊到伦敦。即使这样,我从未忘记报仇雪恨,就连梦中都无数次梦到追杀他。
三四年前,我回到了英国,在伦敦,我顺利地找到他的住址。接下来的就是想办法知道那箱珠宝是否在他手里,他是不是真的拿走了宝物。在寻找下落的过程中,我同一个一直帮助我的人成了朋友。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的,也决不想牵连别人。过了不久,我得知那批宝物真的在他手里。但是舒尔托太狡猾了,我费尽心力去想法报仇都泡汤了。他家除了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印度仆人外,他雇佣的两个拳击手白天黑夜地守护着他。
“一天,我听说他病重得就要死了,让他就这样死了太便宜他了,我真是好不甘心。我不顾残疾,急冲冲地跑进他的花园,透过窗户,看见舒尔托躺在床上,他的两个儿子站在床边。当时,我真忍受不住要冲进去掐死那个老家伙。正在这时,我发现老舒尔托的下巴猛地往下垂去,这说明他死了,就是盲然地闯进去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那天晚上,我悄悄地溜进他的屋子,搜查了一番,结果关于珠宝的线索一点都没有找到。我愤怒之余,就把标有四个签名的图放到他的胸前,以此作为报仇的标志,日后我会把报了仇的事告诉给我那三个伙伴。他欺骗了我们劫去了我们的财宝,却平平安安地入了天堂,真让人心里气愤。
“打那之后,我在集市或别的一些地方,依靠童克作资本赚点钱维持生计。童克跳战舞吃生肉的能耐,总能使我们收入满满一帽子铜板,几年来,樱沼别墅不时有消息传来,说是他们在庄园内到处挖宝外,再没别的新鲜的事了。最后,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巴瑟洛谬·舒尔托在他的化学实验室屋顶室找到了宝物。若是没有木腿的障碍,我真想爬进窗户里去看个究竟。后来,我又得知屋顶室有个暗门,舒尔托先生每天准时地吃晚饭,我决定让童克帮助我把箱子偷走。我带着一条长绳和童克一同去了樱沼别墅。我把绳子系到他的腰上,他灵巧地和猫一样爬上房进了屋里。没有料到巴瑟洛谬·舒尔托在屋里,童克自作主张,把他给杀了。我顺着绳子爬进去后,他正沾沾自喜地走来走去。我愤怒地用绳子抽打他,骂他是吸血鬼,他才知道自己做了傻事。我把宝箱拿走之前,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张写着四个签名的纸条,表示宝物已归还原主。我先用绳子把箱子绑好,坠到地上,然后我也顺着绳子滑下去,童克把绳子收好,关上窗户,仍由原路爬下来。
“我想要说的就这些了,事先我就准备乘‘曙光’号外逃,我听一个船夫说过,那只快艇的速度惊人。因为这,我对船主史密司讲明只要他能安全地把我们送到大船上,我们会付他一大笔酬金。他并不了解内情,但他也许觉得这事不太正常。我讲的都是真的。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谅解,我觉得说实话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辩护。另外,我要让世人了解舒尔托是怎样卑鄙地欺骗了我们的信任。你们没有对我优待多少,关于他儿子的被害,我没有过失。”
福尔摩斯说:“你的故事挺有意思。这个案子的结局很适当。你在叙述后半段故事时,除了我没考虑到绳子是你带来的之外,和我的推测差不多。可我有点不太明白,童克在作案时,他的毒刺应该全丢了,但后来在船上怎么又吹出一支呢?”
“先生,正像您说的全弄丢了,但是吹管里还剩下一个。”
“啊,真是的,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步呢?”
犯人斯茂又讨好似地问道:“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福尔摩斯摇摇头,说:“没有要问的了,谢谢你讲了这些。”
埃瑟尔尼·琼斯说:“福尔摩斯,我们都知道您是犯罪的鉴定专家,我们应当听从您的教导。可是我有公务在身,还要尽我的职责。
我今天为您和您的朋友已经够通融的了。现在只能将斯茂押回牢里去。两个警长在楼下等着,马车就在外面,对于你们二位的协助我衷心感谢。到开庭的时候,还要请你们出席作证。祝二位晚安。”
琼诺赞·斯茂也说:“祝二位先生晚安。”
警惕性很强的琼斯,在走出屋门时说道:“斯茂,你在前面走。我得注意你别像对待安达曼岛的先生那样,用木腿打我。”
他们走后,我和福尔摩斯静悄悄地抽烟默坐了一会,我说:“这出戏终于结束了,恐怕以后我向你学习的机会要少了,我已同摩斯坦小姐订婚了。”
他表情淡然地哼了一声说:“我早就想到了,请抱歉我不能向你祝贺。”
我有些失望地问他:“你对我的选择感到不满意吗?”
“怎么会呢,我一直认为摩斯坦小姐是我见到的女孩中最可敬最可爱的,她并且会帮助我们这类人的工作。她在这方面是有天赋的,我从她收藏那张阿克拉藏宝的位置图和她父亲的那些文件的事来看,就可以看出。我想爱情是一种情感的事,和我认为最重要的冷静思考是相互矛盾的。我永远不想涉及情感的事,以免影响我的判断力。”
我笑道:“我坚信我的选择会经得住考验,看你,好像有些疲倦了。”
“是有一点,恐怕一周也恢复不过来。”
我说:“真纳闷,怎么一个有时候很懒散的人,会时不时地充满惊人的活力呢?”
他说道:“是这样,我原本就很懒,但同时又很好活动。我时常想到歌德的那句话‘上帝只给你造成了一个人形,原来是体面其外,慵懒其中。’”
接着,他转移话题说:“在尚诺伍德案子中,我怀疑樱沼别墅有一个奸细,他可能就是被琼斯抓捕的印度仆人拉尔·拉奥。无论怎么说功劳都属于琼斯一个人了。”
我不平地说:“这样太不合理了。整个案子是你一个人侦破的,最后,我找到了中意的人,琼斯立了大功,而你又获得什么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我嘛,获得了一次冒险的刺激,不是也很愉快吗。”他说着,满足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