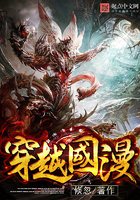“他说:‘这事和堡垒毫无关系,我们要你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们英国人到印度来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吗。我们的目的也是这样。若是你决定和我们合作,我们会把财宝的四分之一给你,这很公平,我们以这把刀向你起誓,锡克教徒从不违背誓言。’
“高个印度人说:“那么你起誓吗?用你父亲的身体,你母亲的名誉和你的宗教信仰起誓,今后绝不做不利于我们的事,不说不利于我们的话。’
“我答道:‘只要堡垒没有危险,我愿意这样起誓。’
“‘我和我的同伴都对你发誓,给你宝物的四分之一。就是四个人平均一人一份。’
“我说:‘可是咱们只有三个人呀。’
“‘还有一份必须给德斯特·阿克波尔。在等候他的这段时间里,我把经过讲给你听听吧。
莫郝米特·辛格,请你到外面等着,他们来了后通知我,。先生,我们信任你,我知道欧洲人恪守诺言。若你是个惯于撒谎的印度人,不管你怎么对神起誓,我们都不会相信你,早把你的尸体扔进河里了。我们相信你们英国人,当然,也相信你们也是信任我们的。还是来说说这个故事吧。
“‘我们印度北部有一个土王,他的领地不大,财产却很多。其中一半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另一半是搜刮来的。他既贪财又小气。叛乱暴发后,他处于两难境地,土王听说杀了不少的人,一面附和着叛军反抗的人,可又怕白人一旦得手,自身会遭不利。反复考虑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把所有的财产一分为二,金银钱币类的都放在宫中的保险柜里;珍贵的珠宝钻石类的,另外放进一个铁箱里。他派一个亲信假扮成商人,准备把它藏到阿克拉堡来。
这样,叛军胜了,他的金银钱币保下了;要是白人胜了呢,他又保住了珠宝钻石。他那边,叛军的势力强大,他只好投靠了叛军。先生,你想想,他的财产是否应当属于忠心于他那个地方的人所有呢。”
“这个被装扮的商人化名叫阿奇麦特,他就在阿克拉城里。今天晚上,他就要到堡里来。他的同伴是我的盟弟德斯特·阿克波尔,他知道这个秘密。
他清楚我们看守这个堡门,就和我们商量好放他从这个堡门进来。一会儿他们就会来了。这地方僻静得很,没人会知道他们的到来,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阿奇麦特这个商人了,土王的财产就要到咱们几个人的手里了。先生,您觉得怎样?’
“在伍斯特尔州,生命被看得极其神圣,但那时到处残杀焚掠,人们就不再那么看重生命了。那时,我真的被那批财宝动心了,对于商人阿奇麦特的生死,我并未放在心上。我脑子里满是今后如何使用这笔财富的念头,想着我这个品行欠佳的人带着大量的金币回归故里时,他们一定会惊呆的。想到这些,我暗暗下了决心。这时埃波德勒·可汗以为我还在考虑呢,又追问我。
“他说:‘先生,你明白,若是指挥官抓住这个人,结果还是被处死,宝物也会充公,谁也甭想搞到一个钱。咱们怎么不可以把他处决了,然后把宝物让咱们四个人平分了。我们会变成有钱人。其实,宝物充公和给了咱们,都是一样。这儿再没有别人,也没有外人看见。我这个主意如何?先生,请您再表态一下,您是与我们合作呢,还是让我们把你当成敌人。’
“我对他说:‘我的人和我的灵魂都和你们站在一起。’
“他把枪还给我,对我说:‘太好了,我相信您和我们会永远遵守许下的诺言。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耐心地等待那两个人的到来。’
“‘德斯特·阿克波尔了解这次的计划吗?’
“‘这都是他一个人谋划出来的。咱们还是和莫郝米特·辛格在外边一块站岗吧。’
“那时正是雨季来临,天上的雨下个不停,片片乌云在空中飘荡。浓重的夜色,肉眼很难看清一箭之外的东西。门前战壕里存着一些积水,有的地方差不多都干了,很容易走过去。我默不作声地在那儿等着那个来送死的人。
“没多久,我看见战壕的对岸有一抹若隐若现的灯光,慢慢地向这边靠近。
“我叫了一声:‘他们来了’
“埃波德勒轻声地说:‘你和往常一样询问他,可别把他吓呆了,然后你把他交给我们,我们会安排他的,他在外面点着灯守着,免得认错了人。’
“这时候一闪一闪的灯光,忽而前进又忽而停住,离我们更近了,可以看清有两个黑影到了战壕的对岸。他们从那边趟水过来,爬上岸后,我压低了嗓音问这两人:“干什么的?”
“他们赶紧回答说是自己人。我举灯靠近他们,见对面是个高个子的印度人,一脸的黑胡子长到腰间,我真没见过真实生活中这么长胡子的人。后边紧跟着他的人胖得出奇,个子很矮,头上裹着大黄包头巾,手里提着一个用围巾包着的包。他像只耗子样钻出洞外,东观西望着,害怕得浑身颤抖,两只手也抖个不停,只有双目亮闪闪地显得精神极度紧张。我想亲手杀掉他,真有些下不了狠心,但那宝物的诱惑力使我定了心神。他瞧见我是白人,立刻欣喜地跑过来。
“他气喘吁吁地说:‘先生,我这个正在逃难的商人阿奇麦特需要您的保护。我从奇布特诺到阿克拉城的路上,总是有人侮辱我,就是因为我以前跟英国军队的关系好。谢天谢地,现在,我和我带的东西终于没有危险了。’
“我问他:‘包里装的什么?’
“他回答:‘箱子里有两件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它不值多少,对我,这可是扔不得的宝贝。我不是来讨饭的,先生,求您让我在这儿暂住两天吧,以后,我会报答您的。’
“我看着他那令人同情的小胖脸,真不忍心杀了他。我真的不敢同他再说了,干脆让他早早见上帝吧。
“我对他说:‘把他送到总部去。’两个印度兵一左一右地把他带进了里面的甬道,那个高个子在后面紧跟着。我未见过像这么被严密包围的人。外面,只留下我一人提着灯笼在站岗。
“这时,从里面传来他们走在长廊上的声音,接着,声音消失了,传来了拼命撕打的声音。
一会儿,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往这边越来越近。我提灯往里一看,大吃一惊,满脸是血的商人正往这边跑,高个子在后面紧追不舍。这商人竟跑得飞快,我明白,若是他逃出我这儿,他就能活命,瞧他那样子,我真动了同情心,但那诱人的财富又让我起了邪恶。他一跑近我,我就用步枪向他的两腿之间狠命抡去,他像是被枪击中了一样向前滚去。还没容他从地上爬起,印度人从后面追上去,两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他未来得及哼一声,躺在地上不动了。可能我那一绊他就昏死过去了。先生们,不管这对我有没有好处,我照实说了。”
说到这儿,他用那双戴着手铐的手接过递给他的加水威士忌。我们从他叙述这事时不在乎的神情里,可以看出这人凶残的本性。无论对他用尽什么刑罚,也不会对他产生同情心。歇洛克·福尔摩斯和琼斯,坐在藤椅上,双手搭着膝盖。他俩对斯茂都不怎么喜欢。斯茂可能看出了我们的想法,他在继续往下说时,声音和动作带着不服输的样子。
他说:“我知道,那事是不能做的,可是我想说,在当时的形势下,谁愿意丢掉性命而不要那宝物呢?他一过来,就注定我同他必须有一个得死,若是他逃跑了,结局是我们四个都得抓起来,会被军事法庭处以枪决。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罚很严。
“接着我和埃波德勒·可汗、德斯特·阿克波尔三个人抬着死尸来到了里面,别看这个人不高,分量却挺重。莫郝米特·辛格在外边放哨。我们走过一条弯曲的甬道,穿过空荡荡大厅,走到大厅角落里一个陷下去的大坑,算是他的归宿吧。这地方我们早已找好,它离着堡门很远。
我们把死者抬进坑里,埋上碎砖。一切都收拾利落后,我们就去看宝物去了。
“那个铁箱就放在刚才死者躺过的地方,也就是你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在箱子刻花的柄上,挂着一把钥匙,它用丝线系着。打开箱子,在灯光映照下,五光十色的珠宝耀眼极了,真和我想象的一样,仿佛我在波舒尔童年时读过的故事一样。这么诱人的珠宝,真让我们过足了眼瘾。当然我们没忘给珠宝列了一张清单。箱内有143颗上等钻石、97块上等翡翠、170块红宝石(包括小块的)、40块红玉、210块青玉、61块玛瑙。其中有一块名叫大摩克尔的钻石号称世界第二大。剩下的是些数不清的绿玉、纹玛瑙、猫眼石、土耳其玉和我叫不出名字的宝石,后来我慢慢把它们认全了。箱子下面是三百颗上好珍珠。其中有十二颗珍珠串成了一条珍珠项链。那天我从樱沼别墅拿回箱子后,仔细查找了一番,发现那串项链不见了。
“我们把珠宝清点后放回箱里,又拿到堡外给莫郝米特·辛格看了一遍,我们又重新郑重地宣誓:要团结一致严守秘密。我们决定先把箱子藏起来,等局势稳定了,再拿出来平分。这批珠宝极贵重,若是带在身边很不安全,容易被别人怀疑。我们当时也找不到隐藏的地方,于是我们把箱子搬到埋着尸体的那间屋子里,从最完整的一面墙上卸下几块砖来,把宝箱放了进去,用砖封好。我们默默地用心记住了藏宝的地方。第二天,我给每人画了一张地图,在上面签上我们四个人的名字,作为我们起誓的标记:从此以后,我们的一举一动全要代表四个人的利益,不得私自独吞。先生,我可以对天起誓,我从未做过不利于我们四个人的事。
“后来,印度暴乱的最后结果怎样,您们也知道了。威尔逊占领了特里,考利爵士收复了拉克瑙后,这次叛乱就瓦解了。新的军队纷纷赶赴印度。那诺·撒希普在国境线上乘机逃走了,克雷特海德上校带着一个急行军纵队把阿克拉的叛军肃清了,至此,印度又恢复了战前的和平状态。我们四个人都梦想着不久就可以平分宝物,远走高飞,可是转眼间我们的梦幻消失了,我们都以杀人罪逮捕入狱了。
“经过是这样的:那土王因为信任阿奇麦特才让他来我们这埋藏珠宝,但土王的疑心重,他又派了一个仆人跟踪阿奇麦特,并让仆人紧紧盯住。那天晚上,他在后面亲眼看见阿奇麦特进入堡门,以为肯定把财宝藏好了,第二天他也设法进入堡内,却没看见阿奇麦特。他觉得很纳闷,于是就告诉了守卫班长,班长又报告给了司令。司令下令在全堡内进行一次周密地搜查,结果找到了阿奇麦德的尸首。在我们还以为安全的时候,就被以谋杀的罪名逮捕了,我们三人当时在值岗,其余一人是和被害者同来的。那时土王被罢免并被逐出印度,已经没有人对宝物有直接的关系了,可是案情确凿,判定我们四人为凶手。三个印度人被判终身监禁,我被判死刑,后来得到减刑,和他们一样。
“我们四人都被判了无期徒刑,恐怕今生再难恢复自由,尽管这样,我们都保守着一个秘密,我们仍然梦想着只要获得宝物,很快就会成为富翁。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清楚宝物的埋藏地,却无法把它取出来,还得吃糙米饭,喝生水,忍受看守的百般凌辱,我对监狱生活真是无法忍受。幸好我的性情坚强,耐心地期望着时机到来。
“好机会真的到来了。一天,我从阿克拉城的监狱转到马特拉斯,又转到安达曼群岛的普雷尔岛。那个地方,白人囚犯很少,我表现得又好,不久我就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子,就在海锐阿特山的好望城。那个岛上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热病,离我不远处还有吃人的原始部落,他们经常朝我们放毒刺。我们开垦荒地、挖沟、种薯蓣,还干好多杂事,整天忙个不停,到了夜晚才有点空闲。我在那儿学会了为外科大夫调配药方,对外科技术也学了一点,我时刻寻找逃跑的机会。可是那个孤岛离任何大陆都有几百英里远,而且在附近一带的海面上几乎没有风。根本不可能逃出去。
外科大夫萨莫顿是个活泼贪玩的青年,一到晚上,驻军的年轻军官都爱到他家去耍牌赌钱。
我配药的外科手术室和他的客厅只有一墙之隔,有一个小窗相通。我在手术室里呆着没啥事的时候,我就熄掉屋里的灯,趴在小窗前看他们玩牌,听他们说笑。我本来也喜欢玩牌,看他们赌钱,在一旁看着也觉得过瘾。他们中,经常有率领着一支土人军队的舒尔托少校、摩斯坦上尉和普罗姆立·普劳恩中尉,另外还有两三个司狱的官员。这几个官员是玩牌的行家,他们几个凑成一桌,玩得挺痛快。
“不久我发现了一件怪事,每次玩牌都是司狱官员们赢,军官输钱。我想可能是司狱官员们到达安达曼岛后,闲着没事打牌的日子久了,水平练得高了。军官们的打牌本领不怎么样,每赌必输,越输越急,压得赌注越大,最后他们的钱少得可怜了。舒尔托少校输得最惨。他先是用钱,现钱用光了,他就用期票。他有时也会赢点,再接着下更大的赌注,结果输得更惨,因为这他整天郁郁寡欢,借酒浇愁。
“有天晚上他比往常输得更多。他同摩斯坦上尉往营地慢慢地走。我当时正在屋子外头纳凉,听见少校边走边向上尉抱怨他的晦气。他和中尉的感情不错,整天呆在一块。
“他经过我房间的时候,少校说:‘摩斯坦,我可怎么办好呢,看来我得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