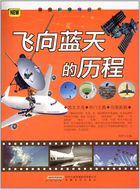清乾隆以来,苏州生产的木制插屏钟,一般称作“苏钟”,广州生产的钟一般称作“广钟”。苏钟和广钟可称是将机械钟与中国古典美融为一体的产物。它们具有现代机械钟的报时功能,又给人以古香古色的美感。50年代,尚有不少老式家庭陈放着这种苏钟或广钟。它们与中国古典家具摆在一起,相映生辉,使厅堂之内显得愈加堂皇高雅,为居室平添了一种文化氛围。我的一位朋友平生最欣赏的就是那些造型古雅、独具风格的中国传统形式的钟表。他收集了几十只苏钟、广钟和近代中国制造的其他形式的大小钟表。他的家也够上一座小型的中国古典钟表博物馆了。
表,则以近现代的产品为多。但玩家最倾心的是那些年代较久、华贵而能代表身份的“占董表”。如“嵌环珠万花不落地”怀表、早期的金壳“蓝篇”表,就十分名贵。18世纪,俄罗斯雪尔夫城有个钟表制造商,别出心裁地造出一只“天文”挂表。这只表的表面缀满天上的星辰,不仅能显示出月亮的盈亏,而且能指出太阳的升沉。这类“古董表”就是玩家梦寐以求的稀见之物。
有的人玩钟表讲求系列性。就是对钟表中的某一产品从其创始而至发展到现代最高水平的各代产品进行系统的收存。以表而言,劳力士、欧美茄是“重头”。但就这两个牌子来说,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其产品也在不断更新样式、结构和功用。因此,仅劳力士一种或欧美茄一种,就分别是一个系列。系列收存是很不容易的,某一产品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换代产品难以搜寻,而其第一代“开山祖”更是得之不易。就拿电子表来说,第一代电子表叫摆轮式电子手表,是50年代由瑞士研制出来的,另外还有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电子表本来不值钱,但要进行系列收存,将各代电子表收集齐全,却绝非足一件简单的事。
玩钟表讲究“原装原件”,即零件不能有后配的,最好是未经修理,甚至应有原链、原盒。这样的钟表,其收藏意义和玩赏价值才是可观的。
七、收藏须知佛教造像
佛教造像是中外收藏家倾心以求的珍贵艺术品。民国年问,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已将造像列入古玩的一个专项,与书画、瓷器、古钱等相提并论。当时,精品的价格高得惊人。据说,1918年河北省正定县有一农民在犁地时犁出一尊北魏鎏金菩萨造像。这尊造像身高约二尺,有莲花座,外围有栏杆,每个栏杆都是一尊小佛像。北京的几个古玩商得知后,合伙以3万元大洋买下,转手以15万元卖给了日本人。
然而,近几十年来,佛教造像的价格很不稳定。尤其是“文革”以后,起落愈加明显,呈现出由低谷走向回升的趋势。
70年代初,佛教造像的平均价格一度曾陷入最低的境地。一些私人持有者甚至根本不了解这种宗教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大多以低价出手。当时一尊北朝石雕造像只卖到30元至100元。有人仅出20元就买到一尊通高7.5厘米四足方座的北齐时的铜质造像。以上都是笔者亲眼所见。佛教造像的价格跌落到如此地步,应该说是一种偶然。当时主要是受时尚的影响,多数人尚未从偏狭的观点中摆脱出来,对宗教艺术品的珍贵价值没有足够的认识,买卖双方大都处于盲目状态。80年代初,一些人开始认识到造像的价值,价格随之上升。但对造像价格的评估仍存有偏颇。在古物市场的民间交易中,许多买卖者并不注重研究作品的年份和造型,而是停留在以大为贵的肤浅认识上。当时尺寸较大的铜质造像卖到几百元,最高达千元,而小一些的,即使是北魏作品,也未必有人能识。这说明造像的潜在价值尚有待挖掘。
90年代初,由于人们鉴赏水平的提高和对宗教艺术品的崇尚,求购佛教造像者日增,价格迅速上涨。笔者从行里打听到,我国大陆,当今明清造像的价格与80年代初相比已增长了几倍。在古物市场,一尊高度在30厘米左右的清代鎏金铜造像能卖到数千元,精品数万元,而且还不易得见。价格涨幅最大的是南北朝、隋唐时代造像。20年前被许多人忽略的石造像现已卖到三四万元乃至几十万元。《观音珍藏》一书载:北齐武平六年石雕观音像,高35.8厘米,价值约120万港元;东魏白大理石观音像,高61.5厘米,价值约250万港元。《佛像珍藏》一书载:一件北魏金铜佛像,高仅12厘米,约值8万港元:北齐石灰岩观音像,高127厘米,约值180万港元,唐代大理石佛坐像,高63厘米,约值60万港元:唐代砂岩佛像,高约68厘米,约值70万港元:北魏石灰岩佛像头部,高约50厘米,约值70万港元:唐代白大理石佛像头部,高约35厘米,约值50万港元。在港台地区,许多人购藏造像精品更是不惜重金。据《龙语文物艺术》报道:1990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苏富比大型拍卖中,一尊明代的鎏金禅坐佛像以495万港元成交,多出最低估价近一倍;另一件明代鎏金三藏坐,像以77万港元成交。如果是同等尺寸的南北朝时代鎏金造像精品,则更不知要高出上述成交价的多少倍。于此可见,佛教造像是很有投资潜力的。
中国佛教造像的收藏价值和保值意义与作品自身的艺术水平基本上是一致的。我国自魏晋以来,佛教造像成千上万,虽然各代都有精品,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六朝、隋、唐的作品成就为最高,收藏造像首先要着眼于这段时期的精品。有人评定铜造像的价值仅以尺寸大小为依据,这就难免走上购藏的误区。因为唐以前的金铜造像最大的不过二三十厘米,小的仅几厘米。单纯强调尺寸,容易把购藏目光转向明清作品而失掉收藏南北朝及至隋唐精品的机会。有人评定石造像过分追求完美无缺,以为略有小残便要不得,这也是不对的。石造像完整无缺当然珍贵,但实际情况是,经过南北朝和唐代的几次灭佛,石造像通体无缺的甚少。收藏石造像不比收藏古瓷器,如果稍有小残便不予投资购买,就很难得到造像真品。夹疗漆观音坐像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佛教造像有的还雕凿文字,称“造像题记”。文字数量不等,多则数百,少则几个或十几个。文字多的,记录的一般是达官贵人或上层人物的事;文字少的,所记的一般是平民百姓的事,上面多有纪年和造像人。如“大魏太延五年乙卯,佛弟子赵忠为男军途困难许造像一驱,永奉存祀,四月三日造”的造像题记,便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类。造像题记对南北朝和隋唐时代造像的收藏价值有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精品,无题记者价钱略低,有造像题记者身价倍增。尤其是文字较多的造像题记,其史料价值、书法价值、雕塑艺术价值兼而有之,更是堪为珍宝。造像题记也有后人伪造的,购藏时要注意鉴别。
至于唐代以后的造像,则应以制作精美和材质稀贵作为购藏的主要标准,其次再考虑尺寸大小。宋、元、明、清的铜造像有精工之作,也有平庸之作。平庸之作,收藏价值并不太高。精工之作则不但通体鎏金,还镶嵌珍珠宝石,给人珠光宝气之感。这样的造像自然珍贵。铜造像之外的精品,也有取金、银、翡翠、象牙、白玉、碧玺为材质的。这类作品就更显珍贵了。一尊清代大型翡翠观音造像在苏富比拍卖中标参考价竞达451万港元,这说明明清造像只要精美绝伦、且为精良之材所制,也是价高一筹的。
八、石佛的收藏与辨伪
佛教造像由单纯的宗教崇拜偶像而成为受人青睐的收藏品和观赏品,当始于清朝初叶。并且,随着清代金石考据的兴起,佛教造像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逐渐为人们所开掘和认识。
从资料上看,唐以前的单体石造像,在清康熙时代已有人收藏。在清宣统年间上海出版的《神州国光集》录有庞芝阁藏东魏武定三年石造像的拓片,上面就有清初画家恽南田的题识。题识对造像的缘起作了分析,之后又记下该造像的风格、文字、归属。其中说道:“此石龛释迦像一尊,坐(座)下字三面,计十四行,每行四字,尾行只一字,统五十三字,为魏武定三年,当是宣武年号,观其字体古拙,犹存汉魏遗风。是像今为蟾一吴子所得,以此拓片见贻,余喜,遂装成并记于上。”最后落款是“康熙乙丑秋七月廿又四日,东园客寿平”。乾隆时代以后,单体石造像不仅为一些人所倾心收集,而且已见之于著录,成为金石学家鉴赏的对象。乾隆时学者王昶以50年之力编《金石萃编》160卷,在是书中就著录了大量的石造像,其中尤以造像碑为多,并附《北朝造像诸碑总记》,对北朝石造像的雕凿情况及其特点作了分析。其后,叶昌炽的《语石》、张鸣珂的《寒松阁题跋》等金石和鉴赏专著,均有石造像的纪中收入石造像跋语数条,如东魏武定八年杜文雍造像、杜照贤造像、西魏大统十四年造像等,对这些造像的雕凿年代和出土地点作了考证。他在《东魏武定三年造像跋》中,还对当初恽南田的题识提出质疑,作了纠正。
近代金石学家早已将佛教造像引入金石学的研究领域。如近人王懿荣的《天壤阁杂记》、马衡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以及后来朱剑心所著《金石学》等,都将单体石造像作为金石中的一个专项加以叙述。王懿荣《天壤阁杂记》还以亲眼所见,对清光绪八年(1882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掘出残石佛像百余的史实作了记载。他说:“成都西关有万佛寺故址,忽出残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蜀碧所称献贼凿去者也。”(所谓“献贼”即指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据史料所证,此非张献忠时所为。)王懿荣自称出私囊拣得有字残像三尊,“一元嘉,极大,一开皇,一无纪元”,又拣得残碑五七方,不成文,皆苏石、川石,本质松,此又经火而复人土者,须甚护惜。于是他用船只将其购得的石造像,统统运往山东福山老家收藏起来。在那一时期,不光王懿荣收藏单体石造像,大江南北不少文人如郑文焯、黄易、童大年诸人,都喜爱这类藏品。民国年间东南日报社出版的《金石书画》特刊中,常刊出单体石造像照片或拓片供世人欣赏,其原物大多是清末民初的私家藏品。如梁顾廷谦陈宝齐造像、南齐维卫尊佛造像、魏王元夫造像、梁中大同慧影造像,为淮阴陈氏石墨楼所藏:北周夏信纯陀造像,为会稽顾氏金佳石好楼所藏:北魏太和二年乐安公主造涂金石像、北魏比丘法光为弟刘桃扶造像,为杭州童氏绿云山房所藏。这些单体石造像精品,皆经名家的考证和题跋。有的藏家本人对自己的藏品也做出评价。北魏太和二年乐安公主造涂金石像的收藏者童大年为该藏品题记道:“此像系近年洛阳出土者,己巳仲秋得于海上,供奉绿云庵中,郑大鹤尝谓造像之足于史者至可宝贵,况此大名鼎鼎乎?涂金虽已剥蚀,而石质细润如玉,亦非凡品,尤足称已。”北周夏信纯陀造像的藏家题记为:“民国七八年间陕西出土,京贾鬻于沪而转入于粤,丁卯秋,余得之番禺,李氏携归上海,供诸思简楼,高今尺二尺弱,三面镌字,共百十有六”云云。(见《金石书画》合订本)从以上题记中可以看出,近现代的造像收藏家多从考古及书法的意义上品评造像的价值。新中国建立后,佛教造像被载入中国雕塑艺术史,收藏家和艺术家不仅注重它们的考古作用,而且更多地从美术的角度挖掘它们的美学价值,对造像的艺术性有了新的认识。当代雕塑家、美术理论家如王子云、史岩等人均有这方面的专著。
由于单体石造像早在清代已被世人所重,故百年以前就有专门仿造古代石造像的高手。清人张鸣珂在谈及北朝石造像时,即有“都门李宝台又善作伪,以售其欺,鱼目混珠”的记载。(见《寒松阁题跋》)民国年间,仿制六朝石造像的风气最甚。因此,多数行家认为,六朝石造像的仿制品十之八九出自民国时代。至于近年来某些盛产石料的地区,工匠们伪造出的石佛,为数就更多了。现今伪造的石佛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劣仿”,神态、眉眼与衣着,制作粗劣,与真品相去甚远:另一类是“高仿”,不但神态、衣着做得讲究,而且能仿出石质剥落的特征,这类伪品极易迷惑藏家,购藏时必须严加鉴别,不可拿今世之物当成古代珍品。
九、古玩的座、架、盒
在文化积淀深厚而又极讲古雅气派的中国古代,古玩的座、架、盒作为青铜器、瓷器、玉器、印讲、奇石、文玩、书画等物的附属、陪衬与装潢,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是颇费心机、相当考究的,哪怕是其独立存在,也有很强的观赏价值和保留价值。
清末年间苏州怡园主人顾鹤逸有一藏石,此石不但有岩峦洞壑之形、枯木之质,叩之有声,而且颠倒、正侧,可以摆出多种不同姿态。主人特意延请木作高手为藏石制做了九个不同形态的座子,以便随时变更其陈列方式。这些座子,个个精巧别致,且刀工准确利落,与藏石的九个底面紧紧相扣,可谓匠心独运。民国时期,天津收藏家徐世讲喜藏古砚。他的砚台作工纤巧,砚盒也极富特色。据古砚鉴定家、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蔡鸿茹讲,徐先生藏砚里外三层包装,里面是布盒,外面是楠木盒,布盒里面的砚台又配以紫檀木盒,盒里有小题签。另有小绢袋装有款识,题写收藏经过及铭文撰写者的小传等,从中也能证明其藏品流传有绪。
至于那些为稀世珍玩配制的座、架、盒,更是尽善尽美,无与伦比,达到了极致。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的西晋陆机所书《平复贴》,在传世的中国法书真迹中堪称魅首,而清代保藏《平复帖》的紫檀盒亦是非同一般。此盒为长方形,素身,盖上刻“西晋陆机平复帖”,并落下款“诒晋斋”等隶楷字样。书风圆健雄浑,雍容华贵,刻工精细,刀法有力。盒的装饰虽略显简单,然朴素雅致,颇具皇家气派。并且采用上好的鸡血紫檀木为料加工制作,通体显现古朴的“包浆亮”。有人推断,此盒乃乾隆皇帝将《平复帖》赐给成亲王后为其所制,或是成亲王请造办处工匠为其制作。据说张伯驹从溥儒手中买到《平复帖》时并无此盒,且多年来下落不明,盒是前几年被人偶然从旧物市场发现的,至此方“珠联璧合”。当年,张先生曾在写给溥儒的信中提到,在《墨绿汇观》中著录的《平复帖》原附带有一件紫檀盒和一块宋代的缂丝,亦可见这位大收藏家对《平复帖》原盒的重视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