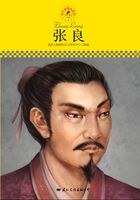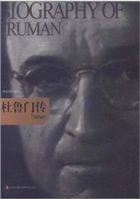王廷相作为明代“前七子”之一,一生中创作了许多诗歌;而且在文学评论上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系统的文学思想。与“前七子”其他成员一样,他推崇古典诗文,但是他又反对盲目效古。他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提出“文以阐道”,“文者,载道之器”。在诗文创作上,他主张“无意于为文”,追求真情实感,反对矫揉造作;同时又提出“诗贵意象透莹”,主张含蓄而不露。
一、崇古论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是“前七子”崇古思潮的核心。对于古典诗文,王廷相亦是推崇备至。他说:
文之体要,难言也。援古照今,可知流委矣。《易》始《卦》、《爻》、《彖》、《象》,《书》载《典》、《谟》、《训》、《诰》,《诗》陈《国风》、《雅》、《颂》,厥事实,厥义显,厥辞平,厥体质,邈兮古哉!蔑以尚矣!自夫崇华饰诡之辞兴,而昔人之质散;自夫竞虚夸靡之风炽,而斯文之致乖;言辩而罔诠,训繁而寡实。于是君子惟古是嗜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广文选序》。
唐、虞、三代,《礼》、《乐》敷教,《诗》、《书》弘训,义旨温雅,文质彬彬,体之则德植,达之则政修,寔斯文之会极也。汉、魏而下,殊矣:厥辞繁,厥道寡,厥致辩,厥旨近,日趋于变然尔。《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何氏集序》。
显然,王廷相极力推崇的是汉魏之前的古典诗文,尤其是《礼》、《乐》、《诗》、《书》之类;而对汉魏之后的诗文,他则予以大加贬低;即使对于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也认为“自今观之,颇为近古,然法言大训,懿章雅歌,漏逸殊多。词人藻客,久为慨惜,然未有能继其旧贯者”(《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广文选序》。)。因此,他主张“君子惟古是嗜”,足见他对于古典诗文的推崇。
在推崇汉魏之前的古典诗文的同时,王廷相对于近体诗则是主张效法盛唐。他说:
律句,唐体也,天宝、大历以还,等而上之,晚唐不复言。苏、黄有高才远意,格调风韵则失之。元人铺叙藻丽耳。古雅含蓄,恶能相续?今礼乐百年,作者辈出,善厥斯艺,可以驰诸唐人真衢,近见二三子,亦可谓难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寄孟望之》。
王廷相认为,近体诗自晚唐开始逐渐衰退,苏轼、黄庭坚的宋诗已失“格调风韵”,元诗则只是“铺叙藻丽”,直至明代,“可以驰诸唐人真衢”者,可谓凤毛麟角。他还说:
古人之作,莫不有体。《风》、《雅》、《颂》逖矣,变而为《离骚》,为《十九首》,为邺中七子,为阮嗣宗,为三谢,质尽而文极矣;又变而为陈子昂,为沈宋,为李杜,为盛唐诸名家,大历以后弗论也。据其辞调风旨,人殊家异,各竞所长以相凌跨,若不可括而齐之矣。君子之言曰:“诗贵辩体。”效《风》、《雅》,类《风》、《雅》;效《离骚》、《十九首》,类《离骚》、《十九首》;效诸子,类诸子;无爽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刘梅国诗集序》。
王廷相推崇古典诗文,认为诗文创作不可与古典诗文相违背。
对于明代的诗文与古典诗文的差距,王廷相予以归纳,他指出:
愚观今不逮古,约有三论。宇宙间事情景物,万古无殊,诗人以来,言之略尽。后世借曰变易局格,终归謦欬耳。世谓律诗起于唐而独盛于唐,不以是夫?此不逮者一也。或者才非超绝,不能御风鞭霆,浮游八极,以脱去尘陋,终尔等流,二也。有高才矣,复不能刻力古往,任情漫道,畔于尺榘。以其洒翰美丽,应情仓卒可也,求诸古人格调,西施东邻之子,颦笑意度,决不至相仿佛矣。此不逮者三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寄孟望之》。
从以上言论中,可以看出王廷相对于古典诗文的偏爱和对当朝文学的贬抑。
王廷相推崇古典诗文,因此对于他同时代的文学家的作品,往往以古典诗文为参照进行评论。他在为“前七子”之一李梦阳的《李空同集》所作的序中说:李梦阳“以恢宏统辩之才,成沉博伟丽之文,厥思超玄,厥词寡和,游精于秦、汉,割正于六朝,执符于《雅》、《谟》,变于诸子”(《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李空同集序》。)。在为“前七子”的何景明所著《大复全集》所作的序中说:“今其文,侵《谟》匹《雅》,欲《骚》俪《选》,遐追周、汉,俯视六朝,温醇典雅。”《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何氏集序》。
王廷相推崇古典诗文,但是他又认为,诗文的创作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各个时代应有各个时代的作品,作家各自的作品应有自己的特点。王廷相说:
大观逖照,虽经坟子史,判不相能,以各发舒其华也。掞道逑政,虽尧、舜、三王,靡所搃摄,以各际会其变也。况兹以文命乎率由,嗜好成于性资,安能古今拟议,同一区畛?《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李空同集序》。
这是认为,即使是古典诗文也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只是代表一定时代的艺术精华,古今不可能一致。可见,王廷相非常强调文学作品的时代特色。王廷相还认为,由于人的天赋才智的不同,要真正做到与古典诗文的一致也是非常艰难的,“神情才慧,赋分允别,综括群灵,圣亦难事。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刘梅国诗集序》。)。
在文学作品创作与古典诗文的关系上,王廷相虽然主张文学创作不可与古典诗文相违背,但也反对只是停留在外在形式上的泥古。他说:
夫今之人,刻意模古,修辞非不美也,文华而义劣,言繁而蔑实,道德政事,寡所涉载,将于世奚益?谓不有歉于斯文也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石龙集序》。
王廷相认为,只是停留在对古典诗文的形式上的刻意模仿,虽然辞美文华言繁,但是并无益于世,而且也与古典诗文相违背。为此,王廷相说:
譬医之治例,三焦五脏,风寒暑湿,药有定品,方有定拟,工医音能循持而守之,虽无大益,保无大缪矣。虽然,工师之巧,不离规矩;画手迈伦,必先拟摹。《风》、《骚》、《乐府》,各具体裁;苏、李、曹、刘,辞分界域。欲擅文囿之撰,须极古之遗,调其步武,约其尺度,以为我则,所不能已也。久焉纯熟,自尔悟入,神情昭于肺腑,灵境彻于视听,开阖起伏,出入变化,古师妙拟,悉归我闼。由是搦翰以抽思,则远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属,生动之物,靡不综摄,为我材品;敷辞以命意,则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仙圣之灵,山川之精,靡不会协,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习而化于我者也。故能摆脱形模,凌虚构结,春育天成,不犯旧迹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王廷相认为,诗文创作首先要以古典诗文的格式体裁为规则,因此“必先拟摹”。但是,他又认为,诗文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水平上,而是要经过长期努力,达到纯熟和感悟,使古典诗文的神情、灵境成为创作的内在的东西,从而达到神似而非仅仅形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前七子”的崇古思潮中,王廷相的崇古论并非完全是一种复古论。他反对当时文坛上的“刻意模古”(《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石龙集序》。),而主张古典诗文的素朴、古雅和神韵,更有吸取古典诗文的精华的意味。他的崇古论实际上是要否定唐以后的诗文创作成就,这无疑有失偏颇;但是他不是虚无主义,他容许诗文创作的因时而异、因人而异,而且对唐以后文学发展中的弊病进行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台阁体”,更有一种文学改革的思想和进步的意义。
二、文以阐道
王廷相推崇古典诗文与他在文道关系上主张“文以阐道”是相互联系的。他认为:“文以阐道,道阐而文实。‘六经’所载皆然也。”《雅述》上篇。但是,到了晋、宋以后,文学作品就变成只有载道之名而无载道之实,有文而无质了。他说:
“晋、宋以往,竞尚浮华,刻意俳丽,刘勰极矣。至唐韩、柳虽稍变其习,而体裁犹文。道止一二,文已千百,谓之阐道,眇乎微矣。”
载道之典,至文也。文不该于道,繁则赘,丽则俳矣,故君子鄙之。尝观唐、虞、三代之典,即事命辞。而文生焉,盖道为主而文为客也。魏晋以降,即辞撰事而文饰焉,盖文为主而道为客也。是故异端谶纬之事作,而先王淳正之道离矣;诬怪谬幽之论兴,而古圣真实之旨塞矣;俗儒曲士之书出,而时君经治之术暗矣。间有大心贞观之士,探源返古,以追洪蒙,然俗蔀已深,涛澜滚滚,莫知所趋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三《近言序》。
显然,王廷相之所以推崇古典诗文,是由于古典诗文以道为主而文为客;贬低魏晋以后的诗文,是由于其以文为主而道为客。而在他看来,只有载道之诗文,才为至文;而且须是道为主、文为客。同时,在王廷相的崇古论中,他反对“刻意模古”,其原因就在于这类作品“文华而义劣,言繁而蔑实,道德政事,寡所涉载”(《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石龙集序》。)。可见,“文以阐道”是王廷相崇古论的深层原因之一。
与提出“文以阐道”相联系,王廷相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作品对于道德教育、治政等的作用。他说:
求诸《三百》之旨,径域乃真耳。其教,温柔敦厚;其志,发乎情,止乎义礼;其究,形四方之风而已。能由是而修之,诗之正始得矣……本乎性情之真,发乎伦义之正,无虚饰,无险索,无淫取,可以移风易俗,可以助流政教。《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刘梅国诗集序》。
文者,载道之器,治迹之会归也。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即道,治即文矣。是故古人之文莫不弘于学术之所趋,莫不实于治功之有成……君子修辞,虽雄深博雅,力总群言,而无当于修己经国之实者,自负曰文,去文万里矣。《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广文选序》。
显然,王廷相是把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也当作评价的标准之一。
王廷相以“文以阐道”及社会功用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并以此评价他同时代的文学家的作品。他赞赏黄绾的作品“学有三尚”,即“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明道而不切于政,则空寂而无实用;稽政而不本于道,则陋劣而非经术;不足以通天下之情,亦不足以协万物之宜,其为志也,得其偏隅而迷其综括,欲周天下之变难矣……夫道明则仁义由,德性成,学术正,风教端矣。政稽则皇极建,治化流,民物遂,社稷奠矣。学具乎此,得时而行,必举海宇而复冒之,非志存于天下万物者能之乎”《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石龙集序》。在《杜研冈集序》中,王廷相称杜柟的诗文,“气冲笔健,学博思深,吐语符道德,发虑中经纶……可以厚人伦,可以植风教,所谓人纪、天道、性情、政理之外无文章者,乃于是乎可睹。”《内台集》卷六《杜研冈集序》。把明道和社会功用看作是评论文学作品的重要依据。
王廷相主张“文以阐道”,但并不否定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是强调“道为主而文为客”;在“文以阐道”的前提下,他也主张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他说:
君子修辞,要在训述道德,经理人纪,垂示政典,尚也。必品格古则而后文之美备,故曰“理胜则传”,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钤山堂集序》。
尝以文不载道,不足传世;词不古雅,虽传弗久。每于饰格命意,以兹为准。而《风》、《雅》、《左氏》先秦之调,恒数数焉。故其文醇正典则,无佻率崄怪之病,足以力追古人而兴之颉及。《内台集》卷六《研冈杜公墓志铭》。
在这里,王廷相既强调“文以阐道”,也主张诗文必须古朴、典雅。但在他看来,“文以阐道”始终是第一位的,是本。他还说:
大抵体道之学,缓急有用于世。诗文之学,君子固不可不务,要之辅世建绩寡矣,而不适用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言君子之学,不可昧其本末先后之序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答王舜夫》。
他认为,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固不可不务”,但是仅停留于此,并不能“辅世建绩”;而只有具备思想性的东西,才能“有用于世”。因此,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本,是为先的,而其艺术性是末,是为后的。在这里,既可看出王廷相在文学作品的道与文、思想性与艺术性二者关系上的基本观点,也可看出他提出“文以阐道”的真正目的在于强调文学作品的有用性。
王廷相主张“文以阐道”,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因而也非常强调作家的道德修养。他说:
乃惟大人硕儒,探元挈要,先之修性体道以敦其本,又能察于君臣之政,观夫天下之势,达乎民物之情,则文之质具矣。从而立言,其道真,其业实,无诞美,无虚饰,参诸“六经”之旨,靡所差别,不亦天下之至文乎!《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广文选序》。
王廷相认为,要创作出“天下之至文”,首先要“修性体道”。他又说:
予尝谓君子之文,根诸德性学术之造诣者,深乎极矣。苟于是二者有歉,虽其才智足以立言,不荡于淫靡,则莽于芜秽;不刻于巧,则痼于浅率;不迂于事情,则迷于时宜;不惟无以考德论学,以之敷政轨物,亦无所于达矣。是故君子病之。《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钤山堂集序》。
这里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与学术造诣是君子之文的根本,若二者有所欠缺,就不可能有佳作。作家的道德修养决定其作品,同时作品也可反映作家的道德修养。他在《钤山堂集序》中评论钤山的作品时说:“今观钤山之集,辞旨冲淡者,则知先生之纯素;雅则者,则知先生之正直;简严者,则知先生之整肃;温润而韫蓄者,则知先生敦大而浑厚;朗练而有剂量者,则知先生炳于几先而时措。嗟乎!兹于道于治,其庶几矣,夫安得而不传?”《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钤山堂集序》。王廷相认为,道德文章互相联系、互相印证。
三、无意于为文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至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骈文。骈文是从汉赋发展而来,讲究词句的整齐对偶和声律,追求词藻的华丽,重视引经据典,但思想内容贫乏。这种文风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此,王廷相说:
嗟乎!文章之敝也久矣。自魏晋以还,刻意藻饰,敦悦色泽,以故文士更相沿袭,摹纂往辙,遂使平淡凋伤,古雅沦陨,辞虽华绘,而天然之神凿矣。况志不存乎道者其识陋,情不周于物者其论颇,学不经乎世者其旨细。由是而为文,乃于人也不足以训,而况支赘淫巧,以垢蔑乎《风》、《雅》、《典》、《谟》之正乎?《内台集》卷六《杜研冈集序》。
王廷相认为,那种“刻意藻饰”而无思想内容的文章,实际上有失“平淡”、“古雅”和“天然之神”,只是“识陋”、“论颇”和“旨细”之文。王廷相还说:“世儒崇尚虚静,而无明物察伦之学,刻意文词,而后辅世和民之绩,则于仲尼门径荒哉遐矣,谓达诸道,何啻霄壤?”《内台集》卷五《栗应宏道甫字说》。显然,王廷相是反对“刻意文词”的。
王廷相虽然推崇古典诗文,但他又反对“刻意模古”。对于那种只是从形式上模仿而无思想内容,“文华而义劣,言繁而蔑实”之类的文章,王廷相以为“有歉于斯文也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石龙集序》。
与此同时,王廷相还反对文学作品创作中的“猎奇”和“泥迹”。他说:
饰词藻者猎奇,执往范者泥迹。猎奇则实用乏,泥迹则时宜迷。斯二者,文之弊也,故君子不贵。《华阳稿》,《赵清献公奏议序》。
可见,在文学创作中,王廷相既反对“刻意文词”,又反对“刻意模古”;既反对“猎奇”,又反对“泥迹”;实际上就是反对弃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专注于文辞形式。因此,王廷相说:
有意于为文者,志专于文,虽裁制衍丽,而其气常塞,组绘雕刻之迹,君子病之矣。无意于为文者,志专于道,虽平易疏淡,而其理常畅,云之变化,湍之喷激,窅无定象可以执索,其文之至矣乎!《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石龙集序》。
他认为,“有意于为文者”,专注于文辞,而忽视作品的思想性,其所要表达的内容受到限制,其内在精神受到阻塞;“无意于为文者”,则专注于思想性,其文理通畅,气势磅礴,飘洒不拘。
王廷相提出“无意于为文”,主张文学创作要“专于道”,而不受文辞的限制,反对“专于文”,在文辞上刻意雕琢,堆砌辞藻,这与他的“文以阐道”的思想是相互联系的。他主张“道为主而文为客”,因此,文学创作就必须专注于道;但道与文并非完全对立,互相排斥,而是在二者的主次上有所差别。
王廷相的“无意于为文”不仅主张文学创作要“专于道”而非“专于文”,而且还包含有文学创作要自然而然、不要为创作而创作的意味。在他论及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有人问他:“群品效材,万象呈美,何若是多?子将以言示于世耶?饬旨摛辞,归综于道,何若是严?子将以贤示于世耶?”王廷相避而不答。此人又问他:“感于天机,万物皆入吾之会,虽言之而非谥言耶?存乎道符,言也举不畔其则,恐淆乱于外,而卓守其贞耶?夫子殆不得已而言,非乎?”王廷相仍然避而不答。此人再次问他:“云之生于山,气机也;升于太空,其象为峰峦,为水波,为白衣,为彩锦,为人物,为花卉。其变也,云何尝以意而为之?龙之乘乎云也,自适其性尔,感而为雨,泽彼下土,不几于神乎?使曰龙之致之,虽问之龙,龙亦不知。夫子之为文,以是求之,可乎?”王廷相辗然而笑曰:“有是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华阳稿序》。王廷相赞同文学创作过程是一个思想自然表露、文辞自然运用的过程,而不是“以意而为之”;对于把文学创作过程看作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学才华或纯粹是为了说教,他持不同意见。他还认为,文学创作犹如“龙兴而云集,月彩而蜃胎”,要“行于无所要取之途,而物自相与感之”。他接着说:
虽然,有物感,有真感。何谓物感?赞德以广誉,分资以通义,拔滞以登仕,排难以舒愤是也。何谓真感?去雕存朴,其心忳忳,万变沓来,守吾之忱,利害险僻不入于灵府,而羲、轩、尧、舜游于至诚之域而不厌者是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二《楚泽赠言序》。
王廷相主张,文学创作是真情实感的自然表露,是一种内在需要,而不是为了“广誉”、“通义”、“登仕”、“舒愤”之类的目的。
四、诗贵意象透莹
王廷相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而且在诗歌创作手法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尤其是他提出“诗贵意象透莹”的观点,是意象论的倡导者。王廷相说:
夫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黏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可以目睹,难以实求是也……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王廷相认为,诗歌创作不可平铺直叙,而是要有意象,一种源于现实生活但又超于现实生活“难以实求是”的艺术虚构;平铺直叙之作“寡余味”、“难动物”,而意象则耐人寻味,使人产生同感和遐想。
王廷相的意象论与他的崇古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说:
《三百篇》比兴杂出,意在辞表;《离骚》引喻借论,不露本情。东国困于赋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则天之不恤自见。齐俗婚礼废坏,不曰“婿不亲迎”也,曰“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璚华乎而”,则“婿不亲迎”可测。不曰“己德之修”也,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则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以改措,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则“己之守道”,缘情以灼。斯皆包韫本根,标显色相,鸿才之妙拟,哲匠之冥造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王廷相认为,《三百篇》、《离骚》等古典诗文均是意象创作的典范,其“比兴杂出,意在辞表”,“引喻借论,不露本情”的创作手法,使作品寓意深远而含蓄。王廷相又说:
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事委实,言多趂帖,情出附辏,此则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王廷相认为,杜甫、韩愈等人的一些叙事诗,平铺直叙,缺乏意象,属“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此言论虽有偏颇之处,但强调诗要有意象,不失为一家之言。
至于诗歌的创作,王廷相提出“四务”、“三会”。他说:“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务;真积力久,以养而充者有三会。谓之务者,庸其力者也。谓之会者,待其自至者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所谓“四务”,他说:
何谓四务?运意、定格、结篇、练句也。意者诗之神气,贵圆融而忌暗滞。格者诗之志向,贵高古而忌芜乱。篇者诗之体质,贵贯通而忌支离。句者诗之肢骸,贵委曲而忌真率。是故超诣变化,随横肖形,与造化同工者,精于意者也;构情古始,侵《风》匹《雅》,不涉凡近者,精于格者也;比类摄故,辞断意属,如贯珠累累者,精于篇者也;机理混含,辞鲜意多,不犯轻佻者,精于句者也。夫是四务者,艺匠之节度也,一有不精,则不足以轩翥翰涂,驰迹古苑,终随代汩没尔。《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王廷相所说的“四务”,就是诗歌创作者的用力之处,也是诗歌创作的四项基本要求。其中“运意”,即是诗歌意象的形成。王廷相认为,“意者诗之神气”,意象是诗的精髓。对于诗歌意象的要求,他认为,“贵圆融而忌暗滞”,要“超诣变化,随模肖形,与造化同工者”,强调意象的清晰、完整、融通;要求超于现实生活,而又体现现实生活的真谛。在“四务”中,王廷相还认为,诗歌的格调“贵高古而忌芜乱”,要“构情古始,侵《风》匹《雅》,不涉凡近者”,强调诗歌的古雅,反映了他的崇古思想。
王廷相认为,要达到“精于意”、“精于格”、“精于篇”、“精于句”,就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为此,他又提出了“三会”。他说:
何谓三会?博学以养才,广著以养气,经事以养道也。才不赡则寡陋而无文,气不充则思短而不属,事不历则理舛而犯义。三者所以弥纶四务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趋可至也,力之久而后得者也。《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王廷相认为诗人必须在“博学”、“广著”、“经事”上作长期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