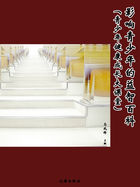我从一无所有到拥有整个世界,包括希望和爱这些难以数计的财富。以坚忍和信念渡过逆境,这就是犹太圣节和那奖品的意义所在,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美好的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兴高采烈地从海滩跑进临时租住的避暑寓所,却发现父亲和母亲四臂相拥,泪眼盈盈。
“怎么了?”我问,心猛烈地跳着。十岁的我从未见父母哭过。
“战争爆发了。”父亲说。虽然我对战争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但是我知道它将永远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在巴黎长大,家里收藏着许多油画、古玩和书籍,十四年前,父亲从立陶宛来到法国学医,与哲学系的母亲相遇,于是父亲娶了母亲,并放弃学业,与姑父一起经营皮货生意。姑姑的女儿弗兰西斯小我两岁半,就像是我的亲妹妹。
姑姑一家和我们住得很近,度假过节总在一起。我特别喜欢犹太圣节,这就是犹太人庆祝两千年前从叙利亚的希腊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节日。犹太圣节象征着不畏压迫,忠于信仰。父亲说:“不能背叛过去,要诚实地生活,以此来激励后人。”
我们珍爱那只古色古香的银质大烛台——九分枝烛台。到了犹太圣节,全家人围着父亲站着,看他隆重地点燃中间的蜡烛——主烛。以后每过一晚,我们都要从这支蜡烛引火点燃一枝分地。直到最后一天,把全部八支分烛点亮为止。
对于我和弗兰西斯来说,这些夜晚的高潮是旋转一只四边形陀螺。陀螺的每边都写着希伯来文:“一次伟大的奇迹发生在那里。”看陀螺停在哪个字上来定输赢。父母一辈的人组成一组,我和弗兰西斯是另一组,赢的总是我们俩。那时,我总是怀着幸福的感觉进入梦乡。
如今,那些幸福宁静的日子结束了。第二年春天,德国人开始轰炸巴黎。我们和姑姑一家到距离巴黎一个半小时路程的偏僻农庄避难。
不久,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北部,当地的犹太人终日惶惶不安。
一天,警察就要来大搜查了,我们惟一可以藏身的地方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地窖。下地窖前,父亲把我叫到跟前。
“莫特尔,我们也许得在下面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得想法记住这个世界是多么特别。”说着,他做出从一个架子上取下瓶子的模样,“让我们打开记忆瓶,把最喜欢的风景。气味和难忘的时刻都装进去。”
父亲让我赤足走过草地,为的是让我记住草的感觉。我嗅着各色花朵,然后闭上眼回味花的芬芳。我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天空,感觉微风的吹拂。“现在,我们把这些放进记忆瓶,盖好塞子。”他边说边假装盖瓶盖,那安详的微笑给了我希望和力量。
我们在地下室呆了几天。每当我感到绝望时,父亲就说:“拔开塞子,取一点记忆出来吧。”有时,我会取出一方蓝天,有时是一缕玫瑰的幽香,每次都让我感到好受些。甚至从地窖出来后,我仍然用记忆瓶来帮助我度过那些黑暗的时刻。
随着迫害的变本加厉,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有一个办法是到西班牙去,听说那里接受犹太难民。但如果在边境被抓住的话,那肯定要遭驱逐了。
在我十三岁生日的前一天,我们开了家庭会议。姑父提出冒险出逃,而父亲却犹豫不决。最后,他望着我问:“莫特尔,你说呢?”
我生平头一次应邀参加成年人的表决:“我们必须走,爸爸,这是惟一的出路。”我相信上帝的双臂拥抱着我们,他会庇护我们的。
“好,就这么定了,走!”父亲说。在我们走后两天,德国人占领了全法国。
我们躲过警察与德军的耳目,偷偷穿过法国南部。阁楼、地下室、后房都是我们的藏身所。终于,我们来到山顶覆盖着白雪的比利牛斯山脚下,在这里,父亲和姑父把身边的一半财富分给了两位向导,他们保证要带我们翻过大山,到西班牙去。
“爸爸。我爬不了山。”我对隐约可见的山峰心存畏惧,父亲拥着我:“不怕,莫特尔,只要迈出一步,就能迈出第二步,第三步。不知不觉,你就成功了。”
向导规定我们晚上爬山,白天隐藏。
拂晓时,我们到达高地,两位向导让我们休息,他们则到前面去探路。结果。他们没有回来。
我们呆在人生地不熟的山顶上束手无策。父亲说:“我们得靠自己走下去。”我们攀登在这似乎走不到头的山上,找不到下山的路。天越来越冷,人越来越饿。第二天,只剩下一片面包。姑姑把这片面包喂给小尤今吃了,我和弗兰西斯在一旁看着,顾左右而言他。
第三天晚上,父亲忽然失足滑下斜坡。在昏暗的月光下,我看到他掉在三十英尺以下的深谷里。他想爬起来却办不到。最后,他喊道:“别管我,你们走吧,我在这里呆一会儿再跟上。”
一股莫名的激情促使我向他跑去。“你一定要站起来!没有你我们不走,我来帮你。”
父亲看着我,倚着我的胳膊慢慢地站起来。我们一步步地朝其他人走去。他那苍白的脸告诉我他正受着多大的痛苦。
我的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通过帮助父亲,我战胜了恐惧,我长大了一些。
第五天凌晨,我们终于能望见山脚下的村庄了。每个人的脑海里都闪现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们还是在法国怎么办?
我们提醒吊胆地朝小村庄走去。终于,我们看到一块用西班牙语写的招牌!我们欢呼雀跃,互相拥抱着。成功了!
父亲前往当地政府。政府官员问:“有入境证吗?”当然没有。“算我没看见你们,请迅速离开这里!”
怎么办?“往葡萄牙走。”大人们决定,“这是惟一的希望。”一连几天,我们在西班牙北部跋涉,夜行日藏,地里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
1942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间牛棚安身,又冷又饿,只有一个在泥地里找到的胡萝卜。
这是过犹太圣节的时候了。往昔的记忆向我涌来,我倚着父亲的肩膀,忍不住含泪说道:“我们连犹太圣节都没有蜡烛!”
“怎么会呢?”父亲回答,“我们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大烛台,它是上帝赐予的。”说着,他把牛棚的门拉开一道缝,我往缝外窥望,只见黑天鹅绒的天空里繁星闪烁。“挑一枝烛心。”父亲轻轻地说,“要最亮的。”
我费了好一会儿才选中了最亮的一颗星星。父亲又说:“再选出另外八颗分地。”我想象着家里的大烛台,选择了烛心周围的星星。我们“点燃”了第一颗星,然后关上门。
“谁有陀螺?”父亲问。然后演戏似的把手放到身后。又很快拿出来,说:“来,玩吧。”
我们围坐在一处,父亲拿出那个胡萝卜,把它放在中间我伸手抓住假想的陀螺,装作是为我和弗兰西斯转陀螺,当我“放手”时,大家仿佛都屏住呼吸,注视着它朝哪边倒。
“莫特尔,你赢了!”父亲说着,隆重地把胡萝卜递给我。弗兰西斯的眼里闪着胜利的光芒,大人们装出失望的样子。就像以往那些幸福的日子里一样。
这个几分钟前象征着饥饿的胡萝卜,忽然变成了一件奇妙的奖品。我接过它,像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一样,掰成几小块,分给全家人:我咬着我的那份,甜得就像小时候吃糖似的。
当我钻进草堆睡觉时,内心充满了欢乐。我从一无所有到拥有整个世界,包括希望和爱这些难以数计的财富。以坚忍和信念渡过逆境,这就是犹太圣节和那奖品的意义所在,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
终于,我们到达边境。在葡萄牙的难民所呆了几个月后。美国的朋友给我们搞到了入境证1943年8月23日,我们来到费城。学会了英语,开始新的生活。好多年过去了,我结婚成家,取得硕士学位,成为外语教授,现在我已是四个孩子的祖母了。但我继续像父亲教的那样,把珍贵的时刻装进我的那只瓶子。
莫特尔 周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