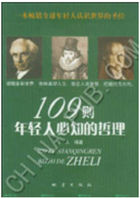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会忘记您。因为那一夜之后,他便乘船出国作战去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美国东海岸波士顿市一位叫温纯格的男子,去年夏天独自一人驱车前往西海岸,在途经伊利诺伊州的公路上时突然出了车祸。当他醒来时已躺在一座小城市的医院里。在这座小城里,他举目无亲——或者说,他自认为是举目无亲。
第二天早上,有关这次车祸的报道登在当地的报纸上。当天下午,一个叫马尔科姆·考文的太太来探望他,但他不记得认识—个叫这名字的夫人。
他说:“你们肯定她是来探望我的吗?这儿我可是一个人也不认识。”医院的人回答得很肯定,于是,客人被领进了病房。同她一起进来的那个小男孩是她的儿子比利。她颇有点自豪地说:“我想您会高兴见到他,护士说带他进来不碍事。”
接着她又急切地说:“您还记得我吗?我可是非常清楚地记得您——我和我丈夫永远也不会忘记二战时在纽约的那个晚上您的大恩大德。在那家旅馆里,还记得吗?”
他顿时想起来了——这让他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刚才她那张消瘦、年轻的面孔,那双湛蓝的眸子之所以让他觉得有些面熟,是由于他感觉这张面孔看上去与其他类似的面孔有些相像而已。但现在,经她这么一提醒,他认出了这张脸,想起了那家人满为患的旅馆,那个在服务台前排队的中尉。
那天下午,温纯格办完登记手续后,住进了这家旅馆。因为他是这家旅馆的常客,所以没费什么工夫便订到了一个房间。把行李搬进楼上的房间之后,他便下楼来到大厅,买了一份当天下午的晚报,坐在一张沙发上读起报来。
因为是战争时期,所以如同往常一样,服务台前排着一长队等待登记住宿的军人。温纯格偶尔抬起头来看看,不知不觉地竟对那众多陆军军官中最年轻一位的命运发生了兴趣——这位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塌鼻梁的陆军中尉,一次又一次地,十分温和地把自己靠前的位置让给军衔比他高的军官。
“这可怜的孩子,看样子是永远也到不了服务台了。”温纯格自言自语地说,终于,当他最终挨到了服务台时,却被告知已经客满。一听这话,那位年轻的中尉眼看就要哭出来似的。“求求您了!”他哀求着那位板着冷冰冰面孔的服务员,“我从今天早上九点钟便一直在找住宿的地方啊!”但这无济于事,答复仍旧是没有多余房间。中尉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了。
温纯格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他走到中尉面前,告诉他自己那间客房很大,有两张单人床,问他愿不愿意将就着在他房间里住一宿。中尉说:“先生,谢谢您,可我还带着我妻子呢。”他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面坐着一位纤弱的女子,瘦削的脸庞,湛蓝的眸子,脸色苍白而憔悴,风尘仆仆,样子十分疲惫。
温纯格大步流星地走进旅馆经理的办公室,为可怜巴巴的小两口说情。经理不耐烦地说:“我知道,可眼下这种情况多着呢,温纯格先生。我也觉得他们怪可怜的,但我这儿确实再也没有空房间了。”
“那好吧,你就在我房间里再支一张行军床,”温纯格说,“让他们同我住在一起。你这儿一定有备用的行军床——和用来把房间隔开的屏风吧?”
这异想天开的想法让旅馆经理大吃一惊——这可是有违惯例的,因此他绝不松口。最后,虽年近四十,但有时也会脾气火暴的温纯格忍无可忍,扯开嗓门叫嚷着:“你们反对这样做,是不是以有伤风化为理由?如果是的话。”沮纯格继续吼叫着,“那么你们这旅馆的人全是一些伪君子!”接着,他带着一丝威胁的意味说他能够证明这一点,并说他知道这家旅馆的底细,等等,等等。
他大吵大闹,弄得经理神经紧张,惊慌失措。如果能让温纯格平静下来,这位经理恐怕付出什么代价都心甘情愿。因此他突然灵机一动,很圆滑地说:“噢,温纯格先生,你不是说这位女士是你的女儿吗?(温纯格压根儿就没这么说过)哦,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许可以照你的要求去做,就算是一种特别的照顾呗。真遗憾,你怎么不早些提到这一点呢。”
形势立刻急转直下——中尉和他的新婚妻子被领到楼上温纯格先生的房间里。在看到一张行军床和一扇屏风被安置妥当之后,温纯格交给小两口一把钥匙,并告诉他俩,他需要出去吃顿饭,然后去看戏,恐怕午夜之后才能回来。回来后,他会悄悄地进屋,睡在屏风后面的那张行军床上。
温纯格一丝不苟地履行诺言,直至午夜过后许久才回到旅馆。他蹑手蹑脚地摸黑走到行军床前。
早晨醒来时,中尉和他的新娘已经离开了。很显然,他们俩只在一张床上睡过,尽管他们很谨慎,故意把另一张床稍微弄皱了一点。枕头上面放着一张留言条,对他表示非常,真的是非常地感激,说他的心地是如此的善良。
如今,七年过后,在美国中西部这座小城里,这间四壁灰白的病房里,当年那位女子又一次向他表示感激之情,并给他带来了一大束自己种的鲜花。那个小男孩把这一大束鲜花抱在怀里,颇有些自豪。这男孩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一个塌鼻子和一头鬈发。温纯格微笑着说:“你看上去可真像你的爸爸。”
“是啊,他很像他父亲,对吧?人人都这么说。”这位母亲高兴地说。
“我还忘了问,您丈夫好吗?我想,现在我不能再称他为‘中尉’了吧……”
话一出口,温纯格意识到,她的目光顿时黯淡了许多,但嗓音还是镇定的,仿佛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才做到了这一点。
她只是说:“他没有回来,在霍特金丛林中阵亡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永远忘不了您的恩德的另一个原因。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会忘记您。因为那一夜之后,他便乘船出国作战去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美]凯瑟琳·布鲁斯 王焕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