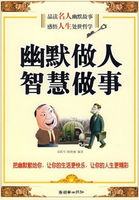忽然他显得很幸福的样子,说:“但是爸爸还能笑呢。”
1995年5月的一天,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我在弗吉尼亚州参加马术比赛,我骑的那匹马在跨越第三个障碍时突然收住了马蹄。这样,惯性使我的身子前冲,越过马头摔了下去,然而我的双手不巧缠在了缰绳上,我腾不出手来平衡自己,头朝下着地。我身高一米九,体重近90公斤,就是凭着这样的身子骨,我在电影《超人》中扮演超人而一举成名——然而,这样的分量头朝下着地的后果可想而知。我当即全身失去了知觉,像一个淹没在水里的人快要窒息而亡了。
5天后,我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弗吉尼亚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神经外科主任约翰·简告诉我,我的第一及第二节颈椎已经折断,能活下来算是万幸了。他还说,我可能再也不能够正常呼吸了。所幸的是,我的脑干,也就是紧贴受伤的部分,似乎没有受到影响。简说,我的颅骨和颈椎要动手术才能重新连接到一起。他不能够确保手术一定能成功,甚至不能确保我能活着离开手术室。
我突然意识到,我成了每一个人的负担,我不但毁了自己的生活,也毁了别人的生活。为什么不死呢?这样一了百了对大家都有益。
家人和朋友不断地来医院探望我,但那段日子我沮丧透顶,总是躺在那里,盯着墙壁,想着未来,难以相信还会有什么好的未来。只有在梦中,我才又成为一个完好的人,同妻子丹娜亲热、骑马或拍电影。醒来后我更加感到沮丧,因为梦中的一切我是一件也干不了,我只是一个占据空间的废物。
一天,丹娜在我的床边时,我有话对她说,但我戴着的呼吸器让我不能启齿,我用眼睛告诉她:“不要救我,让我走吧。”
丹娜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哭着对我说:“不管怎样,我都会永远和你在一起。”随后她又加了一句,这句话打消了我轻生的念头——“你还是你,我爱你。”
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我变得越来越害怕,因为我知道这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大部分时间我都僵直地躺在床上,悲观地胡思乱想。
可是我3岁的儿子威尔给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一次他对丹娜说:“妈妈,爸爸的膀子动不了呢。”
“是的,”丹娜说,“爸爸的膀子动不了。”
“爸爸的腿也不能动了呢。”威尔又说。
“是的,是这样的。”
威尔停了停,有些沮丧,忽然他显得很幸福的样子,说:“但是爸爸还能笑呢。”
6月5日,我接受了手术。手术很成功。
感恩节前夕,我终于完全摆脱了呼吸器,出院回家了。在感恩节的晚餐上,一家人都按照传统说了几句感谢什么的话,而我的儿子威尔只说了两个字——“爸爸。”
〔美〕克里斯托弗·里夫 邓笛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