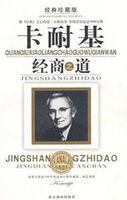比利在新墨西哥州的土地上,在亲人的环绕中闭上了眼睛。他原本很可能死在医院冰冷的急救室里,然而现在,在所有爱他的人的注视下,他慢慢走向了天堂。
有人说住院医师这一群体正趋向年轻化,这些人精力更充沛,更容易冲动,不太成熟,更加理想主义,不过正是这些品质使他们较之那些高龄的、技术纯熟的医生来讲更有人情味。我正是这些年轻医师中的一员。我在波士顿的一家医院任住院医师,我的一个病人是5岁的比利。他患晚期癌症,即将告别人世,每天都要忍受高烧和疼痛带来的折磨。比利一家住在新墨西哥州,来波士顿是他母亲的主意,她希望为孩子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残酷的现实告诉她这是无用的。比利虚弱极了,我们都觉得他随时会死去。
比利最后的愿望是在新墨西哥州的家乡与家人度过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作为一名医生,我知道从波士顿到新墨西哥州的旅行对于比利这样的患者来讲充满了危险,他需要一名医生时刻在他身边观察他的情况,为他注射麻醉药以缓解疼痛,同时还要不停地为他打点滴。而且,比利的父母已一贫如洗,根本支付不起机票费。尽管我对这次旅行充满怀疑,但比利的病情已不允许我再反复权衡,我决定陪伴比利一家踏上回家之旅。我知道我有点冲动,带这样一个重症病人旅行简直是发疯。我知道我是被比利心中回家的希望感动了,那希望是闪烁在这段生命结尾的最后一点光芒。医院方面很快找到了资助这次旅行的资金。比利苍白而痛苦的脸庞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但是,由于比利严重的病情,我们一行人被拒绝登机。不论我做任何解释,比利的病情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挡在我们与飞机之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晚来临了,但我们仍滞留在机场。我担心我带的麻醉药快不够了,没有这些药比利会非常痛苦。我请求机场将我们送到离这里最近的一家医院。怀抱着如此虚弱但渴望回家的比利,身边是身无分文的比利的父母,我记得我当时很绝望。“比利,我没法带你回家了。”我自言自语,“我太年轻,大没有经验。”
但是,我们所到达的那家医院的医护人员重新为我燃起了希望。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完了我们的故事后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一切为了比利的希望。我从没见过这么善良的人们,为了减轻比利的痛苦,他们用尽了所有贮备的麻醉剂。但我们还是无法上飞机。
我担心比利可能等不到回家的时刻了。有几次我听不到比利的心跳了,我以为他死了。但过一会儿,比利又有了呼吸,他微微张开眼睛,仿佛在告诉我,他会坚持,直到我们踏上家乡的土地。冥冥中,我感受到了这脆弱生命中仍蕴含着强烈的希望,比利回家的希望给了所有为他忙碌的人们一个支点。“我们不想看到比利被装在骨灰盒里带回家。”一名医生在为比利注射时对我说。
但机场仍拒绝我们登机,由于这家医院靠近机场,这里的医护人员也曾遇到类似的情况,他们很有经验。“也许班顿医生的私人飞机可以帮忙。”一名护士冒出一句提议。那时是凌晨1点钟,班顿医生在听完这段故事后立即从家里赶到医院。
很快,比利的父母乘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新墨西哥州,我和比利则登上了班顿医生的私人飞机。飞机腾空而起,我怀抱比利融入夜色,周围是满天繁星。那一刻,我心中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我在带着比利飞向天堂。“我们要去哪儿?”比利问我。“你要回家了。”我轻声地对他说。
接近黎明时,我们到达了新墨西哥州的阿尔波克其。地面导航塔指挥班顿医生的私人飞机在比利父母乘坐的班机旁降落。飞机着陆后不久,比利在新墨西哥州的土地上,在亲人的环绕中闭上了眼睛。他原本很可能死在医院冰冷的急救室里,然而现在,在所有爱他的人的注视下,他慢慢走向了天堂。
一周后,比利的母亲为我寄来了一张比利墓碑的图片,上面的铭文是“是爱与希望把他带回家”。
张岩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