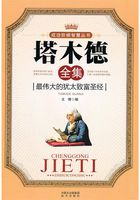一
我是个印第安人,生长在中美洲一个叫大山谷的小镇。镇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靠山吃山。因此,在我离开小镇之前,世界就是门前的大山。
虽然每年都有城里人来收购人心果树胶,拿去做上等的口香糖,但他们总是寒也匆匆,去也匆匆,从不和我们多说一句废话。可是,有一年,一个叫卡门的小姐改变了这种传统。卡门小姐是我这辈子所见到的第一个城市女性。可是她并非树胶商,她是到山区来体验生活的演员。山里的孩子们像看马戏似的跟着她从镇南跑到镇北。我远远地看着她,更确切地说是窥视她跟镇里半遮半裸的妇女搭讪,并不时地用一支硕大的钢笔做斯文的笔记。姑娘们乘机围观。于是,我恨自己是个男人。树胶商到达大山谷的第二天,镇里照例办起了集市。家家户户在门前扯起一块大白布,再用鲜艳的颜色在上面写上树胶的品种和价格。中心广场的露天舞台照例举办一年一度的赛诗会,小伙子们总要借这个机会显示自己的才华并向心中的情人表白内心的渴望。为了不让卡门小姐失望,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居然得了个并列第一。可是,很快我就后悔了。因为应邀出席颁奖仪式的卡门小姐首先代表镇长给名列第三的瘸腿胡安发了奖,而且还很有风度地握了握瘸腿胡安的手(那是一只脏不可耐的手啊)。而给我和另一位获奖者颁奖的却是镇长本人和他的太太(一位身量肥硕的半老徐娘)。于是,我又恨自己得了第一,甚至恨自己不是瘸腿胡安。卡门小姐在镇上待了四天,我就痴痴地睁着眼睛梦了她四天。
二
但是,生活是会发生奇迹的。有一年,国家土著中心派人来物色歌手,我居然被选中了。他们把我带到首都,安置在一听叫圣彼得罗的大学里。也许你不知道,在这之前我从未上过学。老师们对我的处境感到十分尴尬。“一个赛诗会冠军怎么可能是文盲呢?”但事实就是如此。难道我们祖祖辈辈不是这样过来的吗?用镇长的话说,吟诗是我们的本能。无论情况如何,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只凭本能生活的大山谷去了。因为本能告诉我,只要我不离开首都,早晚能见到卡门小姐。可是,日子过去很久了,我除了偶尔在报刊或电视上看到卡门小姐外,她的出现只是一个了无着落的梦。
就这样,我在大学里苦苦地坚持了一年,等待了一年,直至被告知学习期满准予结业。我想我什么也没有学到,惟一值得安慰的是懂得了世界的大小。一天,在另一个印第安人怂恿下,我终于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那一步:花一千个子儿偷渡到墨西哥边境,再从墨西哥边境偷渡到北边的佛罗里达。
早听人说北边的娘儿们风骚,果不期然。到达那里的第三天,我就被一个叫南希的娘儿们给缠上了。她白天把我当佣人,当晚就要把我当情人。我扭头就跑,心里直觉得恶心。好在我天生运道不错,据说还很英俊,不久又找到了差事。只是类似情况不断发生,害得我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仿佛上帝有意拿我开玩笑,试探我对卡门小姐是否忠心。
三
既然这里不适合我,不如早点打道回国。但我囊中空空,撺掇我到这儿来的人又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我天天在机场转悠,指望有试飞的航班让我免费搭乘。
有时,某位旅客让我提个箱子什么的,赏我两个子儿填填肚子。就这样,一晃我就在机场转悠了十几天。忽然有一天,卡门小姐天使似的降临在这个机场。她风尘仆仆,还是那么漂亮。虽然已有细细的皱纹从眼梢放射开来,身段似乎也略显丰满,但这使她更透着成熟,透着丰韵。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你怎么会在这里?”她和善地问。
“我……”我支吾了半晌,不知说什么才好。
“是转机吗?”她又问。
“嗯。”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她似乎只注意到了我前面的表情,问是什么时间的飞机。
我只好将错就错,回说是明天。没想到她说:“我也是明天的飞机。”
“晚上准备在哪儿过?”这时她又问。
我犹豫片刻,小声说了个不知道。
她看了看表,说时间还早,不如一起去吃点东西,然后找个地方住下。
我本能地点了点头。
我们一前一后出了机场,上了一辆大巴。这时,她忽然发现我没带行李。我随即撒了个谎,说寄存了。她于是笑吟吟地说:“还是你聪明,瞧我背着这么个大包。”
我这才想起,男人得有绅士风度,于是赶忙抢过背包背在肩上。她一再表示感谢,说:“想不到你还这么绅士。”
我心里美滋滋的,甭说有多高兴。
接下来是下车、吃饭和找旅馆,统统由她付钱。有一次,我实在不好意思了,就推说钱包忘在旅行箱里了。“谁付都一样。”她很慷慨地抢着支付了所有费用。
四
旅馆的前台小姐不时地在卡门小姐和我脸上瞥来瞥去,瞥得我心里发懂。这时,卡门小姐回头对我说:“不如咱们合用一个房间吧,这样比较省钱。”
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简直不敢相信。
“行吗?”她见我没有反应,又回过头来追问了一句。我赶紧点了点头,过后就刷地涨红了脸。
好在她什么也没有发现,倒是前台小姐抿嘴笑了笑。
就这样,我俩住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床,卡门小姐问我喜欢哪一张:“靠窗这张,还是……”我立即指了指窗边那张,因为当时我心跳得都快要窒息了。
卡门小姐于是让我把背包放在她的床上,然后对我说:“你先洗吧。”
我回了声“唉”,就顺从地进了洗漱间。我在洗漱间里呆呆地忙活,除了兴奋,脑袋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卡门小姐在外面轻轻地敲了敲门。“怎么啦?睡着了吗?”
“没有,没有。我这就出来。”
她在门外格格地笑了起来。我不知她在笑我还是笑电视里的什么人物。等我穿好衣服回到卧室,她已经穿好睡衣钻进被窝了。见我出来,她连忙欠起身来,说:“我以为你在浴缸里睡着了呢。你瞧这电视里的丈夫,被妻子关在厕所里……真有趣。”她边说边起身朝洗漱间走去。
我望望电视,又望望她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是什么滋味。我尽量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低,竖起耳朵倾听她洗澡时传出的各种细小的声音。我还踮着脚,悄悄走到门口,透过针眼似的门缝朝里窥探。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看见,倒被洗澡时突然哼起曲子的卡门小姐给吓了一大跣。我立刻溜回床边,心绪纷乱,胡思乱想,不能自己。
我直想得口干舌燥,随手拿起桌上的杯子,把里面好像是苏打水之类的液体喝个精光。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的时候,卡门小姐已经穿好衣服化好妆,准备出发了。我不明白此前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脑袋沉沉的,浑身不舒服。
卡门小姐见我醒来,就格格地笑个不停。我以为自己无意中做了什么不礼貌但分明又是处心积虑的事。
“睡得怎么样?”她笑着问道。
“不怎么样。”我一不小心叹息说。
“你偷吃了我的安眠药,”卡门小姐笑得更欢了,“害得我一晚上没合眼。”
我又情不自禁地深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我应该事先告诉你的。”她边笑边内疚地说。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叹息。
因为要回机场赶飞机,卡门小姐到前台匆匆地结了账,然后又匆匆地带我坐上了机场大巴。临别,她像老朋友似的向我挥挥手。说:“再见了,年轻人。”就这样,我们彼此连一个指头都没有碰着。
我目送卡门小姐进了候机厅,既幸福又懊悔。
五
从此以后,我一直梦想再次遇见卡门小姐,并决心从此忠实于卡门小姐,无论别的女人怎样挑衅,也无论瘸腿胡安如何以曾经握过卡门小姐的手而沾沾自喜,我默默地干活,然后憋足了劲儿参加一年一度的赛诗会。我用我的全部感情讴歌卡门小姐过人的美丽、超凡的演技(尽管我对她的表演艺术一无所知)。
然而,有一年树胶商带来了面目全非的卡门小姐。据说是车祸使她丧失了两条肋骨和一只眼睛。她面部抽搐,表情痴呆,跟随树胶商长途跋涉,只为见我一面,她感谢我对她的思念和赞美。我完全愣怔了,然后失望,甚至绝望地当众痛哭了一场。
这时,卡门小姐向我伸出手来,而我却胆怯地把手缩了回去并绝情地扭头跑开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卡门小姐是在两天之后。她容光焕发鲍再次来到我的面前,面对无颜以对的我,她一如既往地和颜悦色,问:“我演得如何?”我这才回想起两天前的情景和人群里那台该死的摄像机。
[巴拿马]胡安·阿维拉 陈众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