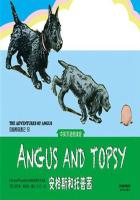密林里的野兽考察组通过对群众的访问和地形的分析,决定分组进行工作。
紫云山山体大致从西南逶迤向东北而去,地处五县之中,最高海拔有一千八百多米的紫云峰,顶天立地,是矗立于我国东部疆域高峰中的佼佼者。
高山的地势,大抵可从顶天冈划分为前山和后山。动物与地形、景观有很大的关系。王陵阳他们把整个山区划分成了四个区域,兵分两路:李立仁和张雄跑前山,王陵阳和尽可能参加的罗大爷在后山。先遍地撒网,然后再紧紧收缩。
李立仁和张雄先在前山东区工作了几天。紫云山号称有七十二峰,其实,山中有山,峰中拔峦,层层叠叠,何止七十二峰!他们经常是艰难地登上一个山峰,又要小心翼翼地下到谷底。还不断被断谷拦住去路,被峭壁隔绝,只得再折回,沿着山坡找路,成天上下起伏。
天刚微亮,他们便出发转向西区。每人背着沉重的爬山包,沿着一条深谷,一步步向来仙峰登去。李立仁对张雄说:
“来仙峰与谷底的相对高差较大,植被垂直分布明显。从山脚到山顶,就像是一本不同气候带的植物图谱。由马尾松林带,逐渐到高山草甸、苔藓地区。这是一本实实存在的自然植被书,需要认真读,仔细看。”
前两天,李立仁已指导张雄观察了海拔较低的马尾松林带。现在,经李立仁一提醒,张雄喘着粗气,开始注意山岭上的树木,发现大多是常绿乔木、落叶的阔叶林和常绿的阔叶林。他为了辨别树木,确实付出了艰苦劳动。
张雄自小生活在大城市里。那几年的中学生也没有学到动、植物知识,还是近几年才认得一些常见的树,至于如何辨别落叶与常绿,这要在冬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是现在万木葱茏,他只得学习、询问。
王陵阳曾一再对他说:
“科学是实实存在的。学习知识,从事科学工作,更应该实事求是。你们上学时基础没打好,要在这次难得的野外工作中勤奋学习,不懂就问。我已和李老师谈过,要主动帮助你。假如可能的话,我们非常愿意一下就把所有的知识都告诉你,但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学习的过程。只要你勤奋学习,是可以缩短这个过程的。
“这么多年科技人才青黄不接,极需要你们迎头赶上来!养动物其实并不简单,学问深着哩。我们现在这种只供欣赏的动物园应当改变,也应该把它办成科学实验的场所。”
对于这次邀请张雄参加考察“云海漂游者”,王陵阳和李立仁也是经过多次、反复考虑后决定的。一方面,因为他是现在可以找到的、唯一见过紫云山大猴子的人;另一方面,从他拜访王陵阳以后,就比较注意学习动物学的知识;还有,就是他们早就想建立一个实验性的动物园。
在学校里创办困难较多,而把动物园改造一下却是可能的。它既可作为科研基地之一,又可以在展出中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同时,进行动物学的科学普及教育。
带出张雄,可以在实际工作中提高他,再选择适当的时间,让他系统学习理论,一步步将他培养成为动物园的科研骨干。
李立仁看张雄这几天对野外工作很勤奋,心里非常高兴。张雄天未亮就得起来上山,直到晚上才回到住地。吃了晚饭,还要在灯下解剖采到的动物,有的制成标本,直到深夜才能休息。
他们正艰难地走着,一股有力的强风迎头吹来。李立仁抬头一看,只见一片雨云快到头顶。还没有找到躲雨的地方,雨就哗哗地下起来了。张雄还在一条流向山谷的小溪另一边,也只得就地找块岩石躲雨。
雨点打在岩石、树的枝叶上,激起了一片片雨雾。千重山、万重岭像是画家大写意的泼墨,浓妆淡抹,群山显得更加雄伟、秀丽了。
群山飞泉了,银练闪闪,水声争鸣。急涌的溪水从陡壁上跌落下来,成了一条条的飞瀑。
隔开李立仁和张雄的小溪,原来只有一线淙淙的溪水,现在已是急流奔腾了。
可这雨来得急速,去也匆匆。云过天开,阳光灿烂。
这个高山气候的小小玩笑,可给他们两人找来了麻烦。张雄几次涉水过溪,都被急流挡了回来,在最后一次,还摔了一跤。
溪水并不宽,只要狠狠跨两步就过去了,可是水冲得人的两腿总是感到发飘。山势又陡,人一跌到水里,水就要把人冲走,到了山谷处就是飞瀑。观瀑是种赏心悦目的乐事,可是人从飞瀑上落下,那就不会令人高兴了。
身材魁梧的张雄,一筹莫展地站在一条小小的溪流对岸。
李立仁用短刀砍来一根粗树枝,要张雄紧紧地抓住,才把他渡过来。
这场雨使他们的行动更加困难了。可是,李立仁仍然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并不时地观察植被情况。张雄有些沮丧,两条腿像是有千斤重,特别是刚才不在意扭了一下腿,现在竟也和他作起对来。
李立仁向他发出了信号:停止前进,就地隐蔽。张雄看李老师在侧耳倾听,凝神注视着左下方的一片灌木林。他虽然什么也没有听到看到,还是放下爬山包,从肩上拿起了枪,隐蔽到一棵树后。
李老师正端着枪,往他刚才注视的地方悄悄地走去。灌木林里静悄悄的,他每走两步就停下来观察一会,好像在设法寻找有利的射击地形。
树林中也有一对眼睛在瞪着李老师,这只野兽把自己的全身都隐藏在茂密的树叶和野花中,一动不动。它竖着尖耳朵,机灵的大眼注视着李立仁的一举一动。
李立仁又等了一会,灌木林里还是一丝动静也没有。他故意放重了脚步,狡猾的野兽依然一动也不动。
张雄端起枪,注意着野兽可能出现的地方。
李立仁只得继续向前探索,他已考虑到,要么就是刚才没有听准,这不太可能;要么这个野兽就是极端狡猾的……隐藏在灌木丛中的野兽,大约已弄清了对方的意图,于是,那双眼睛在树叶中消失了,“哗啦”一声,撒开四蹄就跑。
灌木太密了,李立仁根本看不到野兽,只是从纷乱的树枝的哗哗响声中,知道它已跑了。他放开脚步就追。眼看距离正在逐渐缩短,野兽却突然来了个大转弯,直向张雄埋伏的地点奔去。就在野兽突然大转弯的时候,暴露了它一部分身体,这更激起了李立仁的劲头,他加快了步伐。
张雄一听野兽是朝着自己这里奔来的,立即举枪瞄准,大约是立式不舒服,他又迅速地跪下了一条腿。
已经能看到野兽奔跑时拨得树丛乱动,却见不到它的身体。那狡猾的东西似乎猜透了对手的心思,就是紧紧地依靠树丛遮掩身体,尽量不暴露。
张雄看看野兽已到了自己的射程内,紧张地瞄准,瞄准线随着晃动的树丛而移动。它不离开树丛,是无法射击的。虽然大致能判断出它的位置,连发两颗子弹也完全可以打中目标,但是,茂密的树丛将挡住子弹,使子弹射到野兽时已没有多大力量。他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好的时机,希望它离开树丛,哪怕是跃起的一刹那也行……几只很大的黑蚂蚁,不知什么时候已爬到他的身上,又爬到他的脖子上。张雄动也没动,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瞄准线上。
李立仁眼看难以追上,捡起了一块石头,砸到下面,引起了很大的声响。野兽急忙向前飞奔,准备向山上奔去。
枪没有响好,正好!野兽在两片树丛中露出了身体的斜侧面。张雄及时扣动扳机,可是扳机不动;他又使劲扣,还是扣不动。野兽棕黑色的毛衣消逝在树丛中了,张雄头上沁出了大滴大滴的汗珠。
李立仁一反常态,老远就嚷开了,声色俱厉:“怎么不开枪?”
张雄没有答话,只是低头紧张地检查着枪支。什么都很正常。他又取出子弹,也未发现问题,可是,扳机就是扣不动。
李立仁奔来了,满脸都是乌云。他抓过枪一看,原来是枪身和木托衔接着的上方,有个插销的一头脱槽,一头伸出来了。他不自觉地瞟了一下商标:“齐哈猎枪厂。一九七六年。”“齐哈”,特别是那个“哈”字,正张开它的大嘴,对他尽情地嘲笑。他气愤地把枪一摔,余怒未息:“你昨晚没擦枪?早上也未检查?”
“昨晚我俩一道擦的,今早也检查了。”张雄低声地说。
“这怎么解释呢?”李立仁指了指坏枪。
“可能是刚才过溪时摔的?”
“把枪摔断,也不会把这插销摔出来。我背枪这么多年,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这明显是销子松了。”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情绪逐渐冷静下来,才又嘟囔着,“这不能怪你,是枪的质量不过关,我们事先没检查好。”
张雄用石头把插销往里砸,李立仁说:“没用,砸不进去!只有拆开修,我们没带工具。”
张雄说:“要不,这一枪射去是稳稳的,我装的是零号弹头,连发两枪,不死也重伤。”
李立仁不愿说任何话了。采动物标本,不像采植物标本,这里找不到,在另外可能有的地方再找,它长在那里也跑不了。采动物标本就不一样了,那些长翅膀的会飞,有腿的会跑;即使找到了,采到手也不容易。有时候猎枪里装的是小号子弹,遇到的是大动物;装了大号子弹,跑出来的却是小动物。像刚才这样的机会,是跑几个月未必能找到的,失去了这次机会,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碰到。
张雄满肚子委屈。
从紫云山复杂的地形看来,最好是找一个对猴子有些了解的人做向导。王陵阳听说,新中国成立前,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常有人到这里逮小石猴,专门卖给玩把戏的班子。前两天,他特意带了介绍信到较近的东山分水公社,一边访问群众,做些调查工作,一边请向导。
接待他的公社丁副主任,三十五六岁光景,留着个俏皮的分头,为人很热情。他听完了王陵阳的来意之后,满口答应。
“几天前听说你们来了,正想去拜访,倒让你们占了先,真是对不起。农村工作,就落个忙。‘四人帮’一垮台,科学研究骑着马、加着鞭赶上来了。前几年,你们知识分子受罪,我们贫下中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你们的考察工作,我们一定大力支持,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只是,你问的这野兽、猴子的事,不怕你笑话,我虽是山里生、山里长,还真不如你们晓得的多!我们是大老粗。找个领路、挑东西的,好办!生产怎么紧也要抽出人。要找晓得猴子的人,我马上派人下去摸摸情况,有适合的人,就叫他到你们那边去。”
丁副主任对考察工作确实关心,详详细细询问了考察组的成员、计划,已发现了一些什么情况……王陵阳觉得考察工作也没什么秘密,倒是应该大力宣传,以求得群众的协助,便把行动计划说了。
从丁副主任的话中听出,马上就要个好向导可能有些困难,王陵阳便告辞了。临分手,丁副主任还一再说:
“紫云山范围大,地形复杂,野兽多,毒蛇也厉害,你们可要注意安全。看样子,你王老师是个干起工作不要命的人,这山沟沟里不像办公室,这次找不到,还有下次嘛。有困难尽管讲,一家人,别客气!”
王陵阳今天刚从山上转了一圈回来,一见李立仁和张雄也回来了,很惊讶,按计划,他们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回来;又见李立仁闷声不响地背着两个大包,张雄还在远处一瘸一拐地走着,更吃惊了。
望春连忙去接张雄。
小黑河兴高采烈地跟前跟后,问李立仁:“李叔叔,你们看到什么野物?”
没有回答。
“李叔叔,你们打到什么标本?拿出来看看嘛,还用得着保密?”还是没有回答。这时,他才抬起头,一看李立仁脸上罩着乌云,就把下边的几个“为什么”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李立仁一来就喜欢上了小黑河,小黑河也乐意跟在这个叔叔后面。李立仁可能是因为自己家里有两个都是文文静静的女孩子,一见到活蹦乱跳、一刻也不安稳的小黑河,感到新鲜。小黑河喜欢李立仁,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见面,李立仁非凡的本领就令他崇拜。虽然,这个叔叔不喜欢讲话,但他也不像别人,老是打断他的话。
张雄强忍着痛楚,打起精神,可心里对李立仁的态度很有意见,心想,你自己也承认是猎枪的质量问题,怎么能怨我呢?王陵阳看出两人的情绪都不好,就没有急于问,只是帮助张雄敷上药,让罗奶奶照顾他,就去干自己的事了。后来见李立仁洗了脸,茶也没喝一口,就忙着拆卸张雄的枪,他也奇怪地走了过来,问:
“怎么回事?”
“坏了!”
“特意给了他一支新枪嘛!”
“我也没见过这种坏法!从厂里出来就是次品,唉!”李立仁气愤地叹了口气。
李立仁还在做学生时,王陵阳就器重他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的学习精神,更尊重他默默地工作,从不显示自己的朴实品德。李立仁从不轻易地喜怒于色。因为枪坏了,或者是一支坏枪,也不会是这样,其中一定还有重要情况。
“什么时候发现枪坏了?”
“关键时候。”
“发现了什么?”
“最先没看清。后来,远远地看到了,像是鹿科一类的。”
“身上有没有斑点?这里极有可能分布着华南梅花鹿。”
“没看清,因为距离较远,又只暴露了很短的时间。其实只是一跃,又隐没了。”
王陵阳又问张雄:“你看清没有?”
“我只顾瞄准,没特别注意,有些像只大麂子。”张雄如实地说了当时的情况。
王陵阳思索了一会:“会不会是毛冠鹿?”
李立仁说:“我也这样想过。虽然它只闪了一下,倒是可以看到它的毛色乌黑发亮。不过是迎着太阳光看的,难以断定。”
王陵阳一听此说,立即睁大了眼睛,兴奋得几乎叫了起来:“黑麂!难道是黑麂?”
他急速地转身问张雄:“你说,你看清是什么颜色?”
张雄一点也不明白王陵阳的兴奋和激动,回答时更加字斟句酌了:“好像是个老黄麂的颜色。”
王陵阳一点也不放松:“究竟是黄色,还是棕乌色?”
张雄咕哝着:“两只眼只顾盯在瞄准线上,扳机扣不响,浑身汗毛发炸,哪注意到那么多。”
王陵阳不满意了:“这样说法不对,我们是研究动物科学的,不是猎人。要有一眼就分出毛色、体形特征,叫得出名字,即便叫不出名字也应知道是属于哪一科的基本功。这不行……”
他似乎突然想起了张雄的具体情况,话也就到此为止,否则,后面还有一串话哩!可是,一想到那可能是黑麂,他又兴奋、激动起来:
“黑麂,是我国特有的稀有鹿科动物,生活在高山森林中,别的国家没有!多少年来,已没有见到对它的报道了,很多人都担心生境的破坏,可能已使它灭绝了。
“从文献上看,这里没有发现有关它的记载。我们出的经济动物志上,用的是外国学者三十年代在我国工作的材料。这说明我们研究动物的人,还没有谁采到过黑麂的标本,更不要说对它进行研究了。
“这是落后、无能、耻辱!难道我们再编动物志时,还只得用他们的材料?外国学者先进的东西,我们要学。可这是只在我们祖国土地上生息繁衍的动物,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却没有见过、不知道,只得用四十年前的材料!”
李立仁的感情是埋藏在心底的,王陵阳刚才所说的,他心里也早有一本账。过去,他学习的教材和参考文献中,有一些明明是产在我国,甚至是我国的特产动物,可是,描述的材料,生态学的研究,用的却是外国人的研究成果。每次,对他的心灵都是一次刺伤。
他也常常思索其中的原因:在旧中国,黑暗腐朽当然要落后,要埋没人才;新中国,应该有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自己的老师,其中大多数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新中国的科技人员,是在旧社会挣扎过来的,是在老一辈科学家辛勤教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王陵阳就是他所看到的当中的优秀代表。看来,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有更大的发展,就有更宏大的队伍。自己是这队伍中的一员,需要做到的,就必须做到。另一方面,他也考虑到,动物学研究对象———动物标本的难以采集。除了专业知识外,还需要一个优秀猎人所具备的本领。正是因为要把这些空白填补起来,他放弃了别的兴趣,决心像王老师那样,甘愿做个科学征途上的铺路石子,努力去研究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为了这一工作,他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经受了特殊的锻炼。
李立仁低沉地说:
“前两年,我见到一份材料,介绍了一个外国客人参观我国一个大的动物园,说是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向他介绍了黑麂。我心里一惊,虽然黑麂在我国分布面并不太窄,但还没有一个动物园饲养黑麂,除非是最近有所进展。幸而文中有幅照片,我仔细地看了,那不是黑麂,是毛冠鹿。尽管照片是黑白的,又不太清晰,但从头部还是能看出,它千真万确是毛冠鹿。”
王陵阳在房里踱来踱去:“真丢脸!”
停了一会儿,又说:“动物园的现状一定要改变,要有优秀的动物学工作者去担任领导工作。”
张雄听了他们的谈话,才明白了问题的重要性,委屈的情绪稍稍消了一些,但转而一想:我毕竟只是个饲养员,既不知道这些,更没估计到枪的质量有问题,你们何必这样要求?他正想着,突然听到王陵阳对他说:
“刚才说的,你都听到了,是黑麂、不是黑麂,就要在那一瞬间确定下来。在科学上,这一瞬间是多么宝贵!再要碰到这一瞬间,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我注意观察了这里的生境条件,有极大的可能出产黑麂。今天虽然未能揭穿这个秘密,但只要有,总是有机会的。已过去的事,总结教训吧,更何况这是枪的质量出了问题!”
“我有责任!”李立仁没有原谅自己。
张雄听了,心里仍然不是滋味:“我……我……”嘴张了几次,却没说出下文。
王陵阳安慰他:“多想明天的,但要记住昨天的。”又对李立仁说,“想办法换个插销,既然是松了,勉强装上去,关键时候还可能出毛病。这些年各方面的生产都被‘四人帮’搞得一团糟!”
望春瞪着大眼坐在旁边听着,连喜欢咋呼的黑河也未插一句话。大人们的话,在这两颗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反响。这些新鲜有趣的知识,像股清泉流过他们的心田,滋润着理想的种子。
猴尖歌唱了一天的鸟儿都静下来了,森林还在不时地卷起一阵阵的波浪,就像是遥远的海波发出的涛声,低沉、雄浑。溪水潺潺地流着,像是缠绵的低声细语。高大的群山黑森森地立在人们的面前。
张雄闻到一阵清香,分辨不出是什么样的香味,可是呼吸了这种香味,就感到温暖。他又听到了咕嘟咕嘟的水声,这才看到罗大爷正端起茶壶向杯子里倒茶。
“好香的茶!”张雄惊喜地说。
罗大爷嘿嘿地笑了:“让你们尝尝新!”
王陵阳和李立仁听这样一说,连忙端起了茶。李立仁刚呷了一口,觉得有股醇醇的清香沁人心脾。他又呷了一口,满口清爽,只觉得鼻息里出来的都是幽兰的香味。
李立仁说了声“好茶”,然后又深深地喝了一大口,立刻感到回肠荡气,浑身的疲倦都消散了,全身的筋络都舒松了。
王陵阳也细细地品了茶,长期大量抽烟卷,使他的味觉不是那么灵敏,但这股茶香,还是令他口舌一新。喝了几口以后,愈来愈感到茶的芬芳、醇厚,他问罗大爷:“这是新茶?离谷雨没几天了吧?”
“你们来时,月儿没圆。今晚,到这时月亮还未上山,离谷雨也只有几天了,”罗大爷按照他的计算方法回答,“谷雨前采高档茶;谷雨后嘛,茶山就大忙了。”
黑河高兴地说:“过两天就要放茶假了。”
张雄问:“你会采?”
“会!谁不会采茶?不吹牛,真的。”
王陵阳说:“难怪了,我们喝的原来是紫云山的名茶。”
“俺摘了点野茶,做工又粗,乐得个新。配上了这好山水,你们在城里就难喝到了。”罗大爷谦逊地说。
王陵阳说:“读过苏东坡的诗的人,大都记得‘且将新火试新茶’,这新茶就是不一样。”
李立仁还在一口口品着茶:“这茶喝到嘴里还发甜呢!”
“真的,口里凉润润地发甜。”张雄也加以证实。
“茶的老家在云贵高原。我们的先人试制了茶,最早是拿它治病的。”王陵阳一边喝着茶,一边像讲故事般说。
张雄还品不出茶味,只知道好喝,听王老师这么一说,觉得新鲜,不禁问道:“能治病?”
王陵阳说:“是的,茶能益思明目,助消化,正气正胃,可防治坏血病。特别是以肉食为主的牧民,不喝不行呢!过去,有的老中医开处方,还要加上一味茶。”
“俗话说:山高雾浓,茶才香。俺紫云山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好几种名茶都离不了俺这大山。大的有红、绿两系。红茶中的尖子有功夫茶、礼茶。绿茶中高挑的,有火青、炒青。挂金字招牌的有松萝茶。这松萝茶就是王老师刚才讲的,中医要入药的。特别出名的有紫云毛峰、云雾、猴尖……”罗大爷如数家珍。
王陵阳听到“猴尖”,触动了心思,不禁重复了一句:“猴尖……”
“你喝过?”罗大爷问。
“这猴尖产在紫云山的哪里?”
罗大爷没想到王陵阳问的是这事。
“产在猴岭一带,那里有几个生产队。”
“山头可高?”
“不高,是个山崂子,雾气大。”
“怎么叫这怪名字?”
“听老人说,那里原来是猴子窝。”
“现在还有猴子?”
罗大爷还没答话,小黑河抢着开了口:
“有哩,不吹牛,真的。俺班上鹃鹃外婆家在猴岭。前两天,俺说:你们是来找猴子的。谁晓得猴子在哪里,告诉俺。找到了,叫老师给他记一大功。评‘三好’时,俺第一个举他的手,不吹牛,真的。鹃鹃说,她外婆家那里就有,去年暑假还亲眼见到过。俺试她,说她吹牛。鹃鹃说要跟我打赌。”
王陵阳很认真地听了:“她说见到的是大猴还是小猴?”
“俺也问过她。她说啥大猴小猴,俺见到的就是一种猴,有大的,有小的,还说有老的,有少的。她存心气人哩!不吹牛,真的。”
李立仁也问起罗大爷:“这紫云山,还有与猴子有关的地名吗?”
罗大爷默想了一会,说:“有。猴子望海不就是?”
王陵阳和李立仁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在一起商量起来:根据一般的情况来看,地名总是有来历的。“猴子望海”是海拔较高的山峰。“猴岭”的海拔并不太高,刚好是一高一低,再把这两个地方查一下,可能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紫云山大猴的生活规律。
黑河一听说要到猴岭、猴子望海去,就嚷开了:“放了茶假,俺也要去。”
稳重的望春也提出要去。
罗奶奶说:“净瞎起哄,大人去工作,孩子家去干啥?又不是三里五里。再说,你们跟着碍手碍脚的。”
小黑河一听,缠着奶奶说:“俺走得动,不吹牛,真的。俺做不了大事,但能帮李叔叔捡猴子,他打着了俺就捡回来;猴子死在树上下不来,俺还会上树。上次那只野雉就是俺捡的,真的,不吹牛。”
望春说:“奶奶说的不全对。俺不是去耍的,俺要跟叔叔们学知识,找都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哩!”
“哟,这还挺在理的!”罗奶奶被望春那股稳劲说笑了。
“就是嘛、就是嘛!奶奶瞧不起人!”小黑河只管嚷。
“俺今年初二,过几年,高中毕业,俺就去考王叔叔那个大学的生物系,将来也去研究生物学。”望春一本正经地说。
“我接李叔叔的班。”小黑河大声宣布。
这话,把大家全说得高兴起来。张雄看王陵阳和李立仁都笑眯眯地点头,连忙说:
“在近处跟我们跑跑、玩玩还可以,远了可就……”张雄心想,这样翻山越岭,自己都够呛,何况两个孩子?别到时候成了累赘、负担。
罗大爷没正面提这件事,却接过张雄的话,说了两年前的一件事。
石壁下的坐虎那是中秋节的前两天。在黑河他们读书的清溪,有的生产队没栗树。几个大姑娘、小媳妇趁休假日,到风景区外鹞子岭那边采板栗。那里板栗树高大,但不成林,东一棵、西一棵的。栗子个头大得吓人,长得把刺壳都挤裂开,露出它特有的鲜艳、漂亮的红色。画家们专为它起了个名字:栗红。这种大板栗比一般的栗子要甜,不说糖炒了,就是风干了,吃起来都很甜。因为望春兄弟俩在清溪上学,她们经过罗大爷家时,喝了茶。到吃中午饭时,这五六个人满头大汗,神色仓皇陆陆续续跑回来了,有的还没喘过气来就叫:“哎哟,我的妈嘞!就是栗子堆成了山,八人大轿来请,我也不干了。”
问了半天,事情才清楚了:她们正在采栗子时,有个小姑娘看到前面山石下坐了个野物,就叫她嫂子来看。
嫂子见是一只身上长着黄色夹黑色条纹的野兽,正坐在石头下,背靠石壁。
再一看斑斓花额上,有几条黑黑的像是“王”字的花纹,立刻吓了一跳,“啊”地叫了一声。声音刚刚出口,她又赶紧捂住了嘴,脸都变了色,声音也走了调,告诉小姑子:“老虎!”
小姑娘一听就打哆嗦,嫂子到底大了几岁,悄悄地说:“快通知大家,偷偷地走。”
你嘴咬着我耳朵,她脸又贴着别人的嘴,几声一嘀咕,再偷偷瞧一眼坐在那里的老虎,气氛更加神秘而紧张。
大姑娘、小媳妇全都往回走,开始只是快步走,不时回头望望,都恨走得太慢。不知谁由快步变成了小跑,别人一看她小跑,立即快跑,直到撒开脚丫子没命地跑。谁都怕落在后面。
罗大爷有事不在家。妇女们离开罗家一会,望春瞅空拿了爷爷的火枪,不声不响地往鹞子岭走去,他跟爷爷曾去那里采过黑木耳。
他按刚才几个妇女说的路径,找到了那个地方。果然有只老虎坐在那里,虽然是坐着,那样子仍然挺威武。
望春想,自己就这一支火枪,最要紧的是要一枪打中,万一……对,得找个地方隐藏起来,枪一放就赶快转移、装药。要是它没死,追来了,就再给它一枪。只要沉住气、稳住劲,打不死才怪呢。
果然,他找到了一个如意的地方,轻手轻脚地埋伏了下来,趴在石头后瞄准了老虎。他瞄着瞄着,枪头低下来了。
他先捡了个小石子,轻轻甩了出去,石子落在离老虎还有几尺远的地方。被称为兽中之王的老虎,对此不屑一顾,动都没动一下。
不一会,他又扔出一块大石子,落在老虎旁边,它还是不理不睬。
望春胆大起来,随手又投过一块大石头,“吧”的一下打在老虎的身上。它真有修养,就是不动。
望春长长地舒了口气,提起火枪,大摇大摆地向老虎走去。他那一双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老虎,只要它一有动静,就立即叫它吃子弹。
到了老虎的跟前,它还没动。望春看清楚了,老虎的身上全是蛆虫,皮也烂了。望春估摸着老虎在临死前,实在走不得也坐不住,便靠到石头上休息。谁知,这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他用树棍一戳,威风凛凛的老虎像堆黄沙瘫了下来,屁股上还有一支箭。望春想,这支箭大概就是爷爷常讲的毒箭了。这种毒箭,早就不准用了,哪一个还敢这样胡干?可惜虎皮烂得全是大洞小眼,好在骨头还未发黑。他听说虎骨是名贵的药材,就用棍子把虎骨拨拉到溪边洗干净,找了根藤子捆好,挑在肩上,颤颤悠悠地回家去了。
先头,他举起了枪,正在瞄准,要扣扳机,怎么又突然把枪头低了下来?原来是望春犯了疑心。他想:妇女们跑回去,说老虎坐在这里。俺来了,它还坐在这里。俺从那边转到这里,它还是这个样子坐在那里。为啥一动也不动地坐到现在?得想个办法来试试。黑眼珠一转,一个主意就转出来了。
快到家,迎上了爷爷。爷爷是回家看到他留的条子,撵来的。一看望春那副形象,又是生气,又是高兴。
爷爷以后一和人谈到这事,请人喝虎骨酒,就捋着胡子说:
“嗨嗨,这小东西就比别人多个心眼。他哪里知道,老虎死也不倒威哩!老人说过,老虎到死也不躺下,总是要找个地方靠着。倒下架子,要失去威风。”
收购站知道了,动员罗大爷把虎骨卖了。罗大爷说啥也不要钱,收购站只得丢下钱就走,说是不收钱不能要。
事情又传到捡栗子的妇女们的耳朵,几个人又是拍手,又是跺脚,懊悔那时没想到这样简单的事,只顾撒脚丫子往回跑。多数人称赞望春,说是几个大人的心眼加在一起还没他多。
故事说完了,王陵阳把望春拉到怀里,亲切地抚摸着他,可是,却先问小黑河:“去年我来的时候,听你说,有人叫他……”
“五分加小绵羊。”
“这哪里是个小绵羊呢?是逮虎的英雄嘛,真是颠倒是非。现在好了,打倒了‘四人帮’,国家给你们开辟了一条金灿灿的大道。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文化都会有很大的发展。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知道的传授给你们,李老师,你看……”
“欢迎两个小同志参加我们的考察小组!”李立仁说得很肯定。
“我负责照顾他们。”张雄也很愉快地表了态。
王陵阳兴奋地说:“这就一致通过了!”就带头鼓起掌来。
罗大爷、罗奶奶喜得连忙嘱咐两个孩子要听话,要守规矩,特别是一再警告小黑河。王陵阳却说:“我们的小黑河不像过去调皮了,懂事多了,会遵守纪律的。你说是吗?”
“是,不吹……真的。”
大家都笑了。
李立仁知道,王陵阳不是凭着感情冲动作出决定的。过去,王陵阳曾经是科普协会的理事、生物学会的常务理事。那时,在共青团领导下,少先队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登山、游泳、运动会;少年宫的各个课外兴趣小组,还请科学家担任辅导员、举办夏令营……这一系列活动增进了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激发了他们学文化、学科学的热情。
王陵阳曾经和李立仁商量过,想根据生物学,特别是动物学的特点,举办一次以野外动物考察为内容的夏令营,从全省中学选拔二十来个生物科学爱好者参加。这样,既可以让这些学生们了解生物学发展的情况,学习一些基本的知识,开阔眼界,培养对生物学的爱好,又可以从中发现人才,提高中学动、植物的教学水平和大学录取新生的素质。
这个设想得到很多同志的赞同,其他学科的同志都说:“你们先行一步,摸了经验,我们马上跟上。”
谁知,这样美好的计划却不能实现。连少年宫都被批判为“培养精神贵族的黑窝”,被砸烂了。
不久前,他在向李立仁介绍紫云山情况时,提到望春小兄弟俩不管刮风下雨、飘雪下雹子,都要跑上十多里路,到山下的学校上学。那时,他们就再一次想到了过去的计划。
后来,王陵阳又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国外科技先进的国家,早就开始用夏令营和科学俱乐部作为辅助手段,培养专业人才。这使他们又讨论了过去的计划,甚至感到,如果这次执行“云海漂游者”计划中,条件成熟时,就主动吸收望春兄弟俩参加部分活动,为办好科学夏令营,总结一些经验。
王陵阳问罗大爷:“毒箭还留着吗?”
“在。”罗大爷连忙走进厢房拿了出来。
李立仁和王陵阳仔细端详着这支毒箭。从箭杆和箭镞看来,做箭人的技艺很熟练;特别是箭镞,更是要有经验的人,才能使它带上强烈的毒性。华南虎虽没有东北虎那样雄伟的气势,但也是极珍贵的稀有动物。国家早就三令五申禁猎,就算宣传得不够普遍,但这样的猎人是应该知道的。更何况,新中国成立后早就不准用野蛮的地弓、毒箭了,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按一般规律,总是先发现了虎迹,判断出它的动向,然后在可能的必经之路设地弓、毒箭的。虽说是较荒凉的地方,也容易误伤人。这是明知故犯!
张雄从谈话中已听出了问题。问:“罗大爷,有人来找你要虎骨吗?”
猎人有权要回捕获的猎物,这是一般的规矩。罗大爷还未答话,李立仁先说了:“这是犯法的事,他敢来?”
罗大爷说:“李老师说的在理。”
王陵阳问:“你认不出这毒箭是哪里造的?”
罗大爷说:
“这……听说东山那边有几个人会造,大多不在世了。往年,没禁止用毒箭时,箭杆上刻字,猎主好凭它领回毒倒的野兽。为这箭,我也查了很久,总没打听出个头尾,只听说,那个时间前后,有个人在鹞子岭那边转悠了几天。我也疑心,就有心去碰他,偏偏没碰上。”
“遇见他的人,认不得他?”张雄有些不解。
“山大着哩!他有心躲你,远远就闪到林子里去了,这不像在城里马路上。”罗大爷说。
这件事还挺复杂的,都觉得安箭的人不是个简单人物,像是个很有经验的偷猎者,再联系到访问中听到滥捕滥杀珍贵动物的情况,他们感到问题不仅复杂,还很严重。到底是单个的偷猎者,还是有一帮子人?如果是专门偷猎经济价值很高的动物的“高级”山贼,这对他们的考察将是个威胁,对以后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威胁更大!
月儿升上了东山。几只宿鸟不知被什么惊起,扇动翅膀,掠过夜空,向远处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