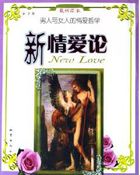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在黑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一些玩世不恭的人更是把所有的哲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愈来愈多的东西知道的愈来愈少,直到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类是对愈来愈少的东西知道的愈来愈多,直刭他们无中生有……
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易传·系辞》
据说有一天,一位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到实验室,向他们展示了一个人身体的物质。这些东西装在一排贴着标签、排列整齐的密封瓶子里。——“这是从前一个名字叫约翰·史密斯的人的全部物质。”教授说。于是,学生们记下了玻璃瓶上的标签:
能够装满一只10加仑圆桶的水;
可做7块肥皂的脂肪;
可做9000支铅笔的碳;
可做2000根火柴的磷;
可打两支钉子的铁;
能够刷一个鸡窝的石灰;
少量的镁和硫磺。
“这一切都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学生做完笔记后说,“但是,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
教授微微一笑道:“回答这个问题是哲学家的事。”
是啊,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他从婴儿到儿童,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容貌、体形、性格、气质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史密斯先生还是史密斯先生,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他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复制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史密斯先生成为了史密斯先生?换句话说,史密斯先生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水吗?不是。是脂肪吗?也不是。当然,它也不可能是碳、磷、铁、石灰和硫磺。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恭喜你!你一旦思考这些问题,就已经进入哲学了。思考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哲学家的专利。我们平常人是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大动脑筋的。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神经错乱的西毒欧阳锋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我是谁?”“欧阳锋是谁?”以前,这个问题不需要问,没必要问,也懒得去问。他是西毒,白驼山的主人,江湖上少有的高手。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现在,所有的这些称号他都记不起来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孤零零的自我,唯一有的就是自我的意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谁?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哲学家。
“延伸阅读”
据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去世后,有一个名叫安德罗尼柯的人承担起了为其整理和编纂遗著的工作。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研究过动植物、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著作更是浩如烟海。安德罗尼柯整理来,整理去,在编纂完《物理学》之后,遇到了一个难题:下一部著作无以命名,因为它探讨的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之中。迫于无奈,安德罗尼柯只好给这部著作起了一个非常拙笨的书名——《物理学之后》。意思是说,这部著作是《物理学》后面的那部著作。再后来,这个词传到了中国,翻译家根据《易传,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将其翻译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即为哲学。
我们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手摸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能感受到的,没什么稀奇,所以说是“形而下”。而哲学研究的都是超越了我们经验的东西。它们或者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或者仅仅能够被我们体悟到。比如,我们看见了一个红的东西,会说:“这是红的。”不错,这个回答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哲学研究的并不是这个“红的东西”,它要研究的是“红”本身。“红”在哪里?“红”是怎么来的?我们谁又见过纯粹的“红”?不相信,你可以在自己脑子里想象一片纯粹的“红”,肯定是无法成功的。因为你想到的,肯定是“红的东西”了。研究“红的东西”是物理学的事情。物理学之后,研究这个纯粹的“红”,就是哲学的工作了。
那只看不见的鸡
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老子
有个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回家后,父亲杀鸡煮酒招待他。吃饭时,父亲问儿子:“你在大学里学的什么?”
儿子回答:“哲学。”
父亲又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儿子说:“学了哲学,看问题和别人就不一样。比如,拿咱们桌子上的这只鸡来说,普通人看来呀,它就是一只鸡,一只具体的鸡。但在我们学过哲学的人看来,是两只鸡,除了一只具体的鸡以外,还有一只抽象的鸡。”
旁边一直听他们谈话的妹妹听了,突然插嘴说:“那好,我和爸爸吃这只具体的鸡,你一个人去吃那只抽象的鸡吧!”
这个大学生说得没有错。哲学研究的对象正是那只“抽象的鸡”!而且,你即使把那只看得见的鸡大卸八块,也找不到这只“抽象的鸡”。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就曾经比喻说:“如果你想把葱皮剥开看看葱的本质是什么,肯定会非常失望。因为即使你把整根葱都剥光了,也不会看到葱的本质。”马克思也拿“商品”举例说:“商品的本质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但是,无论你怎么把玩一个商品,也找不到价值的影子。”
可是,看不见的东西,又怎么去研究呢?正因为此,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善男信女眼里,哲学研究的问题,简直虚无缥缈,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对此,哲学家自己也是承认的。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老子就直言不讳地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看来,如果不能让我们这些“下士”费解甚至发笑,哲学就不配称之为哲学了。
于是有人戏称: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在黑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一些玩世不恭的人更是把所有的哲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愈来愈多的东西知道的愈来愈少,直到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类是对愈来愈少的东西知道的愈来愈多,直到他们无中生有。
“延伸阅读”
无论我们怎么在白纸上摆弄圆规和直尺,估计都无法画出几何学定义中的“圆”。不仅是“圆”,还有“点”、“线”、“面”,只要一被物质载体玷污,这些东西好像就不再纯粹了。而要维持它们纯而又纯的状态,唯有将它们保留在思维当中。
哲学家们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些纯而又纯的东西,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只能在人的头脑里。它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最真实的东西。而现实中的东西,乱七八糟、眼花缭乱,根本就不纯粹,也不真实。而哲学,就是要探究这些纯粹的东西。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就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也就是说,靠思维抽象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相反,眼睛看见的,耳朵听到的,都是骗人的,尽管这些东西就在我们身边。
后来,柏拉图沿着巴门尼德的思路继续走了下去,提出了影响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理念论”。他说,在我们能够经验到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唯有通过思维能够把握的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才是现实世界的根源。或者说,现实世界是沾了理念世界的一点灵光才成其为自身的。上面那个大学生说的那只“抽象的鸡”,就是“鸡”的理念。而他妹妹吵着要吃的那只“具体的鸡”,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只鸡中的一个。但是,不管是公鸡、母鸡、乌鸡、蛋鸡、肉鸡,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鸡”。为什么呢?柏拉图说:这是因为它们都分有了“鸡”的理念。只不过,它们仅仅分有了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占有了全部。所以,它们既是鸡,又不能完全代表鸡。能够完全代表鸡的,只能是“鸡”的理念。
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的影响是最大的。后来的怀特海就曾经感慨地说:“整个西方哲学史都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可以说,西方人就是靠这个理念世界活着的。他们的全部信仰都寄托在这个与现实世界分离的彼岸世界中。当然,经过改造以后,这个理念世界已经变成了上帝所在的天堂。哲学研究这个世界,所以才称为“形而上学”。
不死干什么呢
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
——黑格尔
庄祖鲲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六十年前抗战期间,寄居在贵州一个农家里。有一天他正在看书,农家四五岁的小女孩跑过来,两个人就展开了这样一段对话:
“叔叔,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书。”
“你为什么要看书?”
“看书可以增加知识啊!”
“增加知识干什么?”
“增加知识可以赚钱啊!”
“赚钱干什么?”
“赚钱才可以吃饭啊!”
“吃饭干什么?”
“吃饭才不会死啊!”
“那不死干什么?”
“去!去!去!别罗嗦了,去找你妈去!”
现在这个人已经80多岁了,每天在想的就是:“是啊,不死干什么呢?”
人生在世,总有一些问题是不能问的。你如果非要刨根问底地去追问,最后只能暴露出问题的荒谬——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比如,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无限?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此等等,都没有答案。而且,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时代的局限而没有答案,而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它们也不是因为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愚笨而得不出答案,而是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得不出答案。正如黑格尔所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
由此可见,不仅哲学研究的对象看不见,摸不着,哲学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也没有答案。哲学不仅无中生有,在黑屋子里寻找那只看不见的猫,而且也在强迫自己回答着那些不能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哲学问题看做是方程式,那么,这些方程式都是“无解”的。这里的“无解”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没有标准答案。当然,也没有解答问题的固定思路。谁如果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会留下笑柄。比如,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你可以说人性是善的,因为一些伟大的壮举都是人做出来的,而不是动物。但是,你也可以说人性是恶的,因为一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也是人干出来的,动物根本没有这个本事。所以,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一直在争论,而且还会永远争论下去。
人活着,不会像猪一样吃饱了什么也不想。想着想着,就会浮想联翩,想出一些超出经验,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许都可以归为哲学问题。
“延伸阅读”
所谓的哲学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与人相关,或者是人所提出的,或者是关于人的。人类社会不能等同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也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西方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自然界的规律我们可以说是知识。知识都是必然的,受因果律的制约。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也就越多。而且,这些知识让我们逐渐摆脱了自然界的束缚,获得了外在的自由。比如,太阳每天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这就是知识。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规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利用它,指导我们的生活,安排我们的起居。可见,知识是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对抗中产生的,科学技术就是知识的最高形态。所以我们今天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而人类社会则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即使有所谓的规律,也不可能像科学技术那样以不变应万变,超越空间和时间。由此,我们可以把关于人的学问称之为“智慧”。而哲学家,就是那些热爱智慧的人。智慧没有固定的模式,是因为人生无解,既没有现成的套路,也没有确定的方向。
关于人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两个正反命题可以同时成立。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在其巨著《纯粹理性批判》中将这样的现象称之为“二律背反”,即两个相反的问题可以同时为真,也可以同时为假,违反了逻辑上的矛盾律。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人性善和人性恶是两个相反的命题。但它们可以同时为真,也就是说,我们既可以说人性是善的,也可以说人性是恶的。同样,我们既可以说人性不是善的,也可以说人性不是恶的。而且无论哪一个主张和论点,都可以得到证明。这种现象就是“二律背反”。
康德说,“二律背反”现象的出现,是人理性的误用,即把人生的智慧当成自然的知识来追求了。所以说,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必然思维的产物,只能用到自然界中;而智慧则是辩证法的产物,只能用于人类社会。二者应该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知识进入了智慧的地盘,就是教条;一旦智慧进入了知识的领地,就是迷信。
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
哲学就是哲学的历史。
——黑格尔
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里都讲过西西弗斯的故事。据说,他被认为是最狡猾而且诡计多端的人。因此,神罚他在地下最阴森孤绝的山谷里推着一块巨石上一个陡峭的山坡。可是,每次刚推到山顶,眼看就要成功了,石头就会轰然滚落到山谷中。于是,西西弗斯只能从头再来,曰复一曰,年复一年,永远上同一个山坡,推动同一块石头,同样的艰苦,同样的劳动,而得到的永远是同样的结果。眼看着巨石滚下山坡,干百次的重复,他已把每次推耸后巨石的滚落视为必然,他的生命注定了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然而,如果某一天,巨石被推上了山顶,永不再落,西西弗斯就是幸福的了吗?不,在他荒凄的存在里,他的命运(推巨石上山)就是他的存在,除去了他的命运,他一无所有,而他命运的解脱(巨石不再落)不也就是他追寻的终结,存在韵律的中断,期待的幻灭吗?这样活下去也许就更没有意义可言了。
西西弗斯的故事暗示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尽管人生无解,但人类仍然苦苦地追寻着自身存在的意义,默默地承担着偶然加给的命运。正如那些超越时空的哲学问题,虽然没有答案,但干百年来,人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追问。也许,它的意义本身就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而非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因此,哲学本身就在哲学问题的回答过程中,正如西西弗斯的人生意义就在不断推动巨石的过程中。于是,对哲学问题形形色色的回答,就构成了哲学的历史。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意思是说,哲学本来就没有历史。哲学面对的问题始终是那些问题。它不像其他学说,总是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推陈出新。所以说,哲学无所谓时髦,也无所谓时尚。凡是符合时尚的,都不是真正的哲学。
“延伸阅读”
从一定意义上讲,哲学是没有历史的,它从诞生那一刻就已经死亡了。自从人有自我意识的那一刻起,先知先觉的圣人就已经把人生的种种困境和问题醍醐灌顶地提了出来,剩下的只是回答而已。如果你没有幸运地恰逢哲学的诞生,只能怪自己出生的太晚了。因为世间就一个“道”,早已经被别人发现了。后世的我们,只能去体认这个“道”,而不是再去发现或者发明一个新的“道”。难怪维特根斯坦说:“在哲学中,是不可能有什么新发现的。”罗曼·罗兰更是慨叹地说:“在每一个世纪中,人们都感叹:‘什么都给人说尽了,咱们生得太晚了。’”
同样,哲学是无所谓进步和倒退的。后人未必比前人聪明,前人也未必比后人愚昧。那些自作聪明的思考,总是会遭到上帝的嘲笑。知识是无穷的,总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而智慧是永恒的,几千年下来,谁也不敢大胆地说自己又发明了一种新智慧。哲学家伯林说得好:“人们在试图给出哲学问题的答案时,总是遇到困难,以至于想提供明确的答案却又屡试不爽,由此而产生一种印象:哲学中没有进步。”
也许,在哲学中,越古老的越是有价值的,越古老的,哲学味越足。正如酿酒,时间越长的酒,越是散发清香。每一次哲学创新,都需要重新回到源头,重新回到那些永恒的哲学问题,点燃智慧的火焰。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它就像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知识的圆圈
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
——庄子
据说有一次,一位学生问古希腊的哲学家芝诺:“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您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
芝诺没有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是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多。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无知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多。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的原因。”
芝诺把学习知识看作画圆圈,表明知识总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绵绵没有尽头。在通向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任何人只能不断地追求真理,而不可能占有真理。以至于庄子发出了“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慨叹。
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哲学是否是一门知识?它是否可以像其他知识那样进行学习、传授和积累?
这个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一开始并没有认真反思。他们总希望哲学能像科学那样清楚明白,普遍而适用。正因为此,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总以“科学”为model的。如果谁的哲学不被看成是科学的,就好像受了奇耻大辱。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写了一本书叫做《梦的解析》,主要是研究人的潜意识和精神现象的。但因为这本书大部分内容是讨论梦魇,很多人都不愿意把这本书当作科学著作。其实,不是科学著作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弗洛伊德却无法忍受自己的著作被打上这种“非科学”的烙印,于是又给这本书增加了一个副标题——“精神分析科学导论”。看来,在西方,是不是“科学的”,并不是无关紧要,而是带有强烈的价值色彩,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正确的,尽管不是科学的未必是不合理的。
但讽刺性的是,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知识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而哲学却丝毫没有进步。它仍然在围绕着那么几个哲学问题喋喋不休。直到康德对人的理性进行了彻底清算和界定,西方人才恍然大悟,在“独断论”的美梦中惊醒:知识和价值之间原来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知识能用来掌控自然界的规律为我所用,但却解决不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问题。而后者,才是哲学的真正主题。正如康德自己所说:“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
“延伸阅读”
从严格意义上讲:哲学并不是一门知识。尽管我们很容易就能指出若干“哲学知识”,如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等。但从根本上说,哲学是无法被当作一门知识来学习的。它既无法提供普遍而适用的规律和定理,也无法像其他知识那样严格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由此,哲学好像也无法进行定义和界定。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自嘲地说:谁要想让哲学家出丑,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问他“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哲学家,估计就有一千个关于哲学的定义。
正因为此,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根本就没有设“哲学”这个条目。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有设这个条目,只是在“西方哲学史”条目之下设了“哲学的本质”这样一个子目。它说道:“在各种各样的界说中,很难判定是否能找到某种共同的因素,或为‘哲学’找到某种中心含义,以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全面的定义。不过,人们在这方面首先试图把‘哲学’定义为‘对各种人类经验的反思’或‘对人类最为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理性的、方法论的和系统的思考’。”
熟知并非真知
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生命不是一场梦境?
——笛卡尔
黑格尔在其名著《小逻辑》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有一族人特别崇拜一个名叫“戈尔肖克”(Golshok)的东西。他们相信,“戈尔肖克”孕育着生命和智慧,就像源远流长的密西西比河和一泻干里的亚马逊河一样。它是称量善恶的天平,是佑护人们幸福的万应符咒。由于这个词实在重要,每一代智者都投入毕生精力,青灯黄卷,面壁冥想,企图破译它的真谛。他们的言论汇集成典籍,流布于民间,成为人们世代信守的金科玉律。
终于有一天,一个对此感到厌倦的人问道:什么是“戈尔肖克”?这个词究竟指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惊醒了所有被“戈尔肖克”催眠的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一向以为最熟悉的词竟然一无所知。
黑格尔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熟知与真知是有区别的,甚至可以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熟知仅是表明我们看到了眼前事物的轮廓,但对其内涵却没有加以深思,因而并不是真知。正如他所说:“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了解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这就是说,人们对于熟悉的东西,往往习以为常,不加深究,因而容易停留在表面现象的了解,对它的本质并没有真正深切的认识。
“延伸阅读”
在本质上讲,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活动。所谓反思,就是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念再重新思考一遍,以确定它们是不是确定无疑的。正因为此,哲学并不依赖常识,相反,它总是在那些司空见惯的地方发问。它不是对常识的归纳和总结,而是对常识的超越。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鼻祖。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普遍怀疑”。所谓“普遍怀疑”,就是对那些“熟知”的东西进行彻底的审查,任何东西都不能放过。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容怀疑吗?不对!人的感官知觉经常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事物,也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外在的世界不容怀疑吗?也不对!我们在梦里也会看到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对熟睡中的我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有谁敢保证我们清醒的时候面对的一切不是虚幻?梦幻与现实的区别标准到底在哪里?正如他自己所说:“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生命不是一场梦境?”
笛卡尔是数学家,但他认为,即使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的数学命题,也要怀疑。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不管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二加三总是等于五。这样明显的真理,还需要怀疑吗?不,笛卡儿说,这些东西照样需要怀疑。数学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但是,冷不防就可能有讨厌的“幽灵”蛊惑我们的精神,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放置在我们的心灵里,偷换成我们思想的对象。
笛卡尔说,这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人们经常把眼前出现的幻觉当成真实的。就此,笛卡尔还讲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那是1911年的事情。当时的笛卡尔在荷兰从军,跟随军队来到德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麓。在11月份的一个夜晚,他连续产生三个梦境。在第一个梦境里,有大量的幽灵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境里,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晰地看见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境里,他看见了一部词典和一本诗集。他立即判断出字典象征着各门科学的综合,而诗集则象征着哲学与智慧的统一。笛卡尔说,这三个梦境清晰如同现实,其实都是假的。
照葫芦画瓢
哲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启人思。
——海德格尔
在禅宗公案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一指禅”的故事。
据说唐朝末年,俱胝和尚向他的师父天龙和尚参问“怎样才是佛”,天龙和尚向他竖起一个指头,俱胝和尚当下大悟。此后,凡有向他参问的,他都只竖起一个指头,而不说别的。他在晚年总结说,自从悟透了天龙的一指禅,一生都受用不尽。
在俱胝和尚处,有一个做杂事的童子。他每次遇到人问事时,也总是竖起一个指头作回答。于是,有人告诉俱胝和尚说,您这里那位童子也参透了佛法,凡有人提问题,他总与您一样竖起一个指头。有一天,俱胝和尚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刀,把该童子叫来问道:听说你也参透了佛法,是吗?童子回答说:是的。俱胝又问:那你给我说说,怎样才是佛?童子果然竖起一个指头。俱胝乘其不备,挥刀将其手指砍掉。童子痛得大叫而走。俱胝又把他叫回来,还是问他,怎样才是佛?童子又习惯地举起手准备伸指头,但一看手指没有了,于是豁然大悟。
随便砍掉人的指头是十分残忍的行为。但是,该童子的断指之痛正是他大彻大悟的机缘。在这里,俱胝和尚竖一指,童子也是竖一指,表面上看起来无甚差别,但二人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和体悟却是天壤之别。俱胝是在经天龙和尚的指点后,有了自身的深切体验和觉悟,才以竖一指头来解答问学者的各种问题的。而童子完全是形式上的模仿,根本没有自身体悟可言。因此,只有在被砍去手指后,发现无指可举时,这位童子才从自己这一痛彻心扉的切身体验中得到了觉悟——偏执之处,佛性不显。
“延伸阅读”
黑格尔曾经说:“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通过它们的头脑。”通过这个比喻,黑格尔尖锐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哲学智慧的智慧:“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却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这些人“高谈哲学”,当然也就如同动物听音乐一样,听见的仅仅是“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却听不到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哲学不是现成知识的结论,如果只是记住了某些哲学知识或使用某些哲学概念,那就会像“动物听音乐一样”,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调”,却听不到真正的“音乐”。
我们上面曾提及,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可以学习的。如果我们对一门知识不熟悉或不精通,只要假以时日,肯定会有所了解。但真正难得的是智慧。智慧是学不来的,唯有用心去体验和洞察,别无他法。而且,知识的积累无助于智慧的体察,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佛家的慧能禅师,大字不识一个,却能顿悟成佛,豁然开悟。而有的人念了一辈子经,读了一辈子书,皓首穷经,到最后也没有开悟。对此,冯友兰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修行不是吃大饼,今天吃一点,明天吃一点,早晚能吃完。对智慧,只能“悟”,而不可“学”,别无他法。
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接受,虽然可以使人获得某些哲学概念,但却始终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说到底,哲学不过是一种运思方式。有什么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如何看待世界,就会如何思考世界。预设的前提不同,思考的方式就会大相径庭,得出的结论也会千差万别。学习哲学,无非就是要学习哲学的这种思考方式。比如,我们学习马克思的哲学,无非就是要学会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当年康德就曾经告诫他的听众:“学生唯一可学的仅是进行哲学式的思考。”海德格尔也说:“哲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启人思。”
对智慧的爱
鱼儿对于它终生都在其中游泳的水又知道些什么呢?
——爱因斯坦
哲学是专属于人的,因为它本身不是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爱。柏拉图曾经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适合神,而“爱智慧”这类词倒适合人类。所以说,没有对智慧的爱,而是抱着功利的态度去对待哲学,是进入不了哲学的。一个人如果从哲学中仅仅看到若干范畴和教条,当然会觉得枯燥乏味,那么他也算枉学了哲学。只有那些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考人生和世界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哲学的魅力。
哲学的英文拼写是philosophy。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由“philo”和“sophy”两部分组成。“philo”的意思是“爱”,“sophy”的意思是“智慧”,合起来就是“爱智慧”。所谓“哲学”,它的原初意思就是“爱智慧”或者“对智慧的爱”。顾名思义,哲学家,就是那些热爱智慧的人。据说,最早使用“philosophy”这个词的是毕达哥拉斯。拉尔修在《明哲言行录》中记载说:当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一个philosophos。”毕达哥拉斯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哲学家生来就是寻求真理的。与此相对应,他明确地把哲学家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从而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
智慧是理智的化身,爱,则是情感的投入。而所谓的“爱智慧”,则是理智与情感的双重投入。仅有理智的思维,没有热爱理智的情感,照样无法进入哲学。黑格尔曾说,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一个老人口中的格言可能浸透了他所有的人生阅历,他已给这句格言赋予了深厚的切身体验,他口中的格言已非年轻人眼中的一个普通的知性的道理,而是与生命息息相连的理念,其中包含了无数的升沉荣辱人世沧桑。
“延伸阅读”
通过“同一句格言的”比喻,黑格尔是要告诉我们: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慎思明辨的理性,还是一种需要切身体验的真挚情感;哲学不仅仅是一系列概念的运动和发展,而且还是蕴涵着生活阅历的主观体悟。一个人要想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不仅需要勤于思维,更要浸入主体的生命体验。当哲学饱含人生体验,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时,理性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了。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既不能“教”,也无法“学”,只能靠参与。唯有参与到哲学思考当中去,才能领会到其中思考问题的方式。因此,领会哲学,就不能当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应该抱着投身于其中的姿态参与其中。在人生这场大戏中,人既是导演,也是演员。哲学离不开人生,人在哲学面前也就无法充当一个置身于事外的旁观者。
哲学其实很简单,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但我们似乎觉察不到。正所谓“日用而不知”今天的哲学之所以变得抽象了,变得晦涩了,是因为我们总是将其当作一门知识来学习,而不愿意参与到哲学的思考当中。我们总是期待一门学问给我们多少多少技能和知识,而不是希望从中能获得多少启迪。比如,《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学习而又经常复习,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今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复习旧知识的时候,感到的是索然无味,而没有感觉到快乐呢?原因也许很简单,你没有把学习看作生命,没有带着自己的经历去体悟,总是想着学完知识以后去干点别的,自然就不会快乐了。
爱因斯坦曾经把“哲学”和“人”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他说:“鱼对于它终生都在其中游泳的水又知道些什么呢?”“鱼儿”对“水”一无所知,是因为它本身就在水当中了。这种鱼水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知道”和“不知道”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了。哲学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人就生活在哲学当中,求知本然地就是人的本性,怎么能把哲学当作技能和知识来学习呢?还是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哲学是不能教的,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去参悟人生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