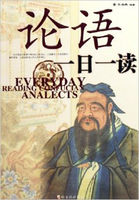当妇女在“子嗣之礼”面前如履薄冰的时候,男人们却享有了种种特权。他们可以借由求嗣,弃妻闲房;可以情不好终,初偶后睽:可以薄荆厚柳,烟花为乐;甚至可以对无子之妻辱而鸩之。更可悲的是,这种“子嗣之礼”作为被普遍认同的文化因素又反过来要求妇女具有贤达不妒的气质,不仅要不妒忌丈夫取妾,而且在可能时还要自觉地为茂衍夫裔充当“荐达淑贤”的角色。如不识相,醋意妒忌,河东狮吼,那便又撞上了“七出”天条之一,其结果就是扫地出门了。
妒,是一种女性主体的心理反射现象,对象客体主要是妾。人类在进入私有制社会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夫一妻制的要求,然而这种带有男女平等意味的婚姻形式在惟男道是行的社会结构中是不可能实行的,最终只能是一种假设、一个幌子,其实际意义只是通过限制女子的性自由来扩大男子的性自由,实现名正言顺的多妻制。对于皇帝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女子,皆可为王所有。周代皇妃制度虽难确论,但何休“唯天子娶十二女?(《公羊传·成公十年注》)的说法还是可信的。这是正式的,至于兴致所至的淫趣秽欲随时利用大量侍妾来处理。春秋时,大人”侍妾数百(《孟子·尽心下》),到唐代,“皇后而下,有贵妃、淑妃、德妃,是为夫人。昭仪、昭容、昭媛、脩仪、脩容、脩媛、充仪、充容、充媛,是为九嫔。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合二十七,是代世妇。宝林、御女、采女、合八十一,是代御妻”(《新唐书·后妃传》)。这浩浩荡荡的队伍还只是些排列在前台的人物,后台的更加可观。王莽登基“乃染其须发,进所征天下淑女,凡百二十人”(《汉书·王莽传》)。《旧唐书·宦官传序》说,玄宗开元、天宝中“大率宫女四万人”,亦非虚妄,白居易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实在是为尊者讳了。
皇帝如此,一般贵族、士大夫及文人学士纳置媵妾就只是一个数量多少的问题了。多则姬妾成群,少则三房六妾,当然补充队伍也是不可或缺的。如《唐六典》规定,三品以上正员清官可私备女乐五人,五品以上可私备女乐三人。天宝十载特下敕文,“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蓄丝竹,以展欢娱”(《唐会要》卷三四)。另外各州府还配备官妓,专门送往迎来,陪酒侍夜。这些都是作为贵族士大夫两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形式,同时也巧妙地在君臣之间建立了一种心理平衡机制,达到了男道意识的沟通与默契。至于到青楼北里去寻花问柳,肆浪风情,对于文人庶士也绝不是挂不上嘴的耻行,相反,这类事情倒是常常成为风流倜傥的“才子举为”见载于史。
这里特别需要在具有典型意义的宋代荡开一笔。宋儒标榜礼教,北宋起即炽兴理学,至南宋理学宗主几经更替,道统越趋完善巩固。但这种以“礼”为中心的教化只是宋代社会维持功能的一种发挥而已,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宋代君臣的淫乐要求。从宋太祖亲自提倡“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置歌儿舞女,日夕相欢,以终天年”(《宋史经事本末》卷二)开始,便形成了持续高涨的纵欲享乐之风。在生活上他们根本不去管道学那一套,荒淫贪欢,腐化至极。清人史梦兰曾作诗讽刺道:“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为《宋艳》题辞),说的是宋徽宗暗通妓女李师师,宋理宗私乱妓女唐安安,这是帝王艳事,那么道学家们怎么样呢?号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人本不可能无欲,也不可能免欲,于是人格分裂,作弄虚伪。监察御史胡盭、沈继祖庆元二年(1196年)曾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朱熹言行不一,“其为害于风教大矣”,其中就包括“引诱尼姑二人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和“使冢妇不夫而自孕”(《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言行悖逆如此,便难怪陈亮及后来李贽等人见到朱熹门人黄癲的《朱熹行状》把他描绘成幅巾方履、规行矩步、瞑目端坐,无情无欲同于泥塑的形象都嗤笑不已。
纳妾(这里把她作为嫔、妃、媵、妾的代称)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历代各个阶层都通行无阻,从根本上说,它对于封建宗法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维持效应,对于宗法制度的延续具有保证作用。也正是在这面宗法制的大旗上,“不妒”二字才显得似乎合理而有力。因而,在家庭关系上,尽管与妾的地位悬殊,管他家中有几房妾,正妻总是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处于众妾头人的位置,但是,在丈夫的性生活上正妻却不得擅宠妒忌,甚至应当创造条件使众妾有被幸的机会,这就能赢得“贤达”的口碑了。汉儒训解《诗经》时故意风马牛不相及地称《关雎》是“美后妃之德”,《癳木》是美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螽斯》是“美后妃不嫉妒,则子孙众多”,《小星》是“美夫人无嫉妒之行,惠及贱妾”,就是在倡导这种“贤达”。直到清代,《改良女儿经》还一以贯之地告诫为妻者:“夫无嗣,劝娶妾,继宗祀,最为切。”《新妇谱》更劝妻子对“风雅之人,游意青楼,置买婢妾”这些才子风流行止定勿见怪,应该“能容婢妾,宽待青楼”,使全家和睦,外不被耻笑,内获丈夫感激,夫妻之情就更加坚笃绸缪了。《金瓶梅》中的吴月娘,是西门庆正妻,在经济上助夫理财,帮助西门庆周旋官场,最为风光,可惜不孕无子。但能体现出“贤达”品质的是,她对于西门庆一个接一个地迎娶小妾来“广继嗣”从未不满,对西门庆的种种荒淫也特别宽容。惟有在西门庆要娶李瓶儿的问题上,她插了一手,投了反对票。西门庆和她反目,背地里骂她不贤良,她心里诚惶诚恐,千方百计要作出贤良的样子来,每月吃斋三次,逢七拜斗,夜夜焚香祝祷,“贤达”的祝愿终于被西门庆亲耳听到:
妾身吴氏,作配西门,奈因夫主流恋烟花,中年无子。妾等妻妾六人俱无所出,缺少坟前拜扫之人。妾夙夜忧心,恐无所托。是以瞒着儿夫,发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祝赞三光。要祈保佑儿夫,早早回心,弃却繁华,齐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见嗣息,以为终身之计,乃妾之素愿也。
这番祈祷是那样的“无私”,毫无骄妒之意,西门庆暗中听见,感动得上前抱起吴月娘,真心认她是个“好人”,重归于好。用封建礼教来衡量,吴月娘可称是最“能容婢妾”,最“宽待青楼”的典范了。
一般说来,妾从进入侧室起,总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情结,不仅要对夫权绝对驯从,而且要表现出对正妻地位的认同,仰承丈夫如天,奉事正妻若母,即使生下一子一囡也通常以正妻为嫡母,其地位之低下可想而知。但是,男女两性关系毕竟是排他性的,而生育功能一旦满足了丈夫“广继嗣”的愿望又确实为妾改变低下的地位提供了可能。因而妻室往往从维持自己的利益和巩固已有的地位的目的出发,本能地采取“妒忌”的特殊手段。吕后将一度受汉高祖之宠的戚夫人摧残为“人彘”,开后宫大妒之先。袁绍夫人刘氏甚妒,绍死未殡,刘便尽杀宠妾五人,杀后亦毁其形貌。其少子袁尚又尽杀死妾全家。谢安的刘夫人坚决反对丈夫纳妾召妓,另立别室,当甥侄同来传达丈夫之意并用《关雎》、《螽斯》有不妒之德劝讽时,刘夫人问道:“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刘夫人道:“周公是男子,故作此诗,若是周姥撰诗,就不这样写了。”唐代奇妒之事亦每见记载。如《朝野佥载》补辑云:“唐宜城公主驸马裴巽,有外宠一人。公主遣阉人执之,截其耳鼻,剥其阴皮,漫驸马面上,并截其发,令厅上判事,集僚吏共观之。”又,《酉阳杂俎》卷八载:“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限?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妒火中烧时,毫无理性可言,其报复性行为,足以让人怵目惊心。饱受过妒妇悍凌的蒲松龄曾深有体会地感叹“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江城》),果真如此,那是不胜枚举的。
妒妇因情而恨,因恨而悍,如不加以遏止,任其恣肆,岂不是阴盛阳衰,乾坤错位?多妻制又岂能长治久安?因而,尽管在后宫和民间都能随手拈出许多狡狞残忍、每每得手的妒妇,但总体观照,历史上男权为保证多妻纵欲所作的半争是长期而屡见成效的。这种斗争包括两种方式:惩治与改造。始终坚定不移地将“妒”列入休妻条件,是最具有威慑性的惩治。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惩治办法。如南朝宋明帝曾亲自下令赐死袁癴好妒的妻子,药杀有名的妒妇荣彦远的妻子,并赐刘休责打妒妻王氏二十大板,然后让王氏卖扫帚来羞辱她,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对于植根性灵、渗入骨髓的妒性又往往不是靠惩一而能儆百的,改造妒性,使之收敛相安显得更为重要。宋明帝一方面对妒妇严惩不贷,同时又敕令大臣虞通之撰写《妒妇记》,专门搜集古今妇女妒忌的典型,作为警世恒言。后萧梁张缵又作《妒妇赋》,渲染妒妇之凶残,在舆论上丑化妒妇,试图唤醒社会的阳刚意识,恢复阴阳常序。当然,男权社会对妒妇的改造并非停留在书面毫颖,面对具体问题亦有招式。据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构思的方案,大致有两种:一、遣妒妇大归,使其羞辱而改过。出妻惩治,本当一了百了。但从蒲氏笔下看,举凡被出之妒妻,往往都迁过向善而复归,方知出妻在一定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改造手段。如《吕无病》中孙麒之填房王氏,入门数月,擅宠专房,妒气甚深,小妾无病在面前,啼笑皆罪,并时常迁怒夫婿,数相斗阋,最后终于作践得前妻的遗子夭折,小妾遁亡。孙麒懊恼不已,排除一切干扰,将王氏遣归。归后,王氏妒悍之名大噪,简直无地自容,每每私下托人向孙致意,表示忏悔,孙置之不理。不得已,王氏亲率一婢,径自奔孙,跪于阶下,泣悔不止。孙见其妒气已消,心意竭诚,方使人挽扶入室。为再明悔改之意,王氏竟剁掉左手一指相誓。孙日后非常嬖爱王氏,而王氏总是宽达让宠,请夫婿到妾处就欢。二、不近妒妇,使其渐生失落感而改过。如《邵女》里金氏,不能生育,奇妒异常。其夫柴延宾以重金买一妾,金氏凶暴地加以摧残,不到一年,妾就惨兮兮地死了。柴忿恨离家,独宿数月,不践金氏闺门一步。金氏深感孤独无依,如熬如煎。柴一次偶然回家,金氏急忙上前卑词庄礼,设筵招寝,并软语宽慰:“后请纳金钗十二,妾不汝瑕疵也”,保证不再干涉丈夫娶妾了。
丈夫可以拥有三房六妾,荒淫作乐,妻子却只能成全、迁就,不能有丝毫妒忌,这是中国古代家庭生活中一个何等荒唐的现象!说到底,“妒”是一个夫多妻制的产物,其施之于男性,是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反抗,但施之于女性,则只能说是以谬误反对谬误了。而所谓去妒向善、回头是岸的“贤达”,恰恰又扩大了男子的特权,维持了畸形变态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