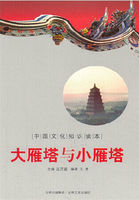一
这些年,散文园地的芜杂自不待言,尤其新千年之后的散文,或玩技巧,或写自我,多流于末技小道,不得要领。在此背景下,韩少功如一株兀立于罡风的乔木,彰显特立独行之姿。韩少功的散文是一面很好的镜子,20世纪后期以来的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从其文本尽得映射。他亦因此成为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的真正领军人物。
作为文坛少见的学者型作家,楚人韩少功充分印证了那句古语:唯楚有材。韩少功的散文继承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下笔夹叙夹议,无拘无束,在海阔天空中一展跨文体写作的风流,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和心智空间。他的一些长篇随笔,深邃洒脱,出入中西,善于避开缠杂不清的争执而直面问题,以平实的语言,搭起坚固的思想平台,显示出卓荦不凡的文化情怀。寻常文人往往文辞精美,却独缺一份识力;有识力者,却又不免于文辞枯槁,表达力欠缺。韩少功是一个例外。对于市场化、全球化、环境与生态、民主与宪政、大众文化、道德与人文精神、后殖民、教育、传媒、腐败、民族主义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热点问题,韩少功皆有涉及,每每以感性与理性的水乳交融,指向精辟之解,明晰之思。面对斑驳陆离的现象和问题,韩少功远观近察,得心应手,自由穿行于文学、哲学、宗教、史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人类学、数学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思想诸领域,体现出把握对象世界的能力和百科全书式的胸襟。
没有翻译体的冗长做作不知所云,也没有国粹主义者的坚执生涩抱残守缺,韩少功的语言是活的语言、自信的语言、充满弹性的语言。鲜活,灵动,厚实,凝重,苍凉,高华;萃集了多重美质的韩少功随笔内外双修,以学识、阅历、思想和教养作支撑,始终情调高洁,笔力沉雄,张力四溢,呈现出某种浮雕般的力度。这种力度,是可以用“铁钩银划”来描述的。韩少功散文不论叙事、描写,还是抒情、议论,功力都颇均衡。“满目波涛接天而下,扑来潮湿的风和钢蓝色的海腥味;海鸥的哇哇声从梦里惊逃而出,一道道弧音终没入寂静。老海满身皱纹,默想往日的灾难和织网女人,它的身上已长出木耳,那倾听着千年沉默的巨耳——几片咬住水平线的白帆。”(《海念》)惊警不俗,气象阔大,蕴蓄着某种内敛的爆发力;“乱石横陈曲折明灭的一条山路,茫茫雪原上悬驻中天的一轮蓝色新月,某位背负沉重柴捆迎面走来的白发老妪,还有失落在血红色晚霞中一串串铃铛丁冬丁冬的脆响……”(《记忆的价值》)如此地道的美文路数,浓郁的抒情气息,虽偶露峥嵘,亦令人感奋。但韩少功没有把精力投放于纯粹的美文一途,而是决然以其文字充当了社会分析报告,承载起凝重的社会内容和现实分量。他的随笔,美在见地,美在精神,美在风骨;缘此,韩少功成为一只高蹈的思想之鹤。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抨击了独断论与虚无论;《强奸的学术》表达了言说真理的艰难;《人在江湖》发掘古朴瑰丽的楚文化和浪漫的巫风,钩沉非常岁月里的民间帮会流派,表现了对历史真相和民间精神的探寻;《感觉跟着什么走》反思席卷全球的技术主义、物质主义洪流,呼唤人文、智慧与理性……不论长篇大论,还是尺牍小文,韩少功的文章均能游走于中外,纵横于古今。《夜行者梦语》思考社会、时代、人类文明、商品经济,对症下药,宏论滔滔:“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们一次次说成龙种,让大家觉得悦耳和体面。”“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弗洛伊德遥望红灯区和三级片,如果让欧文、傅立叶、马克思遥望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文革’,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的。”《世界》以从容犀利的笔触,指涉了语言、国家、集体、民族:“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在忧患和思辨中,贯串着寻觅民族之魂的宏远追求。“关于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让出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如此幽默可心、警意凌厉的妙文,代表了“韩氏语体”的典型风格。
二
韩少功不少国际题材的随笔,表达了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思考,不见丝毫洋奴气和西崽脸。《访法散记》《美国佬彼尔》《安妮之道》《仍有人仰望星空》通过对中西国民性的感性比较,呼唤人类意识与平等观念。《你好,加藤》借日本人说事,突破褊狭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观照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心态和价值观念。面对日本人俭朴如一的生活方式,韩少功感慨:“从西汉之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之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然。这当然是一种轻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烂,粗粝可能更具有强大生力,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州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通过历史的探讨和现实的反思,道出中日两国现代形态的巨大差别。韩少功又在归纳了日本民族源远流长的武士传统和职人传统后指出:“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中国在近代没有职人传统,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因此,中国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中国有儒生加农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职人的维新。也许,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中日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出大差别。与其说这种差别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结果,不如说这种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还受到地理、人口、发展机遇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这样的评说是振聋发聩的。纵览中国社会,儒家文化与小农意识互为表里,两相濡染,再经与专制体制的三相化合——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其对国民性的制约,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拘囿,对中国历史进程的羁绊都是致命的。个中实情,岂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得!眼下,某些“国学家”和“儒学家”正津津乐道于“读经”、“读史”,在一番番甚嚣尘上的“国学热”中,我们更应重申这样的常识:成分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向上的,也是向下的,既是含氧的,亦是含毒的;面对它,如同面对河豚鱼,首先应该做的是必要而必需的排毒。倘真如某些言论鼓噪的那样,省略了这一排毒与取舍的过程,把成型于专制语境中的那些所谓“国学”典籍原封不动请上神坛,奉为时代之《圣经》,文明之圭臬,显然大违常理。诚如东方朔《答客难》云:“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对待传统文化,忽而打倒在地一无足取,疾呼以“蔚蓝色文明”取代“黄土地文明”,忽而抬入九霄万金不易,高喊“以东方文化救助西方文化”,两种态度均欠得当。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非易与之事。鲁迅那一辈人是有资格激进、有资格宣称不必读古书的,也是有资格保守、有资格奉古书为经典的,因为他们身上尚存一脉混沌的天真,单纯的可爱。今人对“国学”的趋之若鹜也好,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情有独钟也罢,往往都在急吼吼的口号姿态下,暴露出庸俗心地和市侩嘴脸,带有了强烈的喜剧色彩,岂可与先贤同日而语。
韩少功聚焦宏大叙事,评说国际风云,皆着意于真相的揭橥。《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反思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扫描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世道人心、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漫不经心间便道出了中国人思维与感觉的误区,民族现代化追求中的排他品格及霸权品格的显影,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体两面,等等。一般论者涉及此类棘手话题,大多如履薄冰,如入雷区,韩少功则排闼直入,昂首阔步于蛛网交织的话语森林和问题迷宫。在常人不免于心魂俱失茫然无措的所在,韩少功游刃有余,顾盼自雄,犹如剧饮千杯而不醉的酒国英雄,犹如“黄沙百战穿金甲”的疆场健儿,总能在清醒自持的状态下纵横捭阖,信心而行。“以集团利益为标榜,在很多情况下常是虚伪之辞。稍稍了解一点现实就可以知道,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义一定是反民族的……这种主义之下的‘民族’名不副实。源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主义也一定是反全球的……这种‘全球化’只是全球少数人的下一盘好菜。因此,重构亚洲与其说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问题,毋宁说首先是一个价值检讨的问题,甚至是清理个人生活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重构一个美好的亚洲,与其说我们需要急急地讨论亚洲的特点、亚洲的传统、亚洲的什么文化优势或所谓经济潜力,毋宁说我们首先更需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追问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韩少功健笔一枝,上下翻飞,左右点染,不经意间即可下笔万言,意犹未尽;如此余勇可贾的文化姿态,透出的岂止是文化人的自信?!韩少功积极提倡“向内看”的反思精神和内省态度,提倡多元文化的并行不悖、自由融通;这种宇宙意识和大同情怀,读来确实可以胸胆开张。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韩少功高度看重体验与实践。积极走出书斋,展现当代知识分子自我超越自我刷新的轨迹,一直是韩少功努力的方向。韩少功是“知识分子”,有其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知道分子”,仅止于知识的挪用和信息的搬动。作为人类真理的言说者,知行合一的实践者,韩少功慷然充当着时代的化验师、知识分子的质检员。韩少功的目光是挑剔的,却不傲慢;是苛刻的,却不尖刻。当今文坛,缺乏的正是像他这样的碧海掣鲸手。作为脚踏实地的启蒙主义者,韩少功深知,真理未必可爱,与其说庸众喜欢真理,无如说他们更喜欢真理的被遮蔽,喜欢真理被遮蔽后的那种无序、堕落的狂欢状态;不少情况下,他们宁愿舍真理而取利益,坦然向世俗缴械。这是人性的阴暗,亦是人性的真实。明乎此,韩少功坚持在言说真理中揭橥本相,挑战流俗,试图以其富于前瞻性与批判性的眼光拨云见日。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正是启蒙者特有的入世勇气。韩少功从不高高在上好为人师,而是时时警惕着启蒙暴力和启蒙霸权,远离伪贵族的清高和伪精英的自负。实际上,“纯粹”的民间立场是行不通的,它往往使人变得很低,以至低到尘埃里,对一切皆持懵懂之姿和仰视之态;“纯粹”的精英立场多又流于俯瞰众生不肯屈尊,导致启蒙路径的阻塞。在众多篇章中,韩少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民众群体的同时,更引领同侪反观己身的自大,无知,势利,媚俗,追逐权力,迷恋资本……由是,知识者韩少功自揭画皮、自批面颊。
三
韩少功《山南水北》的问世,作为新千年以来一次少有的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而引人注目。
逃离城市的巨大漩涡,韩少功在八溪峒筑巢而居,拥抱土地,亲近五谷,让久违的田园之气注入文字,让身影活跃于书斋和旷野。城乡两种迥异的生活,在智者韩少功那里切换自如,圆融无碍。对于他,八溪峒与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互联网、财富、超女是并行不悖的,城与乡是和谐的而非冲突的,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在海口和八溪峒之间,韩少功如冬去春来的候鸟,两脚踏城乡文化,一心写性情文章,由此获得阔大的视阈和弹性的空间,从容地整理和把握世界。作者把久经都市压迫的“人”转移到乡村的空地上充分舒展腰肢,唤醒感觉,复活记忆,激发美感。与历史上诸多“身在南山,心存魏阙”的隐士不同,韩少功的乡村生活并非意在以退为进,而仅仅体现为一种自适、自为、自便的文人生活方式。何况,现实世界里的正厅级干部韩少功乃是地道的农活好手,这使得他与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不事稼穑的历代文人隐士有了更为鲜明的区分。身体向大地扎根,心灵向天空舒展。从此,韩少功拥有了月光和上帝,他在八溪峒的种菜、赏月、养鸡,无不是诗意的生存方式的践行。
如是,韩少功很容易地被联想到美国作家梭罗,《山南水北》也会顺理成章地被誉为中国版的《瓦尔登湖》。但有别于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简单生活,韩少功在八溪峒的生活要复杂得多,作为当下中国乡村改革进程的一个热情参与者而非旁观者,这位“韩爹”需要不断地跟别人打交道,甚至还会帮助山民在一些修路、致富之类的重大问题上献计献策,以至拍板。乡村并非可供臆想和猎奇的隔绝的存在,更非“活着的博物馆”,乡村是一个现实性的真切存在,时时呼应着古老中国的剧变。全书展示了碰撞的尴尬,融合的有趣,中国社会转型时刻种种的世态人心,融入了作者对城市文明的反思,对城乡差距的焦虑,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对自我内心的体认,对现实世界的关切。
读《山南水北》,时常感觉如读一部乡村笑话集。其写法亦实亦虚,绰具魔幻意味。全书往往从貌似诡异荒诞的“奇人异事”切入,却恰恰抓住了乡村生活的本质。正是此类奇闻佚事,千百年来有效地调节着乡村生活的单调、乡村岁月的劳碌,在荒诞的表象之后,显露着乡土中国更深向度的大真实。乡村世界自来便是滋生神话的温室与福地。“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作者试图通过对大自然万千奇异事象的揭示,通过对怪力乱神花妖狐魅的描述,激活现代人贫弱的想象力,骨子里依旧奔突着楚文化浪漫的精髓。在“韩爹”看来,农民围火闲聊时谈到的那些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十八扯,既是当地山民的心理哈哈镜,更是广大乡土中国民众心理的原生态存在。诸如此类的种种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当属野史而非正史的范畴。然而正史未必“正”,野史未必“野”,否则,学识淹通的鲁迅何以只信野史而不屑正史?历史的本相,深邃的思想,恰恰多从野史中澎湃而出。这是民间的胜利,草根的胜利,是大地美学的胜利。置身乡野的腹地,韩少功尽情探测无人接听的远古秘密,执著于求真求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然而真与美常常不能并存,譬如,从美的角度,我们宁愿知道月宫里住着寂寞的嫦娥、伐桂的吴刚和乖巧的玉兔,却不愿知道月亮只是没有生命定居的冰冷天体。科技破除了世界的神性,让世界从混沌趋于明朗,复趋于无趣。倘若真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地步,这世界还有什么意思?自来便魅影重重的幽深乡村,一旦置诸现代化的照妖镜下,其迷人美感必定荡然无存。韩少功的努力,正在于重拾那些为现代科学所剿灭和湮没了的诗性的美丽。祛魅之后如何返魅,解构之后如何建构?《山南水北》引我们思考不已。
从海德格尔所谓的“静观”到“操劳”,作家张扬劳动者的哲学,热情歌咏劳工神圣。在乡村,韩少功静听万物花开,看草木如何抽枝挂果,衔珠抱玉,看愤怒的葡萄如何任性使气,参悟着日月星辰、山川大地、风雨雷电的奥秘。“唱歌也是养禾。尤其是唱情歌,跟下粪一样。你不唱,田里的谷米就不甜。”(《夜半歌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兴寄往来;韩少功始终将悲怀的光照投向世间所有生灵,在对大自然的精细观察中建立起某种对位关系——犹如法布尔之与昆虫,川端康成之与风花雪月。现代都市的快节奏把人淹没于喧哗与骚动之中,种种的都市病于焉而生。以乡村之药,愈城市之疾,正是韩少功的刮骨疗毒之举。凭此,作者足可将现代都市加诸自身的毒素逼出体内。凭此,我们亦可明白,韩少功之入八溪峒,正仿佛鱼虾饮水,蜩螗吸露,尽可滋生气力潜跃飞鸣。
《山南水北》彰显小说家散文的长处:不拘不纵,中规中矩,笔力矫健多变,忽而正面强攻,忽而剑走偏锋,忽而擒拿手变为兰花指,指拂处一派天朗气清;遂有了微言大义文质并重,有了流转自如举重若轻。向以文体探索和创新意识著称的韩少功,因了知性的充沛,感性的发达,理性的高扬,被公推为当代文坛六艺贯通的全能型才子。当世文人中才华特出者夥矣,但像韩少功这般专喜啃硬骨头、打攻坚战者不多。锤幽凿险,开径自行,韩少功不断以一己的艺术创新能力,验证着中国作家可能达到的超越性境界。韩少功运笔有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内篇·养生主》),好一派锋发韵流,钩深致远,千字小品而自具海涵地负气象。“我饮仙露,何必千钟?寸铁杀人,宁非英雄?博极而约,淡蕴於浓。”(袁枚:《随园诗话卷一·矜严》)这些简洁如奥卡姆剃刀的韩氏妙文,看似末道小技,实则丰盈可观,绝非浅斟低唱、以肉麻充有趣的小摆设文字可比。
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韩少功身上都有着鲜明的体现。不同于余秋雨诸多讴歌帝王将相、崇拜权力精英的历史文化散文,《山南水北》发扬光大了韩少功顶礼草根的传统。作者和山民打成一片,在相知相融中寻找到切实的话语通道。韩爹眼里的山民是“思无邪”的,他们天真烂漫,一清如水,拥有着天才般的直觉。“对于他们来说,理论好比辣椒水和老虎凳,一摆上来,足以让他们心惊胆战脚杆发软。”(《哲学》)山民惧理论而重行动,这与讲信修睦的古老乡村伦理是一致的。肉食者鄙,智者韩少功更愿向底层民众虚心问学。《意见领袖》中喜好谈论国事的绪非爹,《开会》中善以纲常伦理治乡的乡长贺麻子,还有《雨读》中的乡村诗人贤爹,往往不立文字而直指人心,以其见解的精到令人震惊,堪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民间高士。“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庄子·内篇·应帝王》中这则寓言,指涉的正是人性与文学的本质特征:混沌。韩少功尊重山民身上的这种混沌性,并师法于斯。混沌中自有大神通和大澄明在,人性之美在于混沌,文学之美亦在于混沌。对混沌性的破坏,意味着人性之死和文学之死。“韩爹”眼中的山民似乎都有一种通过风声鸟语洞察世界的能力,《笑大爷》中疯疯癫癫的笑花子具有预先感知大雨和火灾的神通;《邻家有女》中的小盲女能够听得出过路的牛是哪一头,过路的狗是哪一只,察知各种人的秘密、动物的秘密、植物的秘密、泥土和流水的秘密;《也认识了老应》中的挖土师傅老应能够凭鸟的怪叫和自己的眼皮跳、胃痛等征兆准确地预感到险情……全书既有对农民苦难的认同,更着意于揭橥农民天性中豁达坚韧的一面。明乎此,谁敢说韩少功笔下的庆爹、老潘、哈佬、塌鼻子、卫星佬、老地主、有根、贺麻子等或单纯或精明或狡黠的乡野人物,就不是鲁迅所言的“中国的脊梁”?!
穿行于屈原的汩罗和苏东坡的海南,与其说韩少功是在体味诗性的生活、思索生命的意义,不如说韩少功是在进行一次社会学、人类学的“三农”问题的形象化访谈。居于八溪峒的韩少功独善其身,复敬业乐群。此举绝非仅仅是传统士子“性耽山水”“情系田园”的心态显现,它更是现代知识分子体认生活的独特路径。韩少功既未将乡村苦难化妖魔化,亦未将乡村诗性化神圣化。书中偶有悲风回响,终究格调乐观。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了对生活的痛感,韩少功的文字从来都是远离韶乐悠扬麒麟献舞的。“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沈从文语)《山南水北》彰显哀而不伤的含蓄,谑而不虐的超然。读《山南水北》,我们除了想到韩少功的前辈乡贤、“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的沈从文,还会想到“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苏东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韩少功身上体现出的此种济世情怀,日月可鉴。
《山南水北》堪比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但毕竟有别于沈从文纯然感性的乡野牧歌,更有别于刘亮程、苇岸的乡村乌托邦。要说“乡村哲学家”,韩少功算是最为地道的。邮票般大小的八溪峒,蕴蓄着怎样的深沉、博大、悲悯和爱意,那是韩少功灵魂的领地,是乡土中国的缩微版图。底层与民间自来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沃土和精神摇篮,从中可以获取清醒的文化认知。在一个斯文湮塞人心蛊坏的时代,多少知识者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着底层和民间,韩少功则由书斋欣欣然走向民间,融入底层,直面并不沉默的聪慧民众。这样难得的文章下乡活动,对于重振汉语的精炼、优雅和丰盈怎不大有裨益?
韩少功不是专工雅颂文章和庙堂文字的古代士大夫,他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是富于民主意识的草根代言人。他试图以学者的理性,作家的情怀和史家的胸襟,以自身绝高的才力,将湮没的民间历史化作鲜活的影像,让强大的心灵光芒穿越时代,与天地精神独相往来。为文有大才,为人有大德。作为韩少功的田野笔记和田野调查的《山南水北》,流溢出一种以和为贵的境界,一种上善若水的情怀,一种不流于说教和口号的真正致力于和谐社会建构的深情呼唤。——读《山南水北》,我总有这样的错觉:韩少功不是文人,而是一位悬壶济世的杏林妙手。
四
颇有论者把韩少功归于“新左派”阵营,对此韩少功似亦未遑多让。事实上,作为清醒的智者,韩少功观人察物,力求持中公允、不偏不倚,绝不可能执于一端。面对世界,面对文学,他总在寻找着个体思考的黄金分割点。韩少功呼吁警惕媒体的两面性:媒体让我们无所不知而又一无所知,媒体导致读者白痴化。进而提醒大众,语言狂欢的时代也是语言危机的时代,自命不凡的现代人一不小心就会陷于胡言乱语状态,沦为文化生番。(《文学:梦游与苏醒》)由文学而社会,再由社会而文学,韩少功法眼大开,精光四射,总能从麒麟皮下发现马脚,从红纸包中见到烂肉——他较早感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病灶,坚定不移地从事着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比之20世纪90年代“文化散文”的代表人物余秋雨,韩少功尤多一种心高气傲的决绝。余秋雨作品表面的媚雅和骨子里的媚俗,暴露了创作主体不自重的本相,让人感慨于其徒具大好资质慧根。概而言之,余秋雨之文如美人招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蛾眉婉转间,便生成风情无限;韩少功之文则如玉山巍峨,青松磊落,如高崖坠石,鸣溪出涧,自具“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式的英雄情怀。余秋雨行文难得触及社会肌体,更少作击中腠理的社会分析,对于复杂的现实情状常常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惟沉迷于美人香草式的个人情调的经营;韩少功为文从不屑于寻章摘句,雕肝琢肾,然其文字调弄到佳处,自然突破了语言层和文学层,进入到社会层、历史层、思想层和文化层,寄寓着时代的尊严和文化人的尊严。韩少功既能大题小作,也能小题大做。直面问题,发现问题,剖析问题,正是韩少功所长。他不像张承志那样剑拔弩张快意恩仇,那样磨刀霍霍咬牙切齿,那样压抑不住偏至的性情而动辄“尥蹄子”,时时欲作暴烈的跳跃;“引而不发,跃如也”,韩少功的文字不玩酷,不摆谱,沉静澹定,触手微温,而凛冽之气撼人。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在商品狂潮和消费语境中,韩少功永葆“独钓寒江雪”式的心境。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韩少功远离花拳绣腿的虚伪书写,评人衡文,往往于不露声色间裹挟风雷之气,韩少功从不曾让人期望落空,更不至让人大跌眼镜。我们知道,一方面,散文姓“散”,随笔姓“随”,谁都可以染指;另一方面,散文不“散”,随笔不“随”,并非人人可写。许多在小说园地轻松称雄的文人,一俟涉足散文随笔领域,即纷纷现出原形:或漫天扯淡,不着边调,或满地撒娇,佯狂作态。于此,韩少功的散文随笔排秀独出。某种意义上,要想从韩少功文章中找出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就像要从鲁迅著作中找出不伦之文一样,洵非易事。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宁愿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亦决不苟且于红尘;韩少功为文而意不在文,故其文本骨韵并生,格调天成,不经意间即能咳唾成珠,每每格言警句联翩,撞击出一派环佩丁当的妙音,绝无披金挂银式的俗气。“胡马大宛名,风棱瘦骨成”,在浮肿虚脱垃圾成患的当代文坛,韩少功其人其文,正如书法界之颜筋柳骨。不盲从,不偏执,血性扩张而又理性高扬,韩少功复活了魏晋风度。在“洁的精神”方面,我甚至认为,韩少功比张承志走得更远。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高出众生,能够成为天地之精华、宇宙之灵长,乃在于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大脑和心灵,这也正是“会思想的芦苇”的内涵所在。得天独厚的韩少功,秉一己之力抗衡社会,以个体之思穿透历史,敢于向世界说不;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形而下与形而上,在他笔下交织成一派霁月光风。他那些心雄万丈的散文随笔,可称是为我们这个时代作出的一份全息报告,总能让读者不虚此行,从中品悟出百年沉重,千年忧患,从而对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深长思之。
在一个乱象纷呈莫名所以的时代,韩少功及其醍醐灌顶般的文字,成为一座无法绕过的雄壮的散文岛屿。可想而知,倘韩少功到了时下的高校讨生活,不知会羞杀多少垃圾教授、混混“博导”。在我看来,韩少功是完全当得起“超级教授”或“超级博导”称号的。
2007年9月2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