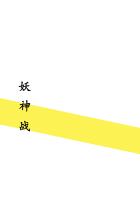列宾19岁时画的自画像,表现了一张年轻勇敢和充满激情的面庞,双眼流露出探索的神态。仿佛这位年轻人正在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世间存在着不公平?新的生活就在前面,可生活将是怎样呢?”当然,除此之外,你还可以感受到一往无前的决心。
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离开了故乡楚古耶夫,告别了亲爱的母亲和弟弟,带上他画圣像辛辛苦苦挣来的100卢布,踏上了漫长的旅途。
到彼得堡去,到远离家乡1500公里的地方去,在那里列宾举目无亲,但是,那座城市是当时俄国的首都,文化艺术的中心,拥有一所他向往已久的美术学院。
一辆四轮马车缓慢地行进在哈尔科夫通往莫斯科的大道上。赶车人不停地挥动鞭子,鞭梢儿在六匹马的头上叭叭作响。
列宾坐在靠外面的一个座位上。他头上还有一层,上边装着行李。马车晃来晃去地走着,爬山时显得十分吃力。为了不被甩到壕沟里去,车一爬山,列宾就得先跳下来徒步而行,这样比较安全。一路上,他多半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车上,寒气砭骨,双手都冻僵了。
列宾穿着银灰色呢面皮袄,皮袄外面还披了一件带风帽的黑呢军大衣。
这件军大衣原本是库片斯卡那儿一个神学校学生的,他是列宾承包人季摩费·雅柯夫列维奈的亲戚。他很喜欢列宾的一件厚呢大衣,而列宾也把对方的军大衣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于是,两人交换了大衣作为纪念。
马车单调地摇晃着,而车上列宾的心里很平静,不久前的往事一幕一幕地从眼前掠过。想到未来,他浮想联翩,既有忧虑,也有美好的憧憬。
阳光灿烂的白天被漆黑的夜晚所代替,接着又是黎明、朝霞和预示着将有一场初寒的落日余晖。一共经过多少次这样的更迭,早已无从记起,唯有马车还在不停地走啊,走……
突然,马车停了下来。周围是漆黑的夜幕。远处传来几声枪声,顿时一片慌乱。只见车长和车夫跑去追赶淹没在黑暗中的人影。
原来是小偷爬到车上,企图割开覆盖行李的雨布,偷走里边的提包。马车这时正行驶在匪患如毛的奥尔洛夫省境内。东方渐渐显出鱼肚白。朦胧之中可见一些衣不遮体的人,光着身子穿着破皮袄。其中有妇女儿童,也有老人和青年。他们眼巴巴地将双手向马车伸过来乞讨、求救。这里无疑在闹着饥荒!人越聚越多,吵嚷声也越来越大。眼前晃动着的都是手。有人扔钱给他们,于是人们一下子涌过去抢钱,你踩我,我踩他,乱作一团。接着,又是举在空中的手,哆哆嗦嗦的手,手,手……
赶车人想把他们从车旁赶开,朝着乞讨的人群甩了一鞭子,马车又重新上路了。
人们依然尾随在车后,伸着双手,边跑边叫。好像整个苦难的俄罗斯伸着颤抖的双手在乞讨。这是在1863年,俄国废除农奴制两年之后的情景。
在去彼得堡的路上,列宾一直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中。但此时饥饿的人群跟在马车后奔跑求乞的情景,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对于踏上独立生活道路的列宾来说,无疑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临别赠言。
他们仍然不间歇地赶路,眼看走了已经整整一个礼拜。但半道停滞了,比起这无休止的单调旅行,更叫人难受。
最长也是最不愉快的一次停滞,是在谢尔普霍夫,在这儿要搭平底渡船渡过宽阔的河面。大家等了大半天,渡船才从对岸划回来。冷风飕飕地迎面吹过来,寒气砭骨。列宾已经没有兴致爬下高座,无动于衷地望着浩荡的流水。船只穿梭般往来,有的载满乘客,吃水深,有的轻装无载,在水上迅速滑行。不过这一切都不能引起列宾的兴趣,他只希望尽快到达莫斯科,但那儿到底怎么样呢?想起便觉得心悸:在陌生的地方,会遇到什么呢?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列宾觉得只有图拉的宫城是叫人流连忘返的胜景。他们那些搭驿车的乘客集合起来,有的步行,有的叫车,向宫城出发。
在乌克兰的村庄镇市中,根本见不到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这雉堞整齐,转角处塔楼高耸的宫墙,令列宾不胜震惊。他不由得想起了《叶鲁斯兰·拉孔列维奇》和《包瓦王子》两本书中的插图,那儿画的正是这样的城墙。脑际里浮现出当年这宫墙内的全部勇士的生活。
在谢尔普霍夫渡河之后——直到黄昏时分才渡完。
又是无边无际的旅途。列宾枯坐着打发无聊的时光。又过了一夜……嗳,到底走了多少昼夜,列宾也记不清了。
终于,在朦胧的夜色中,押运员用特别激动的声调告诉列宾:
“你干吗不看看呢,莫斯科到啦!”
“到啦?在哪儿?”列宾瞪大双眼。
“我们这不是已经走在莫斯科的街道上么。”
“你这话当真?这些破房子,这些东倒西歪的栅栏?”
天色刚刚破晓,但四下里已愈来愈亮,可是街道似乎老是那一条,无穷无尽逶迤下去。总是歪歪斜斜的小平房,房屋塌陷,烟囱又黑又脏,一片颓败模样。但最令人厌恶的,还是这些望不到尽头的腐朽木头栅栏,以及上面冒着防盗贼的锐利长铁叉的围墙。
房舍大门上,越来越频繁地闪现出这种千篇一律的招贴:“空房出租”。天上飘着雪花,好容易在越过一片广场之后,街道宽阔起来,两旁房屋也高大起来。咦,这大门上还钉着狮徽呢。开始出现教堂啦……平日听说,莫斯科的教堂多得数不清……最后,大家进入了驿部的大院。于是,有人向大家宣布,各人可以领取自己的行李各走各的了,两个来钟头以后,驿车即循原路回驶。
列宾是个对新事物异常敏感的少年,他恨不得赶快跑去看一眼“铁路”这希罕玩意儿,看看不用套马的车怎样走法。这时候他想起叫沙夫卡的那个军官的勤务兵来。最初栽电线杆子的时候,在列宾家厨房里,引起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争论:电报到底是用什么法儿传来的?沙夫卡面红耳赤,因为大伙不相信他而委屈得流下泪来,赌咒发誓说,有一种小巧的机器顺着铁丝飞跑,要是落在铁丝上的鸟儿不及时躲开,准被碰个稀烂。
眼前就是火车站了。啊约,原来是这种形状:一长溜十分高大宽敞的走廊,顶上覆盖着玻璃;当中一大块没有铺地板的场地,上面一条条肋骨似的摆着铁轨。远处,一个乌黑茶炊模样的怪东西,呜呜叫着,朝空中喷着浓浓白气,朝人迎面飞奔过来,蓦地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吼叫。列宾被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一种欣喜若狂的情绪马上攫住了他,他赶快向站警打听:去彼得堡的火车什么时候开出?逢什么日子开车?
“不,每天开出两趟。”站里的工作人员笑着回答。
“原来是这样。”列宾暗自思忖,他迫不及待地想上彼得堡,但愿马上有车开出才好。
“今儿马上有车没有?”他问。
“两个来钟点以后,有列客车开出。”
“到彼得堡得走不少时候呢?”
“一个半昼夜。今天上午10点发车,明天傍晚就能到彼得堡了。”
“可是哪卖车票呢?多少钱一张?”
列宾这会儿晕头转向,对什么也无心观看,一心一意只想快点把他那只塞得鼓鼓囊囊、重得要命的箱子弄过来,然后安心等待什么时候放人进车厢,于是找好座位,飞向彼得堡……这难道不是梦么?
车票是一张窄条羊皮纸,上面印出火车要停的各个车站名称。
又是车来车往,机车喘气,吼叫,喷出一会儿是白色,一会儿是黑色的烟雾。列宾心里只挂记着两件事:看住自己的箱子不要丢失,但主要的还是及时坐进他该坐的那趟列车。他在长得没有尽头的站台上来回踱步,静候那趟车进站。站警答应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上车,该坐什么车厢。
啊,多美啊!列宾想:我到底乘火车出站了,坐在舒适的长凳上,和坐在房间里并无两样。不错,大家坐得很挤,车厢刷着灰颜色,到处牢牢钉着放平了的十字架形钩,上面挂满口袋,包袱和工具。凑巧一伙木匠师傅和列宾同车。
教堂、屋宇,都一晃而过,重又是城郊的市镇。瞧,又是村庄,纵横的道路,步行和坐车赶路的人们。但眼前的一切飞快变化,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便已经不见了。火车隆隆飞奔,飞奔……
车厢内开始大为改观。开头坐两个人的板凳,大部分都变了样了:凳上只剩一个躺着,佝偻着双腿,另一个爬进凳下去了,光露出一双树皮鞋或长靴。
空气越来越污浊,特别是因为乌合烟的烟雾。又有人啃起咸鲱鱼来。碎纸乱丢,一会儿便到处肮脏不堪。开门时放进一阵冷冽的气,更让人感到:车厢内的空气混浊得不得了。
列宾想:我算走运,听了站警的劝告,预先已上邻近的餐馆喝完了茶,就着小白面包和牛奶饱餐了一顿,现在一点儿也不饿。在苍茫暮色中,列宾昏昏沉沉进入梦乡。他已经习惯坐着睡觉。
点燃了暗淡的挂灯。朦胧神秘的灯光,洒在口袋包袱上,洒在横躺竖卧的人们身上。现在根本无法弄清,这是谁的胳膊,谁的腿脚,那是谁的树皮鞋,谁的口袋,谁的箱子——混乱一团,纵横交错。不管爬也好,跨也好,都休想溜到门口……
在这时候,乘务员、稽查和站警会同进来查票。
乘务员挨个撕下长条羊皮纸上人们已走过了的车站名称。这样的查票制度简便周到,想得真好!但看看这儿的实际操作情形才有意思呢。瞧,费很大劲把酣睡的乘客推醒;瞧,他掏出自己那条羊皮纸;瞧,乘务员撕掉了已经落在人们身后的车站!……有的睡意,愣怔半天,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折腾半天才搞清楚——这时好戏出场了:他忘记车票搁在什么地方,一时脸上的表情迅速变换,什么奇形怪状都有!
对面坐着一位中年人,列宾尝试着和他搭话,原来他是彼得堡人。这引起了列宾浓厚的兴趣,更想跟他打听下去,但不知为什么,一字不敢提到美术学院。
“你到什么地方高就?”他问道。
这一问,列宾才突然感到自己的前途十分渺茫。他有点惘然,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藏起来才好。
对面的同伴不由得注意起列宾来,这个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中年人,大概发现列宾形迹可疑。继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他便和颜悦色,开始安慰起列宾来——他是个好心肠的善良人。虽然说话时带有极度轻微的德国音,对生活抱不折不扣的实用观点。
“这有什么不便说的呢:你不是没有头脑的人,看一些书,对俄罗斯文学的议论有点见地。上学,想去上学是不是?很好嘛。怎么,你想进大学,对吗?”
他这几句话忽然把列宾的生活照亮了!虽然还没有置身其中,他这个假定却使列宾陶醉: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和大学生相像?在列宾心目中,大学生都是神话的英雄,他甚至不敢正视。他打心眼里惋惜,当时因为“捣乱”的罪名,大学生被禁穿自己的制服、天蓝色的帽箍和特制衣领。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中,他愉快地默不作声。
最后,像受审的犯人一样,列宾决定向他坦白出全部真情。
“你知道,”压低声音,列宾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本来有心想进美术学院……”
“原来如此,哪里用得着这么左右为难哩!进这学校倒容易,但必须要有天分,啊,上帝!”他霍地精神抖擞,用一种激动的声音叫起来:“我们到达彼得堡了!瞧,瞧——马上就会看到十字架教堂,啊呀,家里不知道是什么模样呢!”
他起身从这个窗口跑到那个窗口,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列宾却感到恐慌可怕。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去哪儿落脚呢?
“请告诉我,看在上帝面上”,他对一直与自己攀谈的同伴说,“麻烦你指点我,我该在什么地方落脚?美术学院在什么地方?”
列宾完全不觉得眼前这样喋喋不休多么不是时候。但他仍然缠着同伴不放手,虽然也感觉出来,对方已经心绪大乱,未必能回答自己什么问题。
“啊,这个,你必须上华西里耶夫岛,很远,得穿过整个彼得堡。”
“往后我可以到府上拜访请教吗?能不能留下尊姓大名?”他还不知趣地问。
“可以。维克多·康斯坦丁诺维奇·福尔茨。”
列宾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匆匆和旅伴握手作别。猛地,他感到自己掉进这大城市生活的冰冷海洋中。市声鼎沸,像暴风雨大作时的急流漩涡。他尝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惊骇情绪,远处异乡的吓人孤独感,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到底还是坐进了雪橇,车夫是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雪花漫天飞舞,大片大片地纷纷降落,旋即又溶化了。他眼睛朝宽阔的大街瞧个不停。处处摩肩接踵,车马辐辏。雪橇轿式马车,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人行道上,屋宇和商店前面,人流像做过一年一度的大弥撒后从教堂蜂拥而去似的,密密麻麻。大部分都是青年人,头戴三角形呢帽,佩着金线织绣的领章;也有不少军官、太太和小姐。正是下午四五点钟光景,有人向前,有人往后,行人车马络绎不绝。
一个远离家乡的年轻人,一个只凭画片想象过首都市容的人,此时此刻他的心境可想而知。阿尼契科夫桥上奔腾的群马雕塑,喀山大教堂庄严肃穆、从容典雅的柱廊,涅瓦河街口高耸云霄的尖顶,涅瓦河口矗立的雨西尊斯芬克斯塑像,以及他的幸福、他的命运所系的彼得堡美术学院,都曾千百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列宾心头猛跳:我真的不是在梦中。
“嗯,现在上哪儿去呀?”车夫问。
“找个旅馆住下,房钱便宜一点的——你知道这种客店吗?”
“打听一下吧,你想什么价钱合适?各种房间都有的。”
他们在一家名叫“麋鹿”的旅馆前停车,听说有一卢布一间的客房时,便在这住下来。
已经是暮霭四合的时候,房间内憋闷无聊。列宾要来一个小茶饮,就着锁形白面包一口接一口,也记不清喝了多少杯茶,暖洋洋地出了一身轻微舒服的汗。
在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之后,他感到这儿安谧宁静,称心如意,转眼间睡意起来。在干净舒适的被褥里,一会儿便美滋滋地睡熟了。好久以来,他没有这样自由伸直腿脚,铺盖这样暖和。
列宾醒得很早,天还没有放亮呢。这时,他仿佛第一次清醒过来面对现实,禁不住怦怦心跳,数清楚自己身边所带的钞票以后,他恐慌的心情更加厉害:他发现自己的皮夹里已只剩下47个卢布。在这间房子里还可以住上30天,往后怎么办呢?
“怎么样?”列宾问一个外貌忠厚的服务员,“要是论月租用这房间,一月我该拿多少钱?”
“说不上,先生,我们这儿还没有住过这么长的客人。要是你打算长住,你不如到外面给自己找个论月租一间的房子,好好儿讨价还价一番,租金少则6卢布,多则10卢布。这么着太不上算啦,一月花30卢布房钱!”
“怎么能找到这样的房间?到什么地方去找,跟谁打听呢?”
“就这么沿街一直走下去,瞧瞧大门上贴字条儿没有,看看上面怎么写的,再细问问扫院子的工人就行了。多走几步,靠小马路那儿,租费收得贱些。”
这一天,彼得堡的清晨刚刚开始,去找栖身之处以前,列宾先来到涅瓦河畔,他要看看美术学院。他长久地站在斯芬克斯身旁,四处张望,极力想更快地熟悉一下仅仅在画面上见过的景色。
美术学院那紧闭的大门充满着无限的诱惑力。似乎大门马上就会向他敞开,欢迎他的到来。从里边会走出一个人来,从外表就可以准确地猜出他是一个画家,可是大门并没有打开,时间尚早。
列宾呆呆地伫立在那里,心潮起伏,兴奋异常。此时此刻,他根本想不到,等待他的是重重障碍。他曾相信,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这扇大门。
在斯芬克斯身旁度过的这个晦暗的早晨,他永生难以忘怀。他新的人生之路就要从这里开始。在小马路上,根据大门上贴的招租字条,列宾登上了四楼,也就是顶楼。精明利落的女主人领他看一间房顶微拱的小房间。她想收6卢布的月租费。他觉得房间挺中意,便开始讨价还价,提出5卢布,因为这儿离市中心可够远的。
“那有什么关系,你是大学生吧,这对你还算方便,你不是要找离大学最近的地点儿?”
“不是。”她把列宾当成大学生的假设,让他受宠若惊,不禁难为情起来。“不是”,他嗫嚅着说,“我打算报考美术学院。”他一口气说出后面这句话。
“啊呀,那就太巧啦!我丈夫是建筑艺术家,我侄儿也正准备进美术学院呢。”
列宾心里高兴得突突直跳,他们讲好,这间房的月租金5卢布50戈比。
列宾恨不得马上搬进这开着阁楼式窗户的新居,动手画点什么。
转天一早,列宾便出发了,遍访圣像画师作坊,表示自愿报效,但到处都只是冷淡地登记下他的住址,答应需要时再通知。他感到这方面没有什么希望,便走去另向制作招牌的作坊打听——也是到处只答应需要时再通知。
精疲力竭,他顺便走进一家小馆吃饭。饭菜都十分香美可口,但用去了30戈比,如果天天都吃一顿这样的饭,剩下的几个钱马上便会花光。列宾身边还有从楚古耶夫带出来的茶叶和白糖。于是,他走进一家小店,买了两俄磅黑面包,拖着疲倦的步子走回寓所。傍晚时候,他就着黑面包喝着自泡的热茶,浑身冒汗,感到舒服无比。面包只花了3戈比,喝茶就块糖也所费无几!“日子应该这么过下去”。他心里思谋着。这个发现让他心花怒放,在重重危险面前,抖擞起精神来,唯恐饿死的恐惧心理现在消失了。
给列宾送茶炊的老太婆是房东的远亲,他求她在空闲时候边织袜子边坐着给他做模特。他调好颜色,兴致勃勃地画起她的肖像来,精心琢磨,把她柔细的皱纹用笔画到纸板上。
房东太太看见作品后,大加赞赏,列宾犹豫地发问:“我最近能见到您的丈夫——建筑艺术家么?”
“能呀,能呀”,她说,“正应该叫我那位瞧上你的大作才对,当然,我一点不懂,不过我觉得已经十分好了。听听他怎么说倒挺有意思,他是我们这儿的艺术家嘛。”
“啊,欢迎,欢迎”,列宾央求说,“能给他看,我可太高兴了。”
可爱的老太婆,那个模特,她不光天天早晨给列宾买来3戈比的黑面包,而且还想着把它在炉灶上烤热,喝茶时送来的正是香气喷喷、切好的一块块美味热面包片,使列宾感到自己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面包。黄昏时分,老太婆走来轻声细气地说:“房东亚历山大·德米特利耶维奇·彼特罗夫想知道,现在能到你这儿来吗?”
“啊呀,当然,当然”,列宾慌起来,“请吧,请吧,我已经恭候好几天了……”
门口出现一个非常谦逊、和蔼可亲,带着怯生生神色的人。他穿着皮毛镶边的长袍,头发棕黄,蓄着小连须胡。
房东的光临使列宾兴高采烈,请他坐下,给他端茶,顺便拿东西盖住自己吃的黑面包片——列宾感到惭愧。
轻轻咳嗽几声,柔和的噪音里显示拘束,他谦和、审慎、用极其诚恳和同情的态度,开始询问列宾的计划、愿望和所能指望的物质来源。列宾感到,他想的问题如此严肃,具有如此无法回避的重要性。他怀疑自己是否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把做不到的幻想当成可能实现的事来办,如今自己想赶快回去,趁早回转楚古耶夫,在目前还有可能回家的时候……
“嗯,嗯,就是这些,没有旁的问题哪?你已想到这里来啦,怎么想到这里来啦!不,老弟,不必这样,你已经干完了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你越过了卢比孔河。”列宾知道恺撒横跨卢比孔河这段故事,卢比孔河是古时南阿尔卑斯高卢与意大利之间国境分界的河流。公元前49年,朱里·恺撒不顾元老院反对,率军队越过卢比孔河,首先在意大利发动内战,终于夺取了罗马渡河时,恺撒曾慨然言道:“有进无退。”后也以此比喻采取义无反顾的决定性步骤。这个令人信服的伟大真理,现在从这个文质彬彬的谦逊人口中说出来,叫列宾感到无限高兴。他认真思索起来:打心眼里说,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从彼得堡退回老家去的。我对彼得堡的兴趣正在每分钟地增加。
亚历山大·德米特利耶维奇慢慢地问列宾读过些什么,知道些什么。
“嘿!怎么?你没看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好吧,那你就应该从这两部书入手。不必忙着去找,这种书眼下你也买不到,我借给你,不妨你仔细读读。我孩子们有这部作品。”
列宾和这位头发棕黄的谦逊长者交谈愈深,对他怀的敬意也愈大。他在物质方面的清贫显而易见,但贫穷并没有把他束缚起来,而是远远退在背后,他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对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有深刻的理解。这点很容易感觉出来,这使他变得崇高。他仿佛不是来自这个尘世。
“对啦,给我看看,给我看看,你是怎样描绘我们的老太太来着。我家里的人在那儿特别夸奖你呢。”
列宾把画拿出来。
“好,你已经画得挺好,你还有什么害怕的地方?用不着,一点也不用怕,你前途无量,当然,暂时你得稍稍忍耐,因为还没有人知道你,你去过爱尔米塔会美术馆没有?”
“没有,这很难。听说,上那去需要门票,还得穿燕尾服。”
“嗨,并不像传说那么可怕,穿燕尾服是老早以前的规定了。你无论如何要常去开开眼界,这对一个画家非常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内行,叫他们领你去。薛沙在绘画学校念书,让他领你去买门票。年轻人,你现在是背水一战,绝不能打退堂鼓!对,目前,你最好先进职业介绍所附设绘画学校,那儿一年交3卢布学费。校址在市场附近,皇宫大桥对面。”
一席话说得列宾心花怒放,满怀希望,很快便在绘画学校报名注册。但这儿上课时间每周只有两个下午,外加星期日一个早晨。而美术学院每天清晨到晚上7点,一直不断都有课。
列宾犹豫再三,最后鼓起勇气走进美术学院,打听入学有什么手续。
列宾终于怯生生地走进了学院阴森森的走廊,门上挂着那些“院长”、“教务长”的牌子使他忐忑不安。他觉得大概“教务”还不那么可怕。没想到就是这个外表道貌岸然,内心却冷若冰霜的官僚几乎堵死了他进美术学院的道路,和美术学院教务长的第一次谈话,在他心里留下了疑惑的阴影。
列宾把装着他少年时代习作的口袋交给教务长。一张画的是他小的时候学习过绘画基础的楚古耶夫测绘学校校舍,还有一些栩栩如生的人像素描,全都是以家里人和邻居为模特儿,画得从容自信。
李沃夫草草地翻看一下,然后以不容反驳的口气说:
“进美术学院,您还太早。您的画线条不清,构图也不好。”
此时,他又一次听到了“线条”这个怪词儿。(客观地说,排线条是素描练习的重要技法之一,但并非是品评一件作品的唯一标准。)第一次提到这词的是在美术学院学习过的画家彼尔桑诺夫,这位同乡往楚古耶夫写家信时对乡亲们讲过,他的同学们画画如同“印刷”一样,线条细腻清晰。当时列宾就没明白这话是褒还是贬。正是彼得堡美术学院毁了彼尔桑诺夫,他的才能在那里干涸了,回到家乡时几乎变成了疯子。
列宾在家乡楚古耶夫没画过石膏像和人体,而且根本不懂得所谓“线条”和经美院认可的经典素描不可侵犯的规范。如今又是这个“线条”堵死了列宾进美术学院的大门。年轻的他遇到的是彼得堡显贵的傲慢与偏见。
难道列宾的理想就这样破灭了?难道就这样再回到楚古耶夫?回去爬教堂那高高的拱顶下的脚手架,画基督、画圣母、画天使,当一辈子圣像画匠吗?不!列宾要先读绘画学校,然后再考美术学院,实现自己的理想。
绘画学校的校长是季雅科诺夫,老头身材颀长,头上白发苍苍,活像圣经上的“万军之主”。他神情威严,迈着稳重的步伐,从校长室走出来时,教室里的人都屏住呼吸,一齐朝他转过头去。
教师蔡尔姆的几张素描挂在墙上,绘画的技术高超,画得干净利落,大概,彼尔桑诺夫写信谈的就是这类素描:“素描就跟印出来的一般。”
但列宾禀性难移,力求表现出石膏模型的体积,不注意表画效果。
鲁道尔夫·茹科夫斯基老师走到列宾后面:“你从前在哪儿学的画?”他问列宾。“在楚古耶夫”,列宾回答,“不过像这样在纸上画素描还是第一次,我们在那儿主要是画圣像。”
过一会,他和蔡尔姆老师一起走过来,“不错,”蔡尔姆说,“一眼就看得出来,他画过油画,掌握漂亮的铅笔技法恐怕很困难,瞧他涂的阴影多脏,多没条理。”
在石膏像和头班学素描不久,圣诞节就到了,学校放假,班上同学的作品全部交到事务员处。作为试卷等待评分。
过节以后,同学们回到学校,蜂拥到排行榜前找自己的素描成绩。
列宾也挤了进去,但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他的心里像开了锅似的翻腾起来。他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被刷了下来,画面太脏?不会涂阴影?
大家乱哄哄地寻找自己的姓名,议论纷纷,列宾伤心得差点没有流出眼泪,最后忍不住问一个和善的小孩: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榜上没有姓名?还能补考吗?”
“我不清楚,”他回答说,“大概因为素描的成绩太差吧。你问这个干什么?这榜上没有你的姓名,你姓什么呀?”
“我是列宾,我才来不久……”
“你怎么啦!列宾不是头一名吗!”
列宾以为他拿自己开心,又走到嵌在红木玻璃框里的名次表跟前。第一个写得清清楚楚是“列宾”。
“也许还有另一个列宾吧?”列宾还不放心。
“说不上”,他回答,“事务员正在发卷,画上都有老师评分时拿朱笔批的名次。”
列宾要回自己的卷子,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的卷面上,有笔锋遒劲的花体签名“鲁道尔夫·茹科夫斯基”,名次为第一名,写这个字下笔用力过猛,有铅笔折断留下的痕迹。
一大群不大相识的孩子围着列宾,爱不释手地看着他的画,这时挤进来一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平时,他总本能地背后摆动自己一只干瘦的手,像一条鱼的尾巴。
他拿过列宾的素描,伸手放在离眼睛较远的地方,摇头晃脑,像保护人似的周身打量列宾。
“在这所学校,你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我要是有你这种本事,一定上美术学院参加考试,进那儿做旁听生。手续很简单,只要向监督提出申请,通过石膏头像素描的考试,剩下的便是每年交25卢布的学费。你可以天天画石膏像,很快进入人像写生组。每4个月参加一次奖章竞赛,最要紧的是,那已经用油画画模特,每月按题目,自己布局构图画草图。”
他这番描述,说得列宾的心里热烘烘的。
“话不错,”列宾说:“可我上哪搞25卢布呢?这是大数目的钱……”
“你真傻!好好打听打听,想办法认识一个以保护人自居的将军,奖励艺术委员会的会员,他们喜欢利用年轻人来沽名钓誉:瞧,某人是我保护的哟!见了你,只要他不是白痴,事情一定能成。在美术学院,你也会是佼佼者。”
列宾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回寓所,恨不能立刻把成绩告诉房东,那位建筑师朋友。
“我可以见亚历山大·德米特利耶维奇吗?”列宾敲着门。
“嗯,嗯,谁呀?”屋里传出建筑师的声音。
“我,列宾。”
“学校里情况怎样?”
“我正飞跑回来告诉您,我得到了第一名。可是我纳闷这第一名来得奇怪,希望您作为艺术家,给我解释一下真相……”
“原来这样!快,给我看看画。”
“你瞧:画面很脏,有多处擦抹的痕迹。我还没有学会涂阴影呢。”
“等等,等等。你瞧见没有,整幅素描特征鲜明,层次分明,很有立体感,而最大的优点是你对物象有惊人的敏锐感觉,从画中可看出,你下笔准确而且感情充沛。至于涂阴影,那种松散整洁的线条,如今已过时了。关键是要抓住对象的本质,而不是表面效果,娜斯茜卡!娜斯茜卡,快来看,我们未来的画家在学校名列第一!”
活泼的娜斯塔西雅·彼得罗芙娜,边放衣袖边走进来。
“恭喜,恭喜。我可是总跟孩子他爸念叨,瞧着吧,我们的房客有朝一日准会当上教授!”她响亮快活地笑着。“画得真好!瞧,我说得不错吧,我是个讲实际的女人,你当上教授那天,千万可别忘了送我一磅压紧的黑盒子啊……”
列宾被意想不到的第一次成功所鼓舞,于是下决心去报考美术学院,结果他考中了,但只能作旁听生。也就是说,他要交25个卢布的学费。列宾已一贫如洗,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唯一的办法是求人赞助。
当时,在彼得堡住着一位富豪普里尼会科夫,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将军,现任邮政大臣。他喜爱艺术,收藏绘画,并且资助过一些贫穷的画家。列宾决定忍受痛苦和屈辱去找他。
将军的厨娘叫塔季雅娜·费多托芙娜,曾作为一名香客去过楚古耶夫,在列宾家住了一个冬天,相处很好,母亲曾写信请她关照儿子。列宾靠着这层关系,从后门进去见了厨娘,她马上跑出来用最悦耳的声音亲切向列宾问候,还嗔怪列宾为什么一直不去看她。铺有台木的小木桌上摆出了热气腾腾的小面包、美味的奶油和咖啡。列宾和她坐下来,慢慢回忆着奥西诺夫卡村,那里的人以豌豆做咖啡的代用品,喝不到这种真正的外国饮料,连咖啡壶,当时也是塔季雅娜·费多托芙娜带到列宾家的,这些人压根就没见过这种东西。
谈到末了,厨娘表示把列宾的情况呈报给将军大人,并再三叮嘱列宾要常去看她。
不久列宾从市邮政局收到她的一封信。她通知他必须在当天9点半钟去见将军大人。
列宾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手上流着汗水,不断地颤抖。他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大厅,等候将军大人的接见。大臣年过花甲,穿着红翻领深蓝色的长礼服,随着将军的到来,一股高级雪茄和香水的混合味道也一齐飘进大厅。
列宾根本没有想到,将军会把手伸给他,他没去握这只手,而是轻轻吻了一下,就像过去在教堂里吻大主教的手那样。可以说将军掌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未来,他若能给25个卢布,列宾就能交上美术学院的学费呀。
将军在不停地提出种种问题之后,终答应如数付钱。列宾欣喜若狂,伏下身去,吻了一下天鹅绒服的下摆,激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他顺着不透阳光的走廊一口气跑了出来,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这回也可以进美术学院了,尽管他不愿再考虑他所蒙受的屈辱,可是,有关这一时刻的记忆都十分顽强。直到晚年列宾都难以忘怀。
进彼得堡美术学院读书以后,列宾又碰到教务长李沃夫,这位先生气得几乎发狂,并以鄙夷的口吻说:
“是啊,学费你是交上了,可你只能是个劣等生。”
列宾在后来的生涯中,发奋用功,以优秀的作品做出了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