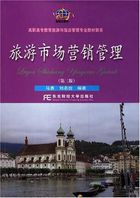埃默里的小支队已出发九天了,是什么使他们放慢了脚步呢?他们遇到了危险或无法克服的障碍吗?他们为什么会耽搁呢?他们的朋友甚至不敢设想他们会集体失踪。
能够想象,被围困在山顶的科学家们是多么地焦急和担心。他们的同事离开已经有九天了,一般条件下六七天就够了,他们历来积极勤恳,专注于科学研究事业,能否到达沃尔奇利亚山顶是整个测量工作成败的关键,这一点他们都很明白,为了成功,他们会竭尽全力的,就算耽搁了他们也不应受到指责。所以,如果九天之后对面山头上仍然没有信号灯的话,他们很可能是牺牲了或者被其他游牧部落俘虏了。
埃弗雷斯特上校和同伴们的头脑中充满了沮丧和痛苦,为了开始晚上的观测,他们是多么焦急地盼望太阳快点下山,而每次观测又是如此地细心。
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望远镜的目镜上,他们把所有生命都浓缩在望远镜的视野之内。3月3日,他们在山顶上烦躁地走来走去,相对无言,同样的希望充满心中,也感到前所未有的郁闷,就连沙漠的燥热、行程带来的疲惫和口渴的煎熬都无法与他们此时的无奈心情相比。
最后一片“土猪”肉被咽下肚内,储存的白蚁也所剩不多了。
夜幕终于降临了,没有月光,天空一片澄澈,是观测的好天气,然而,沃尔奇利亚山上仍没有一点光亮。埃弗雷斯特上校和斯特克斯轮流守候在望远镜后,直到天将破晓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太阳很快就要升起来了,观测只好就此罢手。
山下的强盗们却不急不躁,似乎他们决心这样围困下去,直到山上的人被饥饿所征服。4日这天,被困在山上的人们又得经受饥饿的折磨了,可怜的人们只能以生长在岩石缝里的球状茎为食。
他们曾多次争论着是否让莫孔去恩加密湖北岸打些猎物,但恐怕会被马科罗罗人发现,那样,轮船的暴露会使他们抢劫轮船或堵往北岸,将来撤退会有危险,因此只能要么一起逃,要么呆在一起。至于要在完成测量实验之前离开的想法他们根本就没有产生过,他们需要等待,直到最后一线成功的希望破灭,这只是一个耐心的问题,他们会耐心地等待。
白天,驻扎在山脚下的马科罗罗人显得骚动不安,他们频繁的来往让莫孔有些不安:他们是打算夜晚往山上攀登呢,还是想立即侵袭或者准备撤退了(当然这只是美妙的幻想)?
经过细致地观察之后莫孔预计到马科罗罗人将要发动进攻了,这些匪徒手里都拿着弓箭、长矛,妇女和小孩在几个男人的引导下离开营地返回东部去了,看来他们要全力拼搏了。
莫孔提醒大家要严加防范,并且所有武器整置待发。因为孤注一掷后进攻人数会剧增,几百马科罗罗人的攻势将是难以抵挡的。堡垒万一被攻破,轮船就被提上议程,以备在情况急迫的情况下能够随时出航,但启航准备要等到太阳西下之后,以防白天暴露会引起敌人警惕。
晚餐就只有些坚果和球茎——这点食物要维持着他们为生命而战斗的体力简直是太残酷了。但他们已立场坚定、无所畏惧地等候着。
大约在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水手中的一名机械师偷偷地下山朝轮船奔去,很显然,埃弗雷斯特上校是计划在万一无法抵挡的情况下撤离斯科泽福山。上校对此时放弃观测工作深感遗憾,特别是在晚上,因为埃默里和佐恩随时都可能在沃尔奇利亚山的顶峰亮起信号灯。
水手们部署在堡垒的废墙脚下,机关枪装满了子弹,旁边还有充足的后备弹药,可怕的枪管张开向着四方,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守卫堡垒,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几个小时。
上校和斯特克斯继续轮流守候在望远镜旁仔细地观察远方的沃尔奇利亚山,天边一片黑暗,明亮的星星在夜幕中顽皮地眨着眼睛,仿佛故意逗着这些来自欧洲的天文学家,空中连一丝风也没有,这种天气确实罕见。
莫孔站在一块突起的石头上倾听着发自山脚下的喧闹声,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响。果然不出莫孔所料,马科罗罗人已开始向山顶进攻了——他们准备做最后的尝试。
直到晚上10点多,敌人还没有出现在眼前,他们早已熄灭了平原的篝火,营地已经隐藏在黑夜中了。猛然间,莫孔发现一些影子正在山坡上晃动,侵犯者距山顶已不足100码了。
“注意!有情况!”他喊道。
堡垒里的人马上冲出来朝着侵略者猛烈地开火,而那些可恶的亡命之徒根本不管猛烈的火力仍缓慢地向山顶一步步逼近。借着子弹的火光欧洲人可以发现,敌人人数之多使长久抵抗难以可行。
尽管他们几乎弹无虚发,敌人也伤亡惨重:已有成片的马科罗罗人倒下去,接连不断地滚下了山坡,但什么都制止不了他们的进攻,那些玩命的敌人像野兽一样吼叫着往上冲,他们仍然朝山头冲来——马科罗罗人已决定用血的代价来换取山头的统占权。
埃弗雷斯特上校身先士卒,他的同伴们勇敢地追随其后,就连从没摸过枪的帕兰德也拿起来福枪加入了战斗,默里进行游击作战,他一会儿单膝跪着点射,一会儿趴着扫射,直到来福枪由于不断射击热得烫手才稍作歇息,一度情绪高涨的莫孔此时也恢复了原有的猎人的冷静,变得有耐性、大胆、自信。
围攻的敌人不仅从斯科泽福山的南面进行侵袭,连其他两侧都要被他们全部攻占了。这些不怕死的马科罗罗人完全不管欧洲人的顽强抵抗和强大的火力,他们只管往上冲,欧洲人的火力再密集也阻止不了人潮汹涌,一个敌人倒下了,马上就有二十个敌人冲上来,战斗了约半个小时后上校发现自己的队伍就要被包围了。
被打死的敌人的尸体充当了活人的脚梯,有的甚至用死尸作盾牌来掩护自己。科学家们清楚地知道要想从这批生性好杀戮的野蛮人手里幸免真是万难,他们野兽般的行径比老虎狮子更凶残。
10点半时,第一批马科罗罗人抵达了山顶,被围困的人因此失去了使用枪支的优势,为了避免发生肉搏战只好在墙后面躲了起来,幸而他们当中没有人受伤,因为敌人一直没有使用射箭和投长矛。
“撤!”上校的声音压过了纷乱的嘈杂声。
所有人进行最后一次射击退回了堡垒的墙后面。
他们的后退招来了敌人兴奋的尖叫声,一群劫匪立即出现在破墙前的入口处。
突然,一阵雷鸣般的巨响震入耳膜,拥有25支枪管的机关枪怒吼了,这种枪有自动上弹装置,而且射程很远,其威力足以让刚站稳脚跟的敌人全部倒毙,转眼间惨叫声此起彼伏,而敌人在倒毙之前射出的箭对科学家根本造不成任何伤害。
“它真是棒极了。”莫孔评价道。
但机关枪却停止了吼叫,在枪林弹雨的威慑下马科罗罗人迅速消失,他们躲藏在堡垒四周,在入口处撇下了几十具尸体后暂停了攻击。
趁战斗暂停休息期间,埃弗雷斯特上校和斯特克斯专心致志地观察着沃尔奇利亚山峰,他们已忘记了危险,一番休整之后,马科罗罗人又发动了进攻,上校和斯特克斯两人轮流作战和利用望远镜观测。
战斗又打响了,机关枪并不能照顾到每个敌人,他们又并肩战斗了一个小时,退守在堡垒里的欧洲人除少数几个被标枪擦伤之外几乎都毫发无损。
11点半左右,战斗进入最惨烈阶段,山顶枪声和喊叫声响作一团,斯特克斯来到埃弗雷斯特上校面前,他看上去半是喜悦半是惊恐——一支箭正好射穿他的帽子,箭尾还在他头上颤抖。
“信号灯!信号灯!”他朝上校叫道,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啊!”上校一边上子弹一边叫嚷道。
“没错,信号灯!”
“你已经发现了吗?”
“对!”
上校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幸福感,他放光了子弹之后就冲进了堡垒,他的大声欢呼比刚才打仗还要兴奋得多,他克制地跪下来仔细注视着望远镜的目镜,仿佛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在这一刻凝固了。宝贝,确实没错!沃尔奇利亚山顶正闪耀着一盏大家期盼已久的信号灯!是的!最后一个三角形已经找到了它的顶点!
虽然守卫者们努力做到了寸土不让,但敌人最终还是越过了围墙。埃弗雷斯特上校和斯特克斯冒着枪林箭雨开始了观测,他们俩轮流进行观测和记算,帕兰德像往常一样泰然自若地进行记录和纠正。经常有箭擦着他们的头顶撞在身边的墙上,但他们的目光始终对准对面山头的信号灯上,聚精会神地检验着测量结果。
正当斯特克斯说“要不要再观测一遍”时,一颗巨大的石头击中了一个测量仪并把它掀翻摔得粉碎。
但观测工作已全部完成了!信号灯——三角形顶点的位置已被精确地测算出来了。
现在应该带着科学成果光荣地撤离了,马科罗罗人已攻进了围墙,随时都有可能攻入堡垒。
上校和他的伙伴们重新拿起武器一边进行射击一边朝着缺口转移,所有的欧洲人都安全聚集在一起,他们当中只有几个人受了点轻伤,水手们决定留下来掩护他们先撤退。
正当他们朝山下撤退时斯特克斯叫道:“我们的信号灯!”
他们也需要亮起信号灯以回答北边山头上的两位年轻的科学家,以便使他们能测定斯科泽福山的位置,无疑他们也正在山顶焦急地等待着这边的光亮。
“我们再反击一次。”上校喊道,当同伴们以超凡的毅力把马科罗罗人再次赶退时,上校冲进了堡垒,木塔内有许多干燥的枯木,一点火星就可将它付之一炬,上校撒下些火药将枯木燃着了,当火势“噼噼啪啪”开始旺盛时,上校已逃离开堡垒重新回到了撤退的行列之中。
几分钟之后,所有人员在一片箭雨之中撤到了山脚的小港湾,引擎顺利地启动之后,轮船载着科学家们迅速逃离险境破浪前进。
很快船上的人就能够看到斯科泽福的山顶了,山尖正处在一片熊熊火海之中,这强烈的火光很容易传递到沃尔奇利亚山顶的望远镜上。
英国人和俄国人一齐欢呼着朝巨型火把致意。埃默里和佐恩不会抱怨什么了,他们升起了一颗星星,却得到了一个太阳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