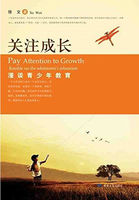“五十年前,我是一个有势力、有威望的人,住在阿尔及尔,贪欲驱使我把一条船武装起来,从事海盗活动。一连干了许多年,从未失手过,因此,我常常得意忘形。然而,有一天,我在撒丁岛把一个托钵僧带到船上。他说,他想不花钱周游世界。我和我的同伙都是粗人,办事没有头脑,不知道此人是神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我多次羞辱他。一次,他出于圣洁的激情,对我罪恶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谴责。晚上,我在我的舱里和大副喝了很多酒,无名火起。我想,即使是苏丹,我也不会让他说我半句坏话,现在一个僧人竟敢对我说三道四,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一气之下冲上甲板,把我的匕首刺进了他的胸膛。临死,他对我和我的船员进行诅咒,要让我们欲死不得,欲生不得,直到我的头颅触着泥土。
“我哪里肯信一个要死的人说的话,便吩咐人把他扔到了海里,继续吃喝玩乐。谁知就在当天晚上,他的诅咒应验了,我的一部分船员起来反对我,结果发生了一场恶斗,拥护我的人都被杀死,我也被钉在桅杆上。但对方也是身受重伤,一个个地死去。
“不久,我的船就成了一个大坟墓。我眼前一黑,呼吸也越来越艰难,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呢。谁知这不过是肢体的僵硬,使我不能动弹而已。第二天晚上,在我们把托钵僧扔下海的时候,我和全体船员一齐苏醒过来,大家又活了,不过,除了那晚上已经说过的话和作过的事外,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作。
“事实证明,托钵僧的诅咒是千真万确的,这诅咒整整折磨了我们五十年。每当风暴来临时,我们都喜极而狂,扯起满帆航行,希望能在一个暗礁上撞得粉身碎骨,也好让这颗筋疲力尽的脑袋,沉入海底得到安息。然而,我们的希望并没有实现——我们求死也不得。现在我终于可以死了,让我再感谢您一次把,陌生的救命恩人,假若大恩能用金银财宝来报答的话,就请接受我的船作为我感恩戴德的表征吧。”
讲完这段经历,船长便面带笑容地闭上了双眼。他马上就化成了灰,和他的那些伙伴们一样。我们把灰收拾起来,装进小盒子,埋葬在海边。我从城里请了几个工人,修复了船只。我把我在船上所获得的货物换成其他货物,得到了巨额利润。于是,我雇了几个水手,付给朋友穆伦丰厚的报酬,乘船返回祖国。我绕道航行,停靠许多岛屿和国家,把货物推向市场。先知保佑我的买卖。九个月后,我回到巴尔索拉。我的财富在已故船长赠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还多。乡亲们对我的致富和运气感到不可思议,还以为我是找到了着名旅行家辛巴德的宝石谷。——由他们瞎猜吧,我管不着。从此以后,巴尔索拉的年轻人一满十八岁,就得出门去寻找像我那样的财运。而我则在家乡过着清闲安乐的日子,每五年到麦加旅行一次,朝拜圣地的真主,一来感谢他保佑我,二来替船长和他的船员们祈祷,求主把他们带入天堂。
(全书完)第1章断手的故事
我从小出生在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长大。我父亲在宫廷中做事,空闲时间经营一些香料和丝绸,赚了不少钱。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的耳濡目染,使我无形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在亲自启发开导我的同时,又让我去教士那里听课。当我稍大一些的时候,他决定要我接管他的商店,但是,当我显露出来的才华高出他的期望值的时候,他又决定按朋友们的建议,要我学医。因为,一位医生的医术如果高于一般的江湖医生,在君士坦丁堡的机遇是很多的。同时,也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有一天,我家来了许多法兰克人,其中一人劝我父亲把我送到他的祖国去,到巴黎去学习。在那里,学习这种专业是免费的,而且能够学得最好。他甚至想在他回家时把我带去,不要我出钱。我父亲年轻时也喜欢旅行,就欣然同意了。这个法兰克人对我说,我可以在三个月内做好出发的准备。能到外国生活,这使我高兴得有点忘乎所以,恨不得马上就上船出发。那个法兰克人终于做完了生意,准备上路。
出发前夕,父亲把我领到他的小卧室。在那里,我看见桌子上放着漂亮的衣服和武器。
但是对我的目光更有吸引力的,还是一大堆金币,这么多金币放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
父亲拥抱我,对我说:“亲爱的孩子,我给你买了旅途上穿的衣服,那些武器是给你的,是我出国时你祖父给我挂在身上的。我知道你会使用。但是,在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决不要使用它。要打的时候,就一定要狠狠地打。我的财产不多,亲爱的,我把它们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是你的;第二部分是我的生活费和备用金;第三部分对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那是供你救急之用的。”我的老父亲这样对我说,两眼泪光盈盈。这或许是一个不祥之兆吧,因为我从此就再没有见过他。
我们一路上非常顺利,平安抵达。不久就到了法兰克人的国家,又走了六天才抵达大都市巴黎。我这位法兰克朋友替我在巴黎租了一间房子,劝我不要乱花钱——这时我身边共有两千银币。我在这个大都市住了三年,学到了作为一个名医必须具有的医术。但若是说我很愿意留在巴黎,那我就是撒谎了,因为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不适合我,同时,我在巴黎交到的好朋友也寥寥无几,不过都是些高贵的青年人罢了。
我的思乡之情终于变得更加强烈了——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得到我父亲的任何消息,因此,我抓住一个好机会,回家去了。
这时法兰克斯坦正要派遣一个使团到东方,我应聘作为外科医生加入使团的随员团中,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但我发现我父亲的房子上了锁。乡邻们看到我都很吃惊,他们告诉我,我父亲已于两个月前去世了。在我幼年时代教导过我的那位教士,给我送来了钥匙。我孤零零地走进那所荒凉的房子里——我父亲留下来的东西全都没有动,只有他答应死后送给我的钱不见了。我向教士追问这笔钱。他鞠了一个躬,说道:“您父亲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圣徒死去的,因为他把他的这笔钱捐赠给教会了。”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证据反驳教士。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并没有把所有房子和父亲的货物当作捐献物品。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不幸。可是自从那时起,打击一个一个接连不断,我作为一个医生,一直没有把名气传出去,因为我很清高,不好意思到市场上去推销自己。我没有父亲的处世能力和社交才能。他如果还健在,肯定会把我介绍给富贵人家的。这些人再也不会想到我这个可怜的扎罗伊科斯了。父亲的货物也找不到市场,因为自从父亲去世后,老客户们纷纷走了,新的客户得慢慢寻找。
当我对这种处境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在法兰克的时候,经常看见我国同胞,他们走遍全国,在各个城市的市场上展销商品。我记得很清楚,当地人喜欢购买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来自异国他乡。做这种买卖,可以获得百倍利润。我很快作出决定,变卖父亲的房子,把所得的一部分钱交给一位可靠的朋友保管,又从剩下的财产中拿出一些购买法兰克所缺少的物品,例如围巾、丝织品、化妆品和食油等。我在一条船上租了一个舱位,踏上了第二次赴法旅程。
出了达达尼尔海峡,我的运气似乎来了。我们的航程短,而且顺利。我走遍法兰克的大小城镇,发现各地顾客踊跃购买我的货物。我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个朋友不断发来新鲜货,我一天一天地富起来,终于积蓄了足够的财富,深信可以大胆地做一笔较大买卖了,便带着货物来到了意大利。有一点我也必须承认,那就是:我之所以赚了不少钱,还得益于我的医药知识。我每到一个城市,都请人张贴广告,宣传来了一位希腊医生,治愈过好多人的病。我的药膏和冲剂确实帮我赚了不少钱。于是,我来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打算在这个城市多呆些时间,一方面,我在这里感觉很好;另一方面,在长期奔波劳累以后,我也想得到充分休整。我在圣克罗齐区租了一个门面,门前很宽阔,人流也比较多,非常适合卖东西。在不远的一家旅店租了几个漂亮的房子,房子外面有一个阳台。一切安顿好了之后,我马上贴出广告,说我在这儿行医兼经商。我的铺子刚一开张,顾客就川流不息地涌来。虽然我要价高一点,但还是比别人卖得多,因为我对顾客很殷勤、和蔼。
我在佛罗伦萨市很愉快地度过了四天。有一天晚上,当我已经打洋,正要照例盘点时,突然发现一个小盒子里有一张便条。我不知道这是谁放进去的。我打开纸条一看,原来是邀我今晚十二点整到一座桥上去,这座桥大家称为古桥。我考虑了很久,请我的人是谁呢?既然我在佛罗伦萨一个人也不认识,这人想必是要暗中带我去看一个什么病人——这样的事本来是屡见不鲜的。因此,我决定前往,但为了确保安全,我把父亲以前送给我的佩刀也带上了。
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我独自动身前往,很快到了古桥。桥上不见人影,我决定等到他出现的时候,相信他会叫我的。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月光如水。我俯首观赏阿尔诺河水,见它在月光中泛着微波。市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十二点。我直起身来,眼前出现了一个彪形大汉,一件红色斗篷把他全身裹住,斗篷的一角遮住了他的脸。开始,我有点怕,因为他过于突然地站到了我的背后。但是,我马上控制住了自己,对他说:“既然是您把我叫到这里来,那么我想问你,有什么吩咐?”
披红斗篷的人转过身去,慢慢地说:“跟我走!”
天啊!单独同这样一个陌生人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这的确使我有些胆寒。我站着不动,说道:“这样不行,亲爱的先生,您首先得告诉我上哪儿去。另外,还要烦您稍露尊容,让我看看,您是否对我怀有好意——不然的话,我只好说:‘恕不奉陪。’
披红斗篷的人对我的话似乎不当一回事。“如果你不愿前往,扎罗伊科斯,那就不用来了。”他一面回答,一面向前走去。
我忍不住火冒三丈。“您以为您是谁,”我大叫道,“凭我这样的人会随便让一个浑小子捉弄吗?您以为我会在这种寒冷的夜晚白白等人吗?”
我一个箭步快速来到他背后,一手抓住他的披风,咆哮如雷,同时另一只手握住刀把。
可是,披风虽然抓住,人却从前面第一个转弯处溜走了。我的怒气渐渐平静下来。披风尚在我手里,这就会使我找到线索,弄清这件奇怪的事情。于是,我把它披在肩上,向住所走去。走出大约还不到一百步远的时候,突然有人紧紧地贴着我旁边跑过,用法文悄悄说道:“当心些,伯爵,今晚上干不成了。”
正当我想回头看时,那人已经跑过去了,只见一道黑影在房子上一晃即逝。我知道这话不是向我说的,而是向这件披风的主人说的,但我仍然没有找到弄清真相的线索。第二天早晨,我考虑了对策。最初,我打算拿着斗篷去叫卖,就好像它是我捡来的一样。但这样一来,那个陌生人有可能通过第三者取走,我就得不到弄清事实真相的线索了。我一边思索,一边更细心地观察这个斗篷。面料是紫红色的热那亚厚天鹅绒,边料是阿斯特罕毛皮,上面绣满了金线,斗篷的豪华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决心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
我把斗篷带到街上自己的店子里去出卖,给它定了很高的价格,我相信找不到这样肯出钱的顾客。我的目的是,对凡是来打听这件皮货的人,我都仔细观察,因为失去斗篷的那个陌生人,虽然当时是一闪即逝,但毕竟露了一下脸,即使在成千上万人中,我也会把他认出来。有兴趣购买的人很多,它极其漂亮的款式吸引着所有过路的顾客,但是没有一个人的模样像那个陌生人,没有一个人愿以二百枚金币的高价买那件斗篷。我特别注意到,当我问起,佛罗伦萨是否做过这样买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没有,并且肯定,从来没有见过一件这么名贵的、这么令人爱不释手的工艺品。天快黑了,走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经常光顾我的商店。今天,他出很高的价买这件斗篷,把一个钱袋往桌子上一放,高喊:“上天作证,扎罗伊科斯,我一定要买下你的斗篷,就是去当乞丐也在所不惜。”
他一边喊,一边不停地数金币,这真让我进退两难。我把斗篷挂出来,完全是为了引起那个陌生人的注意。谁料到来了个傻小子,竟然愿意出异乎寻常的高价买它。遇到这种情况,我有什么办法?不卖也得卖。仔细一想,觉得卖有卖的好处,可以作为对于我那个夜晚冒险行为的一种补偿。那小子披上斗篷就走,可是还没有出门又折了回来,把一张贴在斗篷上的纸条揭下来,扔给我,说:
“这里,扎罗伊科斯,挂了一件东西,看样子不是斗篷原有的。”
我信手接过纸条,并不在意,随便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今晚十二点请将斗篷送到桥上,四百金币相谢。”
我被这一消息惊呆了,虽然我开始没有当一回事,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跑了出去,快步追上了那个买走披风的小伙子,递给他二百金币。我说:“请收回你的金币,朋友,把斗篷还给我吧——我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