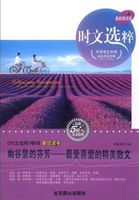亲爱的朋友!
我从“奥菲厄斯”那儿来,这使我的心温柔,安静下来。我流了眼泪,但没有痛哭。我的痛苦是和缓的,每想到你悲伤便消失了,我的思念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我哭悼死者,但我的爱情仍只倾注在你的身上,我这颗心偏要二者兼顾。
何等奇妙的艺术啊!肯定是一种上帝的馈赠!音乐必定是一个细致的人发明出来安慰不幸的人的。
亲爱的朋友,一个人对于无法避免的痛苦除掉找镇痛剂以外,别无办法,而全世界的东西能作为我的心灵的镇痛剂的仅有3种。我心爱的人啊,最有灵验的是你,你可以减去我的痛苦,可以使我心醉,使我忘记过去和未来。在一切药物中,除掉这种最好的外,就要算鸦片烟了。这东西对于帮助我抵抗失望很有价值,它的效益是关于生理上的,但我却不可一日没有它。第三种便是音乐。那美丽的音符差不多可以使我忘却了悲哀不幸,当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刻,音乐却没有对我现在这个时刻富于真正的价值。
亲爱的朋友,当你还没出发之前,我一次也没去“奥菲厄斯”,我不需前往,因为你在我这儿,你刚才还在我这儿,我等待着你,这便是我生活的内容,这就足够了。可是我现在,憔悴地呻吟在荒野之中,失望与精神上的痛苦不断地袭来,我必须寻找各种方式来拯救自己,然而这些方式对于损害我生命的毒物来说,显得何等软弱无力啊!
亲爱的朋友,一种内在的声音悄悄告诉我:“你将再看到他,你的生命将会重新获得价值,你的忧愁也将不至于难以忍受!”即使这只是幻想也是好的,因为这是最终的幻想,格里朗伯爵来听音乐剧,坐在王家的包厢里,和成千的格里朗家族都在这里。我照常坐在我的包厢里,我看见了他的夫人。他像平常一样和我打招呼,并不令人讨厌。伯爵到我的包厢来看我,我们并没有说起他的夫人,而谈了一阵子关于他的事业,一大笔财产就是一大宗负担,他在美洲有工厂、商店,还有法律事务所,他总是忙忙碌碌。因此可以获得利益,但这并不是理想的事业,幸福并不存在于丰富的财产中。幸福在哪儿呢?幸福在一个寂寞而又笨拙的学者的工作室中,或者是在工厂中的第一流的作业者手中,他们都在创造,而不至于精神枯竭。或者是在忠实的农民中间,他们有许多儿女和相应的收入。地球上其余部分都充满着愚人、蠢蛋和无赖汉!
我读过一部关于戏剧的书,很不令人满意,但其中也有几点可以称道的,我为你留着这本书。
整个世界都是暗淡无光。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常常想在门上这样写着:“走进来的,是向我致以敬意;不进来的,却也让我非常欢喜!”
马蒙泰尔先生向我请求:要在我这里朗读一个新的音乐喜剧,他来了,我们共有12名听众。大家喜欢听《老新郎》,这是剧的名称。第一幕开头使我觉得很混乱,我所听到的全部出乎常理,你知道么,我竟没听进一个字。就是绞死我,我也记不住剧中的一个人物和一点情节来,真的,毫不夸张。我退了出来,并且说了实话,同时也觉得他们也坚持不了多大会儿。当我听到同伴们重新高声争论起来时,我真有点惊讶了。
自从我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在某事物上之后,我最喜欢朗诵。这使我自由自在。在交谈时,我自己绝不介入,他们常是互相吵闹,特别是那几个争强好胜的家伙,吵闹得最凶,有时真令人难堪。你当相信,我只爱和你,或和查斯泰卢克思的骑士闲谈。
晚安?现在应当让你休息了。我在火车中写的这封信。演音乐剧的日子是我最舒服、畅快的日子。我独自呆在剧场,将家中的门紧锁着。达列伯特已经见到了那“小丑”,“小丑”对他所说的笑话比“奥菲厄斯”要多。各有各的长处。
现在要暂时分手了,明天再会!
1774年10月14日,星期五晚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