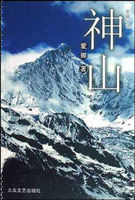偌大的天然气管道袒露一侧。
心猿意马的牛二蛋与马寡妇各在自己的田里锄务杏苗。牛二蛋哼唱民歌,不时偷望马寡妇。
牛二蛋 (唱)蓝格铮铮的裤子白格生生的衫,
你把我的心儿给全扰乱。
听而不闻的马寡妇亦随之哼唱开。
马寡妇 (唱)我穿上新衣裳我好看,
与那些旁人何相干?
牛二蛋 (唱)不愿意就说你不愿意的话,
为什么把人给闪戏下?
马寡妇 (暗自发笑,突然停住手中的活儿)哎,二蛋,你狗入的有胆量再过这边来,甭那哇哇的穷骚情!
牛二蛋 嘿嘿,谁还敢过来,昨天你脱鞋打哩,今日个敢拿锄把掂哩。
马寡妇 熊包!三十几年的光棍打得活该。给你说,昨天我是想试伙一下你小子对我的那份情的深浅,没想到我的鞋还没脱到手,你个熊包就吓跑了。
牛二蛋 那,妈妈哎,你真把人给害苦了。好,我现在就过来帮你锄。(不由得唱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三跷两步地跑到马身边锄开)
马寡妇 (坐在界石上)等等!
牛二蛋 怎啦?
马寡妇 嘻嘻,昨天不是把你想干的事儿给中断了?今日个就给你再补上。
牛二蛋 补上?
马寡妇 哎,嘻嘻。
牛二蛋 那,那这情绪……
马寡妇 熊包,那甚哩,就照昨天的,从头来。
牛二蛋 对,从头来,昨天我不是就这样坐在你身边了吗?(坐下)接下来我就……
马寡妇 怎样?
牛二蛋 就,偷偷地拉过你这只手。
马寡妇 再下来呢?
牛二蛋 再下来我就这样趔着身子,将头慢慢向你伸过来……
马寡妇 那再下来呢?
牛二蛋 再下来你就不是伸手脱鞋了吗?
马寡妇 嘻嘻,那现在接着来。
牛二蛋将头慢慢向马伸去,马闭了双眼,一只手向下伸去,二蛋大惊,急向后退。
牛二蛋 啊?你又要脱鞋?
马寡妇 神经病,过来!
牛二蛋 你不是脱鞋?那……
马寡妇 接着来。
牛二蛋 对,接着来。(将头慢慢伸过去,一张未落在实处的脸上显出急促的呼吸)
马寡妇 (片刻后)就这?
牛二蛋 对,昨天我就准备这样。
马寡妇 唉,熊包,真是有贼心没贼胆!(说着主动将头靠向二蛋胸部,少顷)我问你,甚时候对我产生了这想法?
牛二蛋 我也说不准,反正从那时起我老想帮你多做点事儿。
马寡妇 是吗?
牛二蛋 你知道,去年春季你的责任田是谁给你耕的?
马寡妇 是你?
牛二蛋 今年天旱时你这杏苗子是谁给你浇的?
马寡妇 也是你?
牛二蛋 上月底,有人半夜强行进你的家门,你说是谁帮你撵走的?
马寡妇 噢——也是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牛二蛋 我……每天夜里都不止一次地要在你的院前走走。
马寡妇 为甚哩?
牛二蛋 不是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吗?我老担心你一个人住着出事。
马寡妇 你就常在暗中保护我?
牛二蛋 哎。
马寡妇 (激动地)你为我还做了些啥事呢?
牛二蛋 有几个晚上,你的窗户纸上不是开了几个小洞洞吗?
马寡妇 对,谁干的?
牛二蛋 是……是我。
马寡妇 啊?你为甚?
牛二蛋 不瞅瞅你,我睡不着觉呀。
马寡妇 二蛋!(激动地)我把你个坏熊,你为甚不早些给我说呢?(说着紧紧抱住二蛋)
牛二蛋 早先打光棍是因为穷,现在生活好了,我,我又开不了这个口嘛!这不,给你买了对金耳环,(从兜里掏出)揣在我身上半年了还给不了你么。
马寡妇 二蛋,你这样做是不是也想占我的便宜呢?
牛二蛋 妈呀,我哪有这个胆量。
马寡妇 那,你是个从没成过家的人,和我合适吗?
牛二蛋 哎哟,连做梦都在想你哩!
马寡妇 二蛋,那这耳环……
牛二蛋 只要你愿意,就给你戴上。
马寡妇 哎。
二蛋笨着手帮马寡妇戴耳环。
马寡妇 哟,慢点,你这手怎么老是在抖呢?
牛二蛋 哎呀,我也不知道这狗入的为甚。
马寡妇 二蛋,好看吗?
牛二蛋 好!嫂子呀,这千大几票子是没白花的!
马寡妇 哎,你叫我啥?按年龄你要叫我妹子哩!
牛二蛋 那行,我就叫你——马妹子!
马寡妇 哎!二蛋……叫你哥多咬口,还不如叫二蛋顺当。
牛二蛋 能行,怎顺当怎来。
马寡妇 二蛋,来,坐这儿。
牛二蛋 哎。(坐至马身旁)
马寡妇 二蛋,你现在真的发了?
牛二蛋 不发也不像以前那样穷了,你看咱陕北现在煤也出来了,气也出来了,老百姓都跟着沾光了;特别是那个“甘露工程”把咱祖祖辈辈的缺水问题解决了,咱把祖辈没种过的作物种上了。这不,你我这两亩银杏苗子赶明年就能叫三四万票子到咱手了!
马寡妇 哎哟,二蛋呀,我总把你当作是个没嘴的葫芦,没想到你说开了还真能行哩!
牛二蛋 嘿,这不是咱要能哩,是眼前摆的事叫咱能哩。以前咱人穷志短,只有人家给咱的,没有咱给人家的;现在咱这煤呀、气呀都是人家用得着的好东西。你没看这一条条运煤气的铁家伙,东边通了北京城,南边通了西安市,北边通了宁夏自治区,就连回民弟兄们也和咱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咱陕北呀,真是隔着窗子吹喇叭哩,名声在外了,咱这些陕北人也跟着风光得不能再风光了!
马寡妇 行了、行了。二蛋,打锣千锤,捉音一点,咱往实处掂,你说你什么时候娶我?
牛二蛋 我想过了,等把咱村这段运气管道的改道工程完了,咱就办事。
马寡妇 哟,为甚要等到那阵哩?
牛二蛋 一来这改道工程一开始咱得去尽点儿义务劳动;二来借上这个改道机会咱还能发点儿不大不小的财。
马寡妇 能发啥财哩?
牛二蛋 咋,你还不知道?这管道要从咱这种银杏苗的地上通过。
马寡妇 真的?
牛二蛋 已经画线定桩了。
马寡妇 妈哟,那这杏苗地又得日塌多少呀?
牛二蛋 妹子,这你别担心,人家给咱包产呢,说不准这锤子下来,咱俩结婚用的钱足足有余了。
马寡妇 人家能给咱多少钱呢?
牛二蛋 咋,这是个算账问题,一株银杏苗从挂果到老死的二十年里,少说能收入五千元吧,这一株五千元,毁坏这一片你想能有多少钱?
马寡妇 那你就准备这样给人家算钱哩?
牛二蛋 咋,不能么,这样算也显得咱有点儿太那个了,不过他不给咱六万七万,也得给咱四万五万,要不咱就不答应。咱不答应了,他的管子就改不了道,这是咱的权利。
马寡妇 哎哟,二蛋呀,我根本没看出你个狗入的心上的眼子比那筛眼子还稠。
牛二蛋 嘿嘿,哪里,这也算我为咱俩设立的那个“甘露工程”;你看,这三十几年里,我一直是……
马寡妇 受旱着呢!
牛二蛋 好妹子哩,旱得不能再旱了。
马寡妇 那就没把你给旱死!
牛二蛋 我这久旱的枯枝,再不给点甘露,也真的快要死掉啦,所以我就加快咱的“甘露工程”实施。
马寡妇 依我看,你这个算不上数的工程,还远没有人家那个大的工程好实现。
牛二蛋 为甚?
马寡妇 你也不想想,人家为咱施行的那个“甘露工程”,为咱搞的那些扶贫开发从没要过咱的钱,而你呢?就在人家刚刚用到咱的时候,你却为成全你的那个狗屁工程向人家要黑心钱,这像话吗?
牛二蛋 这……
马寡妇 这甚哩,这只能说明你这个人根本不能以心相报,所以我现在声明:你这工程我不参与,(取耳环)给,原物归主。(欲走)
牛二蛋 哎,妹子,你觉着哪达不合适还能商量哩。
马寡妇 对不起,内心的东西不改变,恐怕你这旱象还得蔓延发展。(疾步离去)
牛二蛋 哎妹子,妹子……(追马而去)
灯暗。
(2002年获中国曹禺小戏小品三等奖、陕西省小戏小品二等奖,发表于2002年《当代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