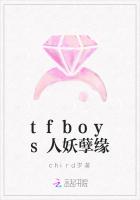《书志》:子日:“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日:“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又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世之作者,其鉴之哉!谈何容易,驷不及舌,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干载也。
《断限》:夫子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
《称谓》:孔子日:“唯名不可以假入。”又日:“名不正则言不顺”、“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复列之篇籍,传之不朽者邪。
《采撰》:子日:“吾犹及史之阚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补其遗逸者哉?
《采撰》:晋世杂书,谅非一族,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皇朝新撰《晋书》,多采以为书。
《叙事》: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
《曲笔》:肇有入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琉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顾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摸拟》:《左氏》与《论语》,有叙入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日”、“问日”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日:“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书事》:子日:“于予何诛?”于此数家见之矣。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书事》: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孔子日:“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谓矣。
《人物》:语日:“吾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察所不该,理无足咎。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核才》: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违遭不遇。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核才》: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
《序传》:夫自媒自街,士女之丑行。然则人莫我知,君子不耻。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又日:“吾每自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日:“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则圣达之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其情,或选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诸门人“各言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
《杂述》:然则茎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辨职》: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日:“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又语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观历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戏,而竟不废其职者,盖存夫爱礼,吝彼典刑者乎。
《疑古》: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故二传大行,擅名于世。又孔门之著录也,《论语》专述言辞,《家语》兼陈事业。而自古学徒相授,唯称《论语》而已。由斯而谈,并古人轻事重言之明效也。
《疑古》:案《论语》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又日:成事不说,(原注:事已成,不可复解说。)遂事不谏,(原注:事已遂,不可复谏止。)既往不咎。(原注:事已往,不可复追咎。)又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原注: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经四处,注皆全写先儒所释也。)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
《疑古》: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娶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
《疑吉》: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日:“尧、舜之入,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
《疑古》:子贡日:“桀纣之恶不至是,君子恶居下流。”
《疑古》:《论语》日:“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案《尚书廖》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诸侯,而辄行征伐,结怨王室,殊无愧畏。此则《春秋》荆蛮之灭诸姬,《论语》季氏之伐颛顼也。失天无二日,地唯一入,有殷犹存,而王号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吴、越僭号而陵天子也。然则戡黎灭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犹近者魏司马文王害权臣,鼬少帝,坐加九锡,行驾六马。及其殁也,而苟勖犹谓之人臣以终。盖姬之事殷,当比马之臣魏,必称周德之大者,不亦虚为其说乎?
《疑古》:《论语》日:“太伯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案《吕氏春秋》所载云云,斯则太王钟爱厥孙,将立其父。太伯年居长嫡,地实妨贤。向若强颜苟视,怀疑不去,大则类卫仅之诛,小则同楚建之逐,虽欲勿让,君亲其立诸?且太王之殂,太伯来赴,季历承考遗命,推让厥昆。太伯以形质已残,有辞获免。原夫毁兹玉体,从彼被发者,本以外绝嫌疑,内释猜忌,譬雄鸡自断其尾,用获免于人牺者焉。又案《春秋》,晋士芳见申生之将废也,日:为吴太伯,犹有令名。斯则太伯、申生,事如一体。直以出处有异,故成败不同。若夫人之论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转祸为福,斯则当矣。如云“可谓至德”者,无乃谬为其誉矣?
《惑经》: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恩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者欤?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
《惑经》: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申左》: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论语》子日:“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干,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申左》:《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日:昔卫蒯喷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日: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日: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择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将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
《杂说上》: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本书。(原注:谓《管子》也。)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辑勒,只觉烦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
《杂说下》: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
《杂说下》:子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杂说下》:“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已降,吾未之见也。
《杂说下》:子日:“齐景公有马干驷,死之日,入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
《暗惑》:又《史记·田敬仲世家》日: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日:“妪乎采芭,归乎田成子。”
难日:“夫人既从物故,然后加以易名。田常见存,而遽呼以谥,此之不实,明然可知。”又案《左氏传》,石碚日:“陈桓公方有宠于王。”《论语》,陈司败问孔子:“昭公知礼乎?”……诸如此说,其例皆同。
《暗惑》:盖语日:“君子可欺不可罔。”
案:《论语》通行本共二十篇,刘氏称引涉及十五篇,可谓广征博引。孔子思想影响知几者有多途,现拈出其突出几点而言之。其一日文与史之关系。《叙事》、《核才》二篇引“文胜质则史”(见《论语·雍也》)之语,迸而阐明“史之为务,必藉于文”,“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之观点,极有理论价值。史离不开文但与文又有区别,此论精当,颇有辩证统一性。其二日史之阙文。《采撰》篇据“吾犹及史之阙文”(见《论语·卫灵公》而知史文有阙,其来有尚竹,因此,刘氏于《书志》、《人物》诸篇反复声明孔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见《论语·为改》)、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一(见《论语·子路》)之遗训,号召史家要对史料之遗逸与残阙持谨慎态度。尊重历史文献之客观实际,乃良史基本工作态度。其三日正名。孔子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即正名。《称谓)篇可谓全以孔子正名思想为理论根据。史书能传名不朽,善恶褒贬,非同小可,故刘氏主张史官笔削,应慎之又慎。如《人物》篇云: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竹又《题目》篇之核心为“考名贵实”,与孔子思想亦不无关联。其四日不语怪力乱神。如《采撰》、《书事》诸篇均标明此论。刘氏反对史书记载神鬼怪物,《采撰》即据孔子语以驳晋之杂书及唐修《晋书》。刘氏特别轻视充满“诡说异辞”之子部小说家言。知几力诋《汉书五行志》,亦可从此寻出一二原因。若谓孔子之哲学为重人事之哲学,那么刘氏之史学可谓重人事之史学。
刘知几既广泛征引孔子之语以伸己说,又对孔子言论有所批评。如《序传》篇揭发孔子“扬露己才”,《疑古》篇驳难孔子夸大失实,均直言不讳,洵为王充《论衡·问孔》之遗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