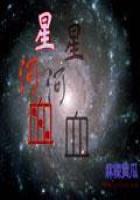《论赞》:(略,见《公羊传》同条。)
《叙事》: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原注……如《谷梁传》云:骊姬以鸩为酒,药脯以毒。献公田来,骊姬日:“世子已祀,故致福于君。”君将食,骊姬跪日:“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而地坟;以脯与犬,犬毙。骊姬下堂而啼呼日:“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乎为君!”……此则既书事迹,又载言语也。)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原注:《公》、《梁》、《礼》、《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鉴识):(路,见《公羊传》同条。)
《古今正史》:(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杂说上》:(略,见《公羊传》同条。)
(杂说上》:(略,见《公羊传》同条。)
《汉书五行志错误》:《志》云:庶征之恒风,刘向以《春秋》无其应。刘歆以为麓十六年,《左氏传》释六鹇退飞是也。案旧史称刘向学《谷梁》,歆学《左氏》。既袒习各异,而闻见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郑车偾济,风之为害,被于《尚书》、《春秋》。向则略而不言,歆则知而不传。盖学有不同,识无通鉴故也。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
《五行志杂驳):《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蚀之。董仲舒、刘向皆以为自此前后,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后为溴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君若缀旒,不得举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刘向以为是岁三月,大夫盟于溴粱,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无冰。班固以为天下异也。襄公时,天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君不能制,渐将日甚。(原注:《谷梁》云:“诸侯始失政,大夫执国权。”又日: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案春秋诸国,权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鸡泽之会、溴粱之盟,其臣岂有若向之所说者邪。然而《谷梁)谓大夫不臣,诸侯失政。讥其无礼自擅,在兹一举而已。非是如“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国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刘之徒,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厂为它说,多肆梦言。仍云“君若缀旒”,“臣将日甚”,何其妄也?
《五行志杂驳》:(略,见《公羊传》同条。)
案:《谷梁传》,《汉志》著录十一篇,题鲁人谷梁子所作。然其主名实无明文可考,见之汉唐载籍者有喜、嘉、赤、寞、傲诸名之说。大抵其书非作于一时,非成于一手。《谷粱》之体例近《公羊》,故历来(公》、《谷》并称为二传,同属今文学派,以与《左传》抗衡。若进而析之,《谷梁》之地位及影响实不及《公羊》与《左传》。皮锡瑞日:“《谷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谷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刘知几之于《谷梁》,一如《公羊》,完全取讥斥态度。笔者已于《公羊传》之案语有所评说,此不赘言。《公》、《谷》在晚清尝重振旗鼓,行时一阵。然近几十年似又遭冷落,迄今尚无二传之新注本同世,可谓遗憾。而时下流行之史料学书籍亦多不重视二传,如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仅列《左传),并日:“汉代立于学官的有所谓解释《春秋》义例的《公羊传》、《谷梁传》,与周代史事关涉不大,不必参考。”。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上)亦只提《左传》、《国语,》,而不及二传。如此编排,似失完备。要之,吕思勉先生所论最为可取:今日将《三传》作史读,《左氏》优于《公》、《谷》,自无待言;然亦有宜参考二传者,不得一笔抹杀,作十成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