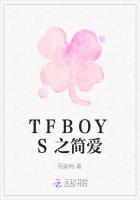我去阿尔芒家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
“您在发烧。”我对他说。
“没事,只是路上赶得太急,感到疲劳罢了。”
“您从玛格丽特姐姐家里回来吗?”
“是啊,谁告诉您的?”
“我已经知道了,您想办的事谈成了吗?”
“谈成了,但是,谁告诉您我出门了?谁告诉您我出门去干什么的?”
“公墓的园丁。”
“您看到那座坟墓了吗?”我装着没有听见,试着把话岔开,换一件别的事情谈谈。
“您出门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吧。”我对他说。
“整整三个星期。”
“您的旅程很长。”
“啊,我并不是一直在路上,我病了两个星期,否则我早就回来了。我一到那里就发起烧来,只好呆在房间里。”
“但您的病还没好就回来了。”
“要是我再在那里呆一个星期,我就会死在那里。”
“现在您已经回来了,应当养好身体;您的朋友们会来看您的。我会第一个来的,如果您允许的话。”
“两小时以后我就得起床。”
“您太冒失了!”
“我必须这样做。”
“您有什么事这样急着要办吗?”
“我必须去找警官。”
“您为什么不委托别人去办呢?您自己去会加重病情的。”“这是惟一能治好我的病的方法。我必须见到她。”
“等您完全康复以后再迁坟吧。”
“不!您放心,我身体会好的。再说它已成为我的一块心病,如果不尽快把这件事办成,我会发疯的。我对您起誓,只有在见到玛格丽特后我才能平静下来。
“我明白,”我对阿尔芒说,“我会尽力帮您的忙。您见到朱丽·迪普拉了吗?”
“见过。啊!我在第一次回来当天就见过她了。”
“她把玛格丽特托她为您保存的日记交给您了吗?”
“在这儿呢。”
阿尔芒从他的枕下抽出一个纸卷,又立即放了回去。
“我记熟了这些日记,”他对我说,“三个星期来我每天都要重读十遍。您也可以读读,不过要等些时候,待我心绪平静,并且能让您明白这忏悔揭示的心迹和爱情。眼下,我求您做件事。”
“什么事?”
“您有一辆车子停在下面吧?”
“是啊。”
“那么,能不能请您拿了我的护照到邮局去一次,问问有没有寄给我的留局待领的信件?等您去邮局回来以后,我们再一起去把明天迁葬的事通知警长。”
阿尔芒把护照交给我,我就到让雅克卢梭大街去了。那里有两封给杜瓦尔先生的信,我拿了回来。我回到他家里的时候,阿尔芒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门了。
“谢谢,”他接过信对我说,“是啊,”他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又接着说,“是啊,这是我父亲和我妹妹寄给我的。他们一定弄不懂我为什么没有回信。”
“我们走吧,”他对我说,“我明天再写回信。”
我们到了警长那儿,阿尔芒把玛格丽特姐姐的委托书交给了他。
警长收下委托书,写了一张给公墓看守人的通知书交给他。我对参加这样一次迁葬也很感兴趣,老实说,我一夜都没睡好。连我的脑子都是乱糟糟的,可想而知这一夜对阿尔芒来说是多么漫长啊!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我到了他家。他脸色苍白得吓人,但神态还算安详。
他对我笑了笑,伸过手来。
阿尔芒带上厚厚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父亲的。
半小时后,我们到了蒙马特墓地。
警官已经在等我们。
我们缓缓地朝着玛格丽特的墓走去。警官走在前面,阿尔芒和我跟在他身后。
我不时地感到我同伴的胳臂在痉挛地抖动,仿佛突然间他全身阵阵战栗。于是我看着他,他理解我的目光,冲着我微笑,但从走出家门之后,我们没有讲一句话。
快到那座坟墓时,阿尔芒停下来拭擦他那浸透汗珠的面孔。我利用片刻时间换了口气,因为我这颗心也好像被老虎钳夹住似的。
阿尔芒倚在一棵树上注视着,他的整个生命仿佛凝聚在他的眼睛里。
一个掘墓人拿起一把巨大的铁铲,一点一点地清除墓穴里的积土;后来,墓穴里只剩下盖在棺材上面的石块,他就一块一块地往外扔。棺材全部露出来以后,警长对掘墓的工人们说:“打开!”他们开始旋取棺材盖上的螺钉,这些螺钉受了潮都锈住了。好不容易才把棺材打开,一股恶臭迎面扑来。“啊,天哪!天哪!”阿尔芒喃喃地说,脸色雪白。
一块巨大的白色裹尸布裹着尸体,从外面可以看出尸体的轮廓。尸布的一端几乎完全烂掉了,露出死者的一只脚。“我们快一点吧。”警长说。
一个工人动手拆开尸布,他抓住一头把尸布掀开,一下子露出了玛格丽特的脸。
那模样看着实在吓人,说起来也使人不寒而栗。
阿尔芒死死地盯着这张脸,嘴里咬着他掏出来的手帕。
我感觉仿佛有一只铁环紧箍在头上,眼前一片模糊,耳朵里嗡嗡作响。我只能把带在身边以防万一的一只嗅盐瓶打开,拼命地嗅着。
正在我头晕目眩的时候,警长对杜瓦尔先生说:
“认出来了吗?”
“认出来了。”年轻人声音喑哑地回答说。
“那就把棺材盖上搬走。”警长说。
掘墓人把裹尸布重新盖在死者的脸上,合上棺材,一人抬头,向指定的地点走去。
阿尔芒一动不动。他的目光凝固在这个挖空的墓穴上,他的脸像刚才看见的尸体那样苍白……
我走到警官身边指着阿尔芒问道:
“这位先生还有没有必要在场?”
“不必了,”他对我,“我甚至建议您把他带回去,他好像病了。”“走吧。”我挽着阿尔芒的胳臂对他说。
“什么?”他看着我说,仿佛已经不认识我了。
“事情完了。”我又说,“您该走了,我的朋友。您脸色苍白,身体发冷,这样激动会把身体毁了。”
“您说得对,我们走吧。”他机械地回答,但一步未挪动。
于是我抓住他的胳臂,拖着他走。
我们在门口找到了车子。
他刚在车子里坐下,便抽搐得更厉害了,这是一次真正的全身痉挛。他怕我被吓着,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喃喃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哭。”我听到他在喘粗气,他的眼睛充血,眼泪却流不出来。
我让他闻了闻我刚才用过的嗅盐瓶。我们回到他家里时,看得出他还在哆嗦。
仆人帮助我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我把房里的炉火生得旺旺的,又连忙去找我的医生,把刚才的经过告诉了他。
他立刻就来了。
阿尔芒脸色绯红,神志昏迷,结结巴巴地说着一些胡话,这些话里只有玛格丽特的名字才听得清楚。
医生检查过病人以后,我问医生说:“怎么样?”“是这样,算他运气,他得的是脑膜炎,不是什么别的病。天主饶恕我,我还以为他疯了呢!幸而他肉体上的病将压倒他精神上的病。一个月以后,也许他两种病都能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