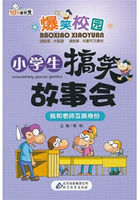由于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票房收入不高,因此我离开了好莱坞,告别了刺激的演员生活,又回到了佛洛斯特的“沼泽之城”,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水波不惊的时光。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常常考虑以后的事情,节省开支,寻找挣钱的途径。因为朋友们资助的款项只能保证我一个人的生活开支,假如我在莎莉文老师之前死了,等她老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想到这一点,我必须想方设法替莎莉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以保证她有一个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
基于这种考虑,我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直到1924年,我们为期4年的客串演出才结束。我们并不像专业演员那样连续不断地参加演出,起初,我们只是随剧团到纽约、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等地作巡回演出。而1921年至1922年这两年期间,我们主要在美国国内巡回演出。
我们在杂耍剧院参加演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议论纷纷,一时间飞短流长:“真是没有想到,海伦如此看重名利,简直不管不顾。”
有许多热心人还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虽说这一行有名利可图,但并不适合我。知道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何尝是为名利所引诱呢?我只是为莎莉文老师担忧而做出了这个决定,并且去实现而已。至于莎莉文老师,也是经我多次劝说,她才决定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目前剧院的工作与写作和演讲比起来要轻松得多,而且收入颇丰。我们巡回演出基本上不用在不同的地方来回奔波,而且停留在一个地方的时间也不短,至少有一个礼拜。不像我们巡回演讲那样,饱受奔波之苦。——我们匆匆联系演讲的地点,有时一天之内要接连不断地赶赴好几个地方,常常来不及休息就要上台演讲,这样下来确实吃不消。而我们现在不用全天都工作,演出是只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20分钟,合计起来也只有40分钟左右。另外,剧院为了保证我们的私人自由和正常生活,制定了规范而严格的管理制度,生活非常有规律,很少受到观众的打扰。不像以前演讲时,听众会争相前来握手,现在几乎没有这种情形发生。
从事这项工作后,我从内心里感到了愉快,而从未感到疲惫不堪。但是,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太适应这种生活,有些放不开,而且从一开始她就觉得浑身不自然。这也难怪,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那些表演的动物——比如猴子、大象和鹦赋等列在一起,也许是这个愿意使莎莉文老师不能坦然接受吧。但我一开始就能泰然处之,从来不认识这是一项卑贱而庸俗的工作,也没有觉得丢脸,正因为这样,我从工作中找到了真正的快乐。
我与剧院的人相处得很融洽,以前我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也结识过许多人,但从来没有产生现在这样强烈的兴趣。他们豪爽开朗、热诚而讲义气,这类举动我尤其欣赏。总的来说,自从来到杂耍剧院,我一直生活在快乐之中。这里的观众非常可爱、友好而热情,每次我开口说话时,他们都会很惊讶,并发出由衷的赞叹。莎莉文老师会告诉他们教育我的过程和方法,接下来我会作一番自我介绍,最后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疑惑一般有以下几点:
“你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分辨白昼和黑夜呢?”
“你打算结婚吗?你怎样安排未来的生活?”
“你的眼睛应该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吧,你认为世界存在鬼魂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吗?”
类似这样可笑的问题不一而足,五花八门!
我很在意观众们看我演出后的反馈意见,让我觉得欣慰和满意的是,观众非常坦诚和热情。只要我的回答有道理,他们就会心地表示同意;当我的演出幽默、滑稽,让他们开心时,他们就会拍手大笑,表露出自己的快乐,从不掩饰,我也乐意真诚地回答他们的各种问题,让他们尽量满意,那样我也会更加快乐。
提到观众们的反馈,我想起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演讲经历,那一次,演讲的会场安排在教会,来这里的听众有着不同的身份,怀着不同的心情,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表现得严肃而庄重,这样的情况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尽管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但我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演讲没有丝毫反应。我一个人高高地站在演讲台上,突然产生了一种自言自语、索然无味的错觉。还有一次,我接受邀请去电台演讲,我只觉得周围一片死寂,没有别人走动和鼓掌带来的震动,就连空气也无法感受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扑鼻的发胶香味也消失了,仿佛置身于一人的世界里。
基于这些原因,我愿意呆在剧院和我的观众笑成一团,最起码我能自然放松,不至于太拘束,也不会感到太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