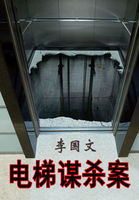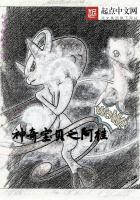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引起了浪女人虎子媳妇的好奇心。这个单干户秋收后的粮食,一半被征去交了公粮,一半留作自己食用。她对食物并无奢求,但对男人的需求几乎到了贪婪的地步。走在路上,每个见她的女人都朝她吐唾沫。对此,虎子媳妇毫不在乎。当她看到全村妇女都往工地上送水时,也学着她们的样子,每天都烧两大锅水,大摇大摆走向工地。对这个淫荡的女人的种种行径,外地民工一无所知。起初,他们善意地喊她大嫂,但日子一久,她那毫无掩饰的淫邪目光让每个喝过她开水的男人想入非非。众人聚在一起休息时开始开她的玩笑,问她男人在不在家。“是死是活还不知呢!”浪女人对虎子的出走未归毫无伤感,她自己提议为众人讲个笑话。这个提议让疲惫的民工立刻来了精神,更近地向她靠过来,边用不怀好意的目光看女人的羞处,边装出认真听讲的样子。虎子媳妇开始讲她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淫秽笑话。她说有这么个赶车的壮汉,一天晚上住进一个马车店。在店里卸车时,一眼见店老板有个闺女又俊又浪,两条辫子在腚后面摆也摆的。一时不自觉脱口而出:这么俊的女人,要能到俺手上,一夜保证能干她八遍。这话被店老板听个正着。店老板问他可真有那本事,赶车人毫不犹豫地点头称有。“那你就试试,”店老板说,“咱得打个赌,要能干八遍,我让你白睡;要是熊了,这车马就归俺。”壮汉当即满口答应……民工们被浪女人逗得哈哈大笑,忙问可是真干了八遍。浪女人说:“急啥,急啥,听俺讲啊。”又讲下去。她说谁知壮汉果真是个熊货,天亮前才干了四遍。“也不少啊。”一个将头剃得瓦亮的民工接口道,他已不怀好意地坐在了浪女人身边,时不时地假装搔头碰碰她的前胸。这更调动了女人的情绪,继续说下去:你说泄气不泄气?住了一晚上店,把大车大马输了个净光。他觉得倒霉透了。一个人摇摇摆摆地往回走,走着走着觉得干渴难耐,正看见一个女人在井边用罐子打水,他便上去讨水喝。那个女人把罐子递给他。你喝水就喝吧,可他抬头看一眼那女人。这一看不打紧,这女人也俊浪俊浪的,一时性起,裆内的东西支起来,手里的水罐掉在地上,你说他这个气呀!骂他那根东西道:让你硬,你不硬,大车大马输个净;让你软,你不软,大清早喝水砸个罐!
女人讲完,所有民工笑得前仰后合。光头民工却没笑,他乘人不注意附在浪女人耳边道:“那人熊俺不熊,一晚上准能干你八遍!”女人站起身,不屑地撇撇嘴,提起两把壶扭着屁股离去。
女人走后,光头男人开始神不守舍,当天晚上,他在同伴们睡下后,准确地寻找到了虎子家的院子里。女人正在等他。第二天再干活。硬挺挺的男人骨头像散了架。同窝棚的民工已猜个八九,一整天都在打他的哈哈。“女人真够浪,不信你们去试试。”光头一副甘拜下风的德性。自此,虎子家每晚都有人光顾。此事很快被蛤蟆湾子村人发觉,但没人觉得奇怪,连议论的闲心都没有。远离故土的男人干涸的心在同一个女人身上得到抚慰,不少人甚至庆幸这次远行。
远在百里外的蛤蟆湾子二百号劳力此时正奋战在自己的工地上。他们谁都想不到,一场灾难正一步步逼近。由于邻近海边,锨下去仅几米深便开始渗水,邓吉昌指挥劳力搭坝往外扬水。大家还是第一次到海边来,每天傍晚放工后,他们不知疲劳地一起涌到浅海里捕鱼捉蟹。鲜活的海货往往成为他们第二天上好的伙食。一段时间后,兆富却有了个新的发现,当他提着罩子灯在海滩上解手时,发现无数螃蟹向他聚拢来。“别往海里去捉了,海滩上就多的是。”他招呼着众人。没有海边生活经验的村人不知,海滩上的蟹是见不得亮光的,在灯光的照耀下,近处的蟹便会毫不犹豫地爬出窝穴,向明处聚拢。兆富的发现让众人欣喜若狂。此后,每到晚上,他们便纷纷提着罩子灯来捉蟹。这种鲜美的海物被一桶桶捉回工地。瘸哥逮起蟹来格外卖力,他的大呼小叫在潮湿的海风里传出很远。这一次,大队因其腿脚不便本不想让他来,可他请战的态度坚决,让人不容置疑,理由是可以为众人做饭。临行的前一天晚上,瞎嫂柔情万千,使瘸哥找到了他初婚的感觉。一直赶到了工地,他仍在甜甜地回忆自己的那个不眠之夜。然而,半月后的一天晚上,他们捕蟹的方法忽然不灵了。在亮灯静等两个小时后,没有一只蟹爬过来。大家骂骂咧咧往回走,都说今晚撞上鬼了。当众人各自回帐篷里睡觉时,邓吉昌却听到了水水的一声惊叫。这声音真切异常,仿佛水水就在身边。呼唤声里带着惊恐,使邓吉昌浑身打了个哆嗦,他茫然四顾,什么也没看到。天上一轮圆月被一个大大的风圈圈定,星星的闪烁似比平日暗了许多。躺在自己铺上的邓吉昌久久难以入睡,被水水的呼唤搅得心神不宁。就在他迷迷糊糊即将入睡时,一股狂风猛地袭来,将塑料帐篷刮得哗哗紧响。他一下钻出帐篷,却见进帐篷时的圆月已无影无踪,昏天黑地里狂风打着呼哨在肆虐。俄而,如霹雳和狂兽狂吼般的声音从海边传来,使他浑身打个哆嗦。多少年来,他曾无数次于海边野宿,却从未见过这个场面。在他的惊异中,怪兽狂叫很快变成海水的呼啸。此时,他记不清从哪里听来的关于“海吼”的说法一下闪入脑海——这海吼绝非海啸和上潮,那是来自海心的巨流,它以数十米的高度推向海滩,扑向内陆。这一奇想使他心惊肉跳,放开嗓喊着帐篷里的众人。而此时,大家已被那怪声全部惊醒,纷纷钻出了帐篷……
“爹——”半夜里水水的一声惊叫使红霞猛地惊醒,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使劲地推醒睡梦中的水水。水水揉着两眼,猛地抓住了红霞的两臂。她惊恐地向红霞述说自己的噩梦,说自己梦见一个怪兽正张着血盆大口扑向自己父亲。第二天一早,刘氏揉着乱跳的右眼心神不宁。水水已进了她的屋里,把自己的梦境又讲给奶奶听。水水仍未从惊恐中摆脱出来,眼里满是恐惧。刘氏慌慌地带水水去找瞎嫂圆梦。瞎嫂正坐在自家院子里,对祖孙二人的到来似乎早有准备。她对刘氏的问题置若罔闻,一双白嫩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衣角,如呆立的雕像。水水的噩梦很快传遍了整个蛤蟆湾子,这噩梦使每个人都心惊肉跳忐忑不安。一整天,全村的妇女都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里,烧火时火苗燃着裤角都浑然不觉;洗碗时瓷碗从手中滑落到地上摔得粉碎;切菜时菜刀再不得心应手,常常跳动起来轻划在手背上,使人看到一条血豆虫从手背上爬下……晚饭后谁也没想睡觉,她们搬一条板凳坐在自家门前,在秋风中瑟瑟发抖。
晚上九点钟,蛤蟆湾子出工的劳力推着二十三具尸体进了村。蛤蟆湾子在一片哭声中颤抖。壮汉兆喜的尸体平放在邓家院里,他独目圆睁大口微启,嘴里流着黏糊糊的东西。在秋兰的哭叫中,刘氏执意让兆富帮她将兆喜抬进屋里。“兆喜没事,”她声音颤抖着说着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话,他记起十年前虎气生生的大儿子出去打仗被人抬回家时的情形,那时兆喜浑身是伤,一只眼被纱布蒙住,已几乎没有了呼吸,但她硬是用母性的慈爱将他救活了。这一次,她用一双手使劲地揉搓着兆喜的四肢和身子,坚信作为母亲能给儿子两次生命,也一定能给第三次。一直到半夜,兆喜却再也没有醒来。刘氏仍然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一双枯黄而有力的手仍揉搓着儿子的脸颊,直到邓吉昌将她拉开。
邓吉昌拖着一双病腿最后一个进村,在他前面,石头推着支书郑好学的尸体。“我对不住乡亲们啊!”他痛心疾首。但村人已无人听他的话,在各自寻找着自己站着或躺着的亲人。常三家的老三风将瘸哥的尸体推至瞎嫂面前时,瞎嫂仍是早晨刘氏来找她时的姿势,她已一天一动未动了。此时,她才将抓住衣角的双手撒开,从上到下抚摸着男人冰冷的尸体。她让风从屋里拿来瘸哥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小心翼翼地亲手为男人剥下脏衣,一件件换上。黎明到来后,整个蛤蟆湾子村仍处于一片悲泣中,几户人家已扎起灵棚,几里外数百名外地民工全都加入了为死者安排后事的队伍里,连浪女人虎子媳妇一双淫邪的双目也变得满是哀怜,在众人的怒骂中,走走东家,串串西家。
蛤蟆湾子遇到了比饥荒更甚的另一次灾难,二十三个活蹦乱跳的青壮汉子在短短时间里永远失去了生命,大多数人根本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邓吉昌的大呼小叫中,他们没命地往海的逆向狂奔,在昏天黑地里,在身后海水的震耳咆哮中,每一个心头都感觉到了世界末日的恐惧。但他们奔跑的双腿远远比不上身后海水的飞追。当兆喜惊骇地回身一望时,见黑暗中,数十米高的巨浪已仅在几米远处。在绝望的惊叫中,数百条生命已被卷入了魔浪,他们的身子随着“海吼”的狂奔旋转,旋转……此时,兆喜对死亡的恐惧已全消,任由生命被怪兽掠夺,脑子里却出现了十年前自己用铁锨杀死那条会自接身体的蛇的痛快淋漓……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邓吉昌在众人的呼唤中睁开双目,眼前全是陌生人。一个汉子用双膝支撑着他的身子,粗大的手在抹着他脸上的泥污。几乎很短的一瞬,邓吉昌便恢复了全部记忆,他挣扎着站起身,已有七八具尸体被众人平放在一起,里面有自己的儿子兆喜。他们遇到了百年未遇的“海吼”!以至数十年后曾身临其境的人向后人讲起这段经历,几乎已无人相信,如听一个老人编来的传说。
蛤蟆湾子坟地里一下多了二十三座新坟。同时遇难的还有数百名外乡民工。他们的尸体就埋在离海滩不远的荒草丛中。
安葬完死者后的第三天,邓吉昌和返回村的民工不顾家人的劝阻,又推着车子再次踏上赶往自己工地的路。大家在邓吉昌的指挥下,在数百名外地民工的尸体掩埋处不远扎起帐篷,每天早晨赶十余里路去工地干活,直到太阳西落返回宿营地。晚上,他们三五成群坐着吸烟,看对面数百座坟墓中间闪烁着蓝绿相间的磷火,没有一个人感到恐惧。
两年后,一沟混浊的黄河水从蛤蟆湾子村前流过,村人在邓吉昌带领下在沟上架起一座草木桥。一支浩浩荡荡的马队从村边经过,数以千计的马匹在上百名军人赶撵下,嘶鸣着踏过荒原上新露的绿色。他们要去蛤蟆湾子八十里外建一处军马场。在走过新挖掘出的大沟时,小眼睛军官下令不让马群从桥上经过,涉水过沟,理由是老乡架座草木桥不容易,走一趟会把桥踩坏。邓吉昌对此十分感激,他执意要留马队在村子里过宿。小眼睛军官不肯,说今晚一定要到达目的地。“真是天然的好牧场啊!”军官放眼一望无际的荒原和稀疏的村落,兴奋异常。在涉水过沟时,他问邓吉昌这横贯荒原的大沟的名字。邓吉昌说:“没个正名儿,因有这草木桥,大家都叫它草桥沟。”目送马队离去,邓吉昌仰头见一群人字形大雁从蓝天徐徐飞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