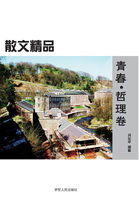先谈谈圈子椅和暖气。我准备说一下,这些事物只有在封建专制制度瓦解和旧式家庭和社会等级衰亡之后才可能出现。软椅子和沙发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人们可以懒洋洋地靠在上面。在一张精致的现代圈手椅上你也只好靠着。而这种姿势是既不足显示尊严又不能表达恭敬的。要打算显得神气或者训斥下属,我们总不能躺在软软的椅子里两脚蹬在壁炉架上,而必须坐直了,摆起架子才成。同样,要对一位夫人表示有礼貌或者对尊长表示敬意,我们也不能靠在那里,就是不站起来也得挺直腰板儿坐着。在过去的人类社会里有一套等级制度,每一个人都要对下显示尊严对上表示恭敬。在这种社会里,斜靠地坐着是绝对不可能的。路易十四在他的朝臣面前不可能这样做,而他的朝臣在他们的皇上面前也不可能这样做。只有亲临议会时,法兰西皇帝才能当众倚在御榻上。在这种场合,他要斜倚在一张名为“正大光明”的榻上,王公们坐着,大臣们站着,其他的小家伙都得跪着。讲舒服被宣布为帝王的特权。只有皇帝可以伸直了腿。我们也可以相信,这腿也会伸得非常有帝王气概。这样斜倚着,纯粹是礼仪上的需要,毫不丧失尊严。不错,在通常日子里皇帝是坐着的。但要庄严端坐;帝王的尊严是不能不保持的。(因为,说到底,帝王的尊严基本上也就是保持外表上尊严的问题。)同时朝臣们也要保持臣服的外表,或是站着,或者因为官高并是皇室近友,甚至在皇上面前也可坐在凳子上。朝廷上如此,贵族家庭里也如此。皇帝和朝臣的关系也就是绅士和他的家人,商人和他的学徒和仆人的关系。毫无例外,在上面的要显示出尊严,在下的要表达出服从以分清上下;这样谁还能不坐直了呢?就是在亲密的家庭关系里也是一样;父母像教皇和贵族一样以天赋的权力统治一切;儿女们就是臣民。我们的祖先对摩西十诚的第五诫是非常认真的——如何认真可从下一事例中看出。在伟大的加尔文以神权统治着日内瓦的时代,有一个孩子因为要打他的父母竟被当众袅首。孩子们在父母面前坐不正,也许不致有杀头之罪,但也会被认作大不敬,要遭到鞭答、不许吃饭或关禁闭。为了没有举手到帽沿向他致敬这一件小事,意大利贵族·岗扎加就把自己的独生子踢死;要是他的儿子竟当着他的面斜靠要椅子里会惹得他干出什么事来——这真叫人不敢想下去了。儿女不能在父母面前歪着靠着,同样,父母也不能在儿女面前歪着靠着,怕的是在有责任尊敬他们的儿女面前降低了自己的威严。因此,我们看到,在二三百年前的欧洲社会里从神圣罗马皇帝、法国国王到最穷的乞丐,从长须的尊长到儿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人前不端端正正坐着。古代的家具就反映出使用它们的那个等级社会的生活习惯。古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工匠有能力造出圈手椅和沙发使人坐上去和今天的产品一样舒服,但社会既是那样,他们也就不去造它了。实际上,直到十六世纪,连椅子也是少见的。在那以前,椅子是权威的象征,现在委员会的委员们可靠在椅子上,(会议员也坐得很舒服,但有权威的还是主席,或者叫做“坐在椅子上的人”(Chairman),权威还是产生于一张有象征性的椅子,中古时代只有大人物有椅子。他们旅行时要带着自己的椅子以便一刻也不离开他的外在的、看得见的权威标识。就是在今天,宝座还跟皇冠一样是皇权的象征。中古时期,就是能坐下时,平民们也只能坐在长短凳或长椅子上。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富裕的独立资产阶级的兴起,使用椅子才随便起来。买得起的就能坐椅子,但要端坐受罪;因为十六世纪的椅子还是定座式的,谁坐上去都不能不被迫采取令人受罪的有威严的姿势。直到十八世纪时,老的等级制度崩溃了,才有使人舒服的家具。但就是那时,也还不能在上面随意歪着靠着。可以在上面随意让人(先是男人,随后是妇女)歪着的圈手椅和沙发是直到民主制度巩固树立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是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起来,老规矩不存在了,妇女解放了,家庭里的限制消失了之后才出现了。
暖气和封建制度适当的房屋供暖是现代化的享受另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件事在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下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对当时的权势者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市民比贵族强。住房较小,所以他们还能暖和些。但是王公贵族和皇帝、红衣主教却要住在和自己身份相称的宏伟壮观的殿堂里。为了证明比别人要高贵些,他们不得不置身于超乎一般大小的环境里。他们在溜冰场大小的敞厅里接见客人;他们常同大群人簇拥着穿过象阿尔卑斯山隧道那样长而多风的走廊过道,又要在恰象尼罗河的瀑布给冻结成大理石那样的楼梯上走上走下。在那种时代里做一位大人物就要花许多时间安排豪华的芭蕾舞等等表演,而这就要有宽敞的地方才能容得下演员和观众。皇宫和贵族的府邸甚至普通的乡绅住宅都要那么高大,这就是原因。他们就好像是巨人一样要住在十丈长三丈高的屋子里,否则就不合身份了。真豪华,真宏伟,可又是多么冷嗖嗖的呀!在我们今天,靠自己的本事奋斗上来的大人物没有必要和那些天生的贵人比阔气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因之他们宁可少摆点架子而多图点舒服,住进了小一点但可以取暖的屋子。(过去的大人物在他们闲暇的时间也是这么办的;大多数古老的宫殿都有些小套房间,宫廷上的大场面结束后,宫殿的主人就退居到那里去。但是大场面往往时间拖得很长,过去的不幸的王公贵人也就不得不摆起排场在冰冷的殿堂里和冷风呼啸的走廊过道里度过许多时间。)有一次在芝加哥的郊区开车,有人领我去看一所房子,房主据说是全城最阔和最有势力的人。那所房子中等大小,有十五到二十间不大的旁间。这很使我诧异,并想起我本人在意大利住过的那些巨大的宫殿来(租金比在芝加哥存一辆福特汽车花的钱要少得多)。我还记得那大排大排的有通常舞厅大小的卧室,有火车站那么宽敞的客厅和宽得可以容两辆小卧车并排开过的楼梯。宏伟的宫殿,住在里面真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可是一想起二月间从阿平宁山那边刮过来的怕人的风,我又觉得芝加哥那位阔人不去学另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国家和他同样的人那样把财富花费在排场上是有道理的了。
洗澡和道德是皇权、贵族和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没落才使我们获得以上谈到的现代享受的两个组成部分;至于第三个组成部分,洗澡,我想至少部分地应当归功于基督教道德的衰败。在欧洲大陆上,而据我所知也在别处,现在都还有修道院学校,在那里面年轻的淑女受到一种教养使她们深信人体是一种不洁和猥亵的东西,不但看到别人的光身子就连看自己的也是犯罪的。就是在准许她们洗澡时(在每两星期的星期六),也要求穿上一件长达膝下的衫。甚至命令她们一种特殊的换衣服的技巧以保证她们越少看见自己的身体越好。幸好这类学校继承的是基督教的苦行传统,这个崇高传统由圣安东尼和那些第比斯的不洗脸、营养不足和禁欲的僧侣传下来几百年直到今天。因为这个传统削弱了,妇女才总算得到了经常洗澡这种享受。
早期基督徒对洗澡是全不热心的;但说句公道话,基督教的苦行传统倒也不一贯敌视洗澡这件事的本身。早期基督教的长老们觉得罗马人洗澡时男女混杂得惊人,这是自然的。但是他们里面较温和的是准备有限制地允许人们洗澡的,只是不要搞得不象样子。最后把罗马人的豪华澡塘搞掉的除了基督教的苦行主义之外,还有来自北方的野蛮人的破坏。实际上在笃信基督的时代洗澡也曾经复兴过一时。十字军从东方回来,带来了东方的蒸汽浴,似乎在欧洲颇为流行。为了某种不易了解的理由,洗澡的风气慢慢衰落了,十六世纪末期和十七世纪初期的男人或女人之不讲卫生和他们野蛮人的老祖宗不相上下。这种起伏可能与医学理论和宫廷的风气有关。
苦行主义的传统总是对妇女特别严格。在他们日记里,法国的龚古尔弟兄曾记下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上层社会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洗澡风行以来,妇女的姻静和道德水平是大为降低了。从此得到的必然推论显然是:“女孩儿家要少洗澡。”青年女士们喜欢享受洗澡乐趣的应当感谢伏尔泰的嘲讽和十九世纪科学家的唯惟物主义。假如没有这些人来打破修道院学校的传统,她们恐怕直到今天也还同她们的先辈一样地娴静,也同她们一样地不讲卫生。
舒适与医学然而,喜爱洗澡者最应感激的还是医学家。微生物传染的发现鼓励了讲卫生。今天我们是以印度教徒那样的宗教热情来对待洗澡的。洗澡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具有魔力的仪式,可是保护我们不受那些体现在喜爱肮脏的细菌上面的邪恶势力的毒害。我们甚至可以预言这种医学宗教还会进一步破坏基督教的苦行传统。自从发现阳光对人的好处以来,从医学上来说,穿过多的衣服就成为一种罪恶。不害羞已成为一种美德。很可能要不了多久,对我们来讲声望犹如原始人间的巫医那样的医生们就会要求我们一丝不挂的了。到了那时也就达到了使衣着越来越舒服的最后阶段。这个过程已进行了有一段时间,先在男子中间,然后在妇女中间,而其间决定性的因素就包括等级制度下的繁文缛节和基督教道德的衰微。在他那本记载了格莱斯东去世前不久访问牛津大学的描绘支持的小册子里,佛莱彻先生记下了那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对牛津学生的评论。看来他对学生们穿衣服既不整齐又不考究是很恼火的。他说他年轻时青年身人身上总要有值百把英镑的衣服和饰品,而每一个有自尊心的青年最少也要有一条他穿上后从不坐下的裤子,怕那一来会走了样子。而格莱斯东去访问牛津时,那里的学生还是穿浆得很硬的高领衬衫和戴圆顶礼帽的。我们不知道若他看见当前大学生们穿的敝领衬衫和花里胡哨的毛衣和松松垮垮的法兰绒裤子的话,他会作何感想。人们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不讲究维护尊严的外表了;这样随随便便是从未有过的。除去最庄严的场合,人们都可以不考虑级别地位而穿他觉得最舒服的衣服。
使妇女们不能舒适的障碍既有道德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妇女除了行动上不得不循规蹈矩之外,还要服从基督教苦行道德的传统。在男人早已放弃他们不舒服的礼服之后很长的时间内,妇女仍然为了庄重的缘故而忍受极大的不便。是世界大战把她们解放了出来。妇女一旦参加了战时工作,她们马上发现那种传统的端庄的衣着和工作效率很不相容。她们选择了效率。等到发现了少端庄一点的好处后,她们就再也不肯回到老样子去了,这大大改进了她们的健康也增加了她们个人的舒适。现代时兴的衣服之舒服是妇女从未享受过的。甚至古希腊人或许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不错,她们的内衣是再合理不过的;但是她们的外衣,和印度妇女的服装一样,只不过是拿一块布裹在身上再用别针别上就算完了。没有哪位妇女会感到要靠别针来保持自己的仪态是真正舒服的。
舒适本身就是目的因传统的人生哲学发生变化而成为可能的什么这件事,现在已经自行发展了。因为追求舒适已成为一种生理习惯,一种风气,一种本身就值得追求的理想。世界上使人舒服的事越多,人们也就越觉得它的可贵。尝过什么叫舒服的滋味的,不舒服对他就成为一种真正的折磨。崇拜舒适的风气是任何其它风气同样厉害的。此外,和提供使人舒服的条件紧密结合的有巨大的物质利益。好舒服的习惯一减退,制造家具的、暖气的设备和管道设备的商家都吃不消。利用了现代广告术,他们有法子迫使它不但存在而且发展。
在简短地追溯了现代享受精神上的来源之后,我还得就它的影响说两句话。我们要得到什么总不免要付出些代价。因之要舒服就要以失去别的同样有价值甚至是更为有价值的东西来作为代价。当前一位有钱的人盖房子般总是首先考虑他未来的住所是否舒服。他要花一大笔钱。因为舒适的代价是很高的;在美国,人们常说水暖俱全,房子出让。在洗澡间、暖气设备和带软垫的家具等等方面,花了这笔钱,他就觉得他的房子是十全十美的。若在以前的时代,象他这样的人却首先会考虑他的房子是否华丽,是否给人以深刻印象——换句话说,就是先考虑美观再考虑舒服。我们同代人花在浴室和暖气上的钱在过去就会花在大理石楼梯,宏伟的外表,壁画,一套套金碧辉煌的房间和绘画雕像上。十六世纪的教皇们的居住条件之不舒服在一位现代银行家看来会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他们有拉斐尔的壁画,他们拥有西斯汀教堂,还有镶有古代雕塑的长廊。难道因为梵蒂岗没有浴室,暖气和软椅子,我们就应当觉得教皇们很可怜了吗?我有点觉得我们当前要求舒服的热情是有点过分了。虽然我个人也好舒服;但我曾住过差不多不具有英国人认为不可缺少的任何现代设备的房子而感到很快乐。东方人,甚至于南欧人是不大知道什么叫舒服的,他们的生活和我们祖先在几世纪前的生活差不多,可是虽然缺少我们那一套复杂而价值高昂的软绵绵的奢侈品,他们似乎生活得也很好。我是个守旧派,仍然相信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东西,我看不出不能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物质进步有什么道理。我喜欢能节省劳力的装置,因为它们可以使人们省下时间去从事脑力活动。(但是这是因为喜欢脑力活动;有许多人可不喜欢这样,他们喜爱节省脑力的装置就和喜欢自动洗碟机和缝纫机一样。)我喜欢迅速而方便的交通。因为扩大人们可以活动的世界的范围就会扩大他们心胸。同样我也觉得寻求舒适是正当的,因为那样就可以提高精神生活。不舒适会阻挠思想的活动:身上又冷又酸痛要用脑子也是困难的。舒适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是当前的看来却把它当作一种目的,一种绝对好的东西了。也许有一天大地会被变成一张巨大的软垫床,人的躯体在上面打盹,而人的心灵被压在下面,象苔丝蒂梦娜那样地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