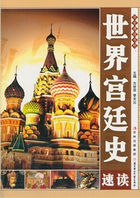又一场噩梦来临了。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喝过茶以后,外祖父和我坐下来念诗,外祖母正在洗盘子和碗,雅科夫舅舅闯了进来。
他一头的乱发和平常倒是没什么两样儿,可是脸色不大对头。他既不问安,也不看谁一眼,而是把帽子一扔,挥着两手嚷起来:“爸爸,米哈伊尔疯了!”
“他在我那儿吃的饭,可能是多喝了两盅儿,又拍桌子又砸碗,玻璃也给砸碎了,他没完没了地挑衅我和格里高里!现在他已经往这儿来了,说是要杀了您!您可要小心啊!”
听罢他的话,外祖父用手把身子慢慢地支起来,眼睛几乎瞪了出来:
“听见了没有,老太婆?”他吼着,“好啊,杀他爹来了,亲生儿子呀!”
他耸着肩膀在屋子里来回走着,突然,他一伸手把门关上了,带上了沉重的门钩,转身冲着雅科夫,说:
“你是不是要把瓦里娅的嫁妆拿到手才甘心?是不是?拿去吧!”
他在食指和中指间露出大拇指,伸到雅科夫的鼻子尖儿底下——这是轻蔑的表示!
雅科夫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来:
“爸爸,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关不关你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什么东西!”
外祖母什么也不说,她在忙着把茶杯往柜子里收。
“我,我是来保护你的……”
“好啊,保护我!好极了,谢谢你,好儿子!”
“老太婆,快给这只狐狸一件武器,雅科夫·华西里耶维奇,你哥哥一冲进来,你对准他的脑袋打他!”
舅舅躲到角落里去了。
“既然不相信我,我就……”
“相信你?”
外祖父跺着脚狂吼:
“告诉你,不管什么鸡、猫狗我都相信,可是你,我还要等等看!”
“我知道,是你灌醉了他,是你让他这么干的!”
“很好,你可以动手,打他或打我都行!”
外祖母悄悄对我说:
“快,跑到上面的小窗户那儿去,你舅舅米哈伊尔一露面,就赶快下来告诉我们!”
受此重任,我感到十分骄傲。
我马上跑上楼去,一丝不苟地注视着街道。
街道上,鹅卵石像一个个肿瘤,近处的“肿瘤”大一些,越远越小,一直延伸到了山谷那一边的奥斯特罗日那雅广场,广场旁边有一座监狱。
那儿还有一个叫久可夫的臭水坑。那就是外祖母讲过的,有一年冬天舅舅们曾经把我父亲扔进去的那个水坑。
向近处瞧瞧,前面是一条小巷,巷子尽头是低矮的三圣教堂。
街上的行人不多,蟑螂般地挪动着。
是他,米哈伊尔舅舅!
他东张西望地出现在巷子口,帽子盖住了他的耳朵和大半个脸。
看他那阵势,杀气腾腾的!
我飞快地跑下楼去,猛敲外祖父的门。
“谁?”
“我!”
“干什么?”
“他进酒馆了。”
“知道了。你去吧!”
“我在那儿害怕……”
“行啦,待会儿吧!”
我只好又上楼去,趴在窗户上。
天黑了下来,各家各户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不知道谁在弹琴,传出一阵阵悠扬而又忧郁的音乐来。
酒馆里的人们在唱歌,门一开,疲倦而又沙哑的歌声就传到了大街上。
那是独眼乞丐尼吉图什加在唱,这个大胡子老头儿的右眼是红色的,左眼则永远也睁不开。
门一关,他的歌声也就像被砍断了似的,戛然而止。
外祖母很羡慕这个独眼儿乞丐,听着他唱歌,她叹息道:
“会唱歌,真幸福啊!”
有的时候,她向坐在台阶上唱歌的老乞丐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说:“我问你,在梁赞也有圣母吗?”
乞丐声音很低地回答:“哪个省都有,到处都有。”
……昏暗的大街让我有一种沉重的疲惫感,我希望这时候有个人在我身边,最好是外祖母,外祖父也行!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我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外祖父和舅舅们都不喜欢他,而外祖母、格里高里和叶夫根尼娅谈起他来又那么怀念他呢?
我的母亲又去哪儿了呢?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母亲,甚至把她当成了外祖母所讲的童话中的主人公。
母亲离家出走了,这就更使我觉得她有传奇色彩了,我觉着她现在已经成了绿林好汉,住在路旁的森林里,杀富济贫……好像是一场梦!
下面的吼叫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把我惊醒了。
我赶紧往窗下看,外祖父、雅科夫和酒馆的伙计麦瑞员正把米哈伊尔往外拉。
米哈伊尔抓住门框,硬是不走。人们打他、踢他、砸他,最后把他扔到了街道上。
酒馆的门“哗啦”一声锁上了,压皱了的帽子被隔着墙扔了出来。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米哈伊尔舅舅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慢慢地爬了起来。
他抓起一个鹅卵石,猛地向酒馆的大门砸去,一声沉闷的响声以后,街道又恢复了沉静。
外祖母坐在门槛上,弯着腰,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抚摸着她的脸。
她好像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嘟哝着:
“上帝啊,给我的孩子们一点智慧吧!”
“上帝啊,饶恕我们吧……”
外祖父在这所宅子里住了总共也就是一年时间,不过,我们却名声大噪,每周都会有一群孩子跑到门口来,欢呼着:“华西里家又打架了!”
天一黑,米哈伊尔舅舅就会来到宅子附近,等待时机下手,大家无不提心吊胆。
他有时候会找几个帮凶,不是醉鬼就是小流氓。
他们拔掉了花园里的花草,捣毁了浴室,把蒸汽浴的架子、长凳子、水锅全都砸了,连门窗也没放过,都砸烂了。
外祖父站在窗子前,脸色阴沉地看着人家破坏他的财产。
外祖母则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不停地叫着:
“米希加,米希加,干什么啊?”
可回答她的却是不堪入耳的俄罗斯式的咒骂。
在这种时候,我很难追得上外祖母,可离开她我又感到不安,只好来到楼下外祖父的房间。
他却嘶哑着嗓子,冲着我大喊:“滚开,混蛋!”
我飞也似的逃回顶楼,从窗口向外盯着外祖母。
我很怕她让人给杀了!
我喊她,让她回来,她不肯。
这一次,米哈伊尔拿着一根大木棒子来打我们的门。
门里面,外祖父、两个房客和酒馆的老板娘,各执武器,等着他冲进来。
外祖母在后面哀求着:“让我出去见见他,跟他谈谈……”
外祖父前腿屈,后腿绷,像个猎人似的守在门口,当外祖母去哀求他时,他无声地用胳膊肘向后推她。
舅舅马上就要攻进门里来了。
外祖父突然说:“别打脑袋,打胳膊和腿……”
门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小窗户,舅舅已经把窗户上的玻璃打碎了。
外祖母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伸出一只胳膊,向外面摆着手,大叫:
“米希加,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走吧!他们要把你打残啊,快跑!”
舅舅在外面,照着她的胳膊就是一棍子,外祖母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米希加,快跑……”
“老太婆,怎么啦?”外祖父大叫一声。
门“哗”地一下开了,舅舅冲进来,几个人一齐动手,他一下子就又被扔了出去。
酒馆主人的妻子把外祖母搀回到外祖父的屋子里,外祖父在后面跟着。
“伤到骨头没有?”
“肯定是折了!”
“唉,你说,拿他怎么办啊?”外祖母闭着眼睛说。
“好啦!已经把他捆起来了!”
外祖母开始痛苦地呻吟着。
“忍一忍吧,我已经叫人去找正骨婆了!老太婆,他们这是要我们现在就死啊!”
“把财产都给他们吧!”
“那瓦里娅呢?”
他们谈了很久。
外祖母的声音越来越低沉无力,而外祖父却始终在大吵大闹。
不一会儿,来了个小老太婆。她的大嘴巴像鱼似的张着,好像没有眼睛,她用拐杖探着路,一步一挪地往前挪着。
我以为她来了就说明外祖母的死期已到,“刷”地一下跳到那个老太婆跟前大吼:“滚出去!”
外祖父粗暴地把我拎起来,上了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