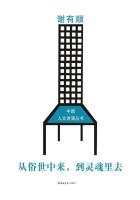等他看见了马颈上的那串铜铃,他的眼睛就早已昏盲了,已经分辨不出那坐在马背上的就是他少年时的同伴。
冯山——10年前他还算是老猎人。可是现在他只坐在马房里细心地剥着山兔的皮毛……鹿和狍子是近年来不常有的兽类,所以只有这山兔每天不断地翻转在他的手里。他常常把刀子放下,向着身边的剥着的山兔说:
“这样的射法,还能算个打猎的!这正是肉厚的地方就是一枪……这叫打猎?打什么猎呢!这叫开后堵……照着屁股就是一枪……”
“会打山兔的是打腿……杨老三,那真是……真是独手……连点血都不染……这可倒好……打个牢实,跑不了……”他一说到杨老三,就不立刻接下去。
“我也是差一点呢!怎样好的打手也怕犯事。杨老三去当胡子那年,我才23岁,真是差一芝麻粒,若不是五东家,我也到不了今天。三翻四覆地想要去……五东家劝我:还是就这样干吧!吃劳金,别看捞钱少。年轻轻的……当胡子是逃不了那最后的一条路。若不是五东家就可真干了,年轻的那一伙人,到现在怕是只有五东家和我了。那时候,他开烧锅……见一见,30多年没有见面。老弟兄……从小就在一块……”他越说越没有力量。手下剥着的山兔皮,用小刀在肚子上划开了,他开始撕着:“这他妈的还算回事!去吧!没有这好的心肠剥你们了……”拉着凳子,他坐到门外去抽烟。
飞着清雪的黄昏,什么也看不见,他一只手摸着自己的长统毡靴,另一只手举着他的烟袋。
从他身边经过的拉柴的老头向他说:“老冯,你在喝西北风吗?”
帮助厨夫烧火的冻破了脚的孩子向他说:“冯二爷,这冷的天,你摸你的胡子都上霜啦。”
冯山的肩头很宽,个子很高,他站起来几乎是触到了房檐。
在马房里他仍然是坐在原来的地方。他的左边有一条板凳。摆着已经剥好了的山兔;右边靠墙的钉子上挂着一排一排的毛皮。这次他再动手工作就什么也不讲了,一直到天黑,一直到夜里他困在炕上。假若有人问他:“冯二爷,你喝酒吗?”这时候,他也是把头摇摇,连一个“不”字也不想再说。并且在他摇头的时候,看得出他的牙齿在嘴里边一定咬得很紧。
在鸡鸣以前,那些猎犬被人们挂了颈铃,哐啷啷地走上了旷野。那铃子的声音好像隔着村子,隔着树林,隔着山坡那样遥远了去。
冯山捋着胡子,使头和枕头离开一点,他听听:
“半里路以外……”他点燃了烟袋,那铃声还没有完全消失。
“嗯……许家村过去啦!嗯……也许停在白河口上,嗯!嗯……白河……”他感到了颤索,于是把两臂缩进被子里边。烟袋就自由地横在枕头旁边。冒着烟,发着小红的火光。为着多日不洗刷的烟管,咝咝的,像是鸣唱似的叫着。在他用力吸着的时候,烟管就好像在房脊上的鸽子在睡觉似的……咕……咕……咕……假若在人们准备着出发的时候他醒来。他就说:“慢慢的,不要忘记了干粮,人还多少能挨住一会,狗可不行……一饿它就随时要吃,不管野鸡,不管兔子。也说不定,人若肚子空了,那就更糟,走几步,就满身是汗,再走几步那就不行了……怕是遇到了狼也逃不脱啦……”
假若他醒,只看到被人们换下来的毡靴,连铃子也听不到的时候,他就越感到孤独,好像被人们遗弃了似的。
今夜,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听到一点铃声,但是孤独的感觉却无缘故的被响亮的旷野上的铃子所唤起……在冯山的心上经过的是:远方、山、河……树林……枪声……他想到了杨老三,想到了年轻时的那一群伙伴:
“就只剩五东家了……见一见……”
他换了一袋烟的时间,铃声完全断绝下去。
“嗯!说不定过了白河啦……”因为他想不出昏沉的旷野上猎犬们跑着的踪迹。
“40来年没再见到,怕是不认识了……”他无意识地又捋了一下胡子,摸摸鼻头和眼睛。
烟管伴着他那遥远的幻想,嘶嘶的鸣叫时时要断落下来。于是他下唇和绵绒一般白胡子也就紧靠住了被边。
三月里的早晨,冯山一推开马房的门扇,就撞掉了几颗挂在檐头的冰溜。
他看一看猎犬们完全没有上锁,任意跑在前面的平原上,孩子们也咆哮在平原上。
他拖着毡靴向平原奔去。他想在那里问问孩子们,五东家要来是不是真事?马倌这野孩子是不是扯谎?
白河在前边横着了。他在河面上几次都是要跪了下去。那些冰排,那些发着响的,灰色的,亮晶晶的被他踏碎了的一块一块的冰块,使他疑心到:“不会被这河葬埋了吧?”
他跑到平原,随意抓到一个结着辫子的孩子,他们在融解掉白雪的冰地上丢着铜钱。
“小五子是要来吗?多少时候来?马倌不扯谎?”小五子是五东家年轻的时候留给他的称呼。
“干什么呀?冯二爷……你给人家踏破了界线!”小姑娘推开了他,用一只脚跳着去取她的铜钱。
“回家去问问你娘,五东家要来吗?多少时候来?你爹是赶车的,他是来回跑北荒的,他准知道。”
他从平原上回来的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路上总是向北方看去,那一层一层的小山岭,山后面被云彩所弥漫着,山后面的远方,他是想看也看不到的,因为有山隔着。就是没有山,他的眼睛也不能看得那么远了。于是他想着通到北荒去的大道,多年了……几十年……从和小五子分开,就没再到北荒去。那道路……嗯……恐怕也改变啦……手里拿着四耳帽子,膝盖向前一弓一弓地过了白河,河冰在下面格吱的呻叫。
他自己说:“雁要来了,白河也要开了。”
大风的下午,冯山看着那黄澄澄的天色。
马倌联着几匹马在檐下遇到了他:
“你还不信吗?你到院里去问问,五东家明天晌午不到,晚饭的时候一定到……”在马身上他高抬着右手,恰巧大门洞里走进去一匹骑马,又加上马倌那摆摆的袖子,冯山感到有什么在心上爆裂了一阵。
“扯谎的小东西,你不骗我?你这小鬼头,你的话,我总是信一半,疑一半……”冯山向大门洞的方向走去,已经走了1丈路他还说:“你这小子扯谎的毛头……五东家,他就能来啦!也是60岁的人了……出门不容易……”他回头去看看马倌坐在马背上连头也不回地跑去了。
冯山也跑了起来:“可是真的?明天就来!”他越跑,大风就好像潮水似的越阻止着他的膝盖。
第一个,他问的少东家,少东家说:“是,来的。”
他又去问倒脏水的老头,他也说:“是。”
可是他总有点不相信:“这是和我开玩笑的圈套吧?”于是他又去问赶马爬犁的马夫:“李山东,我说……北荒的五东家明天来?可是真的?你听见老太太也是说吗?”
“俺山东不知道这个。”他用宽大的扫帚,扫着爬犁上的草末绞着风,扑上了人脸。
冯山想:“这爬犁也许就是进城的吧?”但是他离了他,他想去问问井口正在饮马的闹嚷嚷的一群人。他向马群里去的时候,他听到冯厨子在什么地方招呼他:“冯二爷,冯二爷……你的老老朋友明明天天就来到啦!”
他反过身来,从马群撞出来,他看到马群也好像有几百匹似的在阻拦着他。
“这是真的了!冯厨子,那么报信的已经来啦!”
“来啦!在在,在大上房里吃吃饭!”
冯山在厨房的门口打着转,烟袋插在烟口袋里去,他要给冯厨子吃一袋烟。冯厨子的络腮胡子在他看来也比平日更庄严了些。
“这真是正经人,不瞎开玩笑……”
他点燃一根火柴,又燃了一根火柴。
在他们旁边的窗子空哐地摔落下来。这时候他们走进厨房去,坐在那靠墙壁的小凳上。他正要打听冯厨子关于五东家今夜是停在河西还是河东?他听到上房门口有人为着那报信的人而唤着:“冯厨子,来热一热酒!”
冯山他总想站到一群孩子的前面,右手齐到眉头的地方,向远方照着。虽然他是颤抖着胡子,但那看,却和孩子们的一样。
中午的时候,连东家的太太们也都来到了高岗,高岗下面就临着大路。只要车子或是马匹一转过那个山腰,用不了半里路,就可以跑到人们的脚下。人们都望着那山腰发白的道路。冯山也望着山腰也望着太阳,眼睛终于有些花了起来,他一抬头好像那高处的太阳就变成了无数个。眼睛起了金花,好像那山腰的大道也再看不见了。太阳快要靠近了山边的时候,就更红了起来,并且也大了,好像大盆一样停在山头上。他一看那山腰,他就看到了那大红的太阳,连山腰也不能再看了。于是低下头去,扯着腰间的蓝布腰带的一端揩着眼睛。
孩子们说:“冯二爷哭啦!冯二爷哭啦……”
他连忙把腰带放下去,为的是给孩子们看看:“哪里哭……把眼睛看花啦……”
山腰上出现了两辆车子和一匹骑马。
“来啦!来啦!……骑黑马……”
“正正是,去接的不就是两辆车子吗?”
“是……是……”
孩子们,有的下了高岗顺着大道跑去了。冯山的白胡子像是混杂了金丝似的闪光,他扶了孩子们的肩头,好像要把自己来抻高一点:“来到什么地方了呢?来到——”有人说:“过了太平沟的桥了!”有人说:“不对……那不是有排小树吗?树后面不就是井家岗吗?井家岗是在桥这边。”
“井家岗也不过就是两袋烟的工夫。”
看得见骑黑马的人是戴着土黄色的风帽,并且骑马渐渐离开车子而走在前边,并且那马串铃的声响也听得到了。
冯山的两只手都一齐地遮上了眉头,等他看见了马颈上的那串铜铃,他的眼睛就早已昏盲了,已经分辨不出那坐在马背上的就是他少年时的同伴。
他走了一步,他再走了一步,已经走下了高岗。他过去,他扒住了那马的辔头,他说:“老五……”他就再什么也不说了。
太阳在西边,在山顶上的,只划着半个盆边的形状,扯扯拖拖的,冯山伴着一些孩子们和五东家走进了上房。
在吃酒的时候他和五东家是对面坐着,他们说着杨老三是哪年死的,单明德是哪年死的……还有张国光……这一些都是他们年轻时的同伴。酒喝得多了一些的时候,冯山想要告诉他,某年某年他还勾搭了一个寡妇。但他看看周围站着的东家的太太们或姑娘们,他又感觉得这是不方便说了。
五东家走了的那天夜晚,他好像只记住了那红色的鞍,那土黄色的风帽。他送他过了太平沟的时候,他才看到站在桥上的都是五东家的家族……他后悔自己就没有一个家族。
马房里的特有的气味,一到春天就渐渐地恢复起来。那夜又是刮着狂风的夜,所有的近处的旷野都在发着啸……他又像被人们遗忘了,又好像年轻的时候出去打猎在旷野上迷失了。
他好像听到送马匹的人不知在什么地方喊着:“啊喔呼……长冬来在白河口……啊噢……长冬来在白河口……”
马倌喂马的时候,他喊着马倌:“给老冯来烫两盅酒。”
等他端起酒杯来,他又不想喝了,从那深陷下去的眼窠里,却安详地溢出两条寂寞的泪流。
5月6日
(署名萧红刊于1936年5月15日《作家》第1卷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