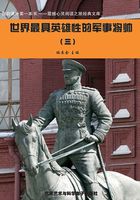毕加索在“洗衣船大楼”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是由于一次“粉红色的奇遇”。这次奇遇的主角就是一个叫费尔南多·奥莉维亚的女人,她是“洗衣船”中的另一个住客,是一个被神志不清的雕刻家丈夫遗弃的法国女人。
她常常看到毕加索跟马诺洛在一起谈笑,在小庭院的树下和西班牙朋友聊天,有时还和当地的小孩儿在灰里面画小鸡、兔子。她觉得奇怪,不知毕加索还有什么时间来工作,后来才发现那是在夜里,油灯或烛光的照明之下。
一天午后,毕加索被暴风雨浇回到“洗衣船”。当他正要转身回画室时,昏暗的楼道里,又冲进一位避雨的姑娘,她正是费尔南多·奥莉维亚。她虽然浑身湿透,但那天使般美丽的光彩并没有被浇灭。一股健康活泼的青春气息,从她湿淋淋的身上徐徐地散发出来,尤其是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正闪烁着迷人的神采。毕加索禁不住满怀爱意地注视着眼前的姑娘。
他热情地邀请姑娘到自己的画室去看看。姑娘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一走进画室,便看到堆放在墙脚的那些巨大的蓝色画幅,还有满地的烟蒂和一些开着瓶盖的颜料。
费尔南多对画室看得多了,却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不只是因为它的杂乱,更是因为里面的一大堆画。它们全都是蓝色的。她虽然觉得有些不健康,却还是很喜欢。
画室里还有一幅蚀刻。刻的是一对羸弱的夫妻坐在桌子前,桌子上放着一个空杯子、一个空盘子、一个酒瓶和一块面包,那个饥饿的男人的手臂围着妻子的肩膀,另一只手握着她的手臂,他的脸却转向旁边。这一幅《淡薄的一餐》是后来极为著名的蚀刻。
此后,费尔南多满怀着好奇和希望,走进了毕加索的生活。她为他打扫居室,料理生活,抚慰他那种时而沮丧时而激昂的情绪。
毕加索和费尔南多的陋室位于洗衣船大楼的顶层,里面有一个放颜料的木柜,一张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普通小圆桌,一张当床睡的长沙发,一个画架。原来的画室被分隔开,形成一个密室,放着一件类似床的东西,这里就是他们的“卧室”。
这时,毕加索背井离乡,再加上经济上的拮据,使他的心情十分沮丧。费尔南多的到来,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虚、亲情的空虚、钱财的空虚和社会地位的空虚。
毕加索在家里,最需要的还是费尔南多女性的特长。如果毕加索不拿起画笔,那他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他好吃、好玩、好恶作剧,好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费尔南多是个出名的懒妇人,但毕加索却能让她勤快起来。她能在一只烧石蜡的小炉子上做出各式色香味俱全的饭菜。她还很会计算,每天花钱不超过两法郎,就能使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吃饱喝好。
她还会利用妇人的小聪明,拖还欠款。她约店家派人把食品送上门时,她就朝门口喊道:“喂,把东西放在门口,我现在还不能去开门,我还没穿衣服呢!”店员不离开,这衣服就永远不会穿上。这一着还挺灵,往往能够赊几天的账。
费尔南多最大的优点,是她能接受毕加索的贫穷和他那些穷朋友的吵闹。费尔南多没有鞋子穿,很长时间走不出画室,只好用大批旧书来消磨时光。
在冬天的时候,他们没有钱买煤炭,就只能钻进被窝里取暖。有个邻居是经营燃料的,当他听说了这种情况,免费送来一箱煤炭,他被费尔南多的“一双眼睛迷住了”。
毕加索被天生丽质与开朗乐观的费尔南多改变了,他深藏在骨子里的诗人气质和顽童秉性在费尔南多的庇护下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她却拒绝了毕加索的求婚,她碍于自己坎坷的经历,也了解毕加索多变的性格,她宁愿和他这样宁静的、浪漫的、不受什么约束地过下去。因为,她知道毕加索是无法约束的。
毕加索很喜欢费尔南多,喜欢她的音容笑貌、她的穿着打扮,喜欢她潇洒风雅地戴着松软帽的样子。只要他手头有点儿钱了,他就马上买来一瓶香水送给费尔南多。他知道费尔南多最喜欢的礼物就是香水。
费尔南多的出现,给毕加索的精神和生活增添了无穷的快乐,费尔南多健康乐观的态度影响了悲观抑郁的毕加索。此时,毕加索的心情,变得轻快、深沉,已含有深深爱意和淡淡的忧伤。
他的这种心情的变化,很快地反映到作品上。那种抑郁悲哀的蓝色渐渐地消退,暖洋洋的粉红色慢慢多起来。他所描绘的人物逐渐有了古典人物画中的血色和丰润感。
他绘画的主题也从城市的咖啡馆、贫民区,转到富于浪漫气息的乡村道路和田野以及杂技演员身上。从此,他的创作进入了“粉红色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作品,色调较以前更加柔和,轮廓更加鲜明,人物形象的处理把握得更有分寸。
1905年3月,查尔斯·莫里斯撰文评论毕加索说:“与早期作品相比,他更加敏感和成熟。以前他更多的是沉湎于悲哀之中,而其中并不含有同情。”
那段时期,在“洗衣船大楼”的附近,有一个叫作“梅德拉诺”的马戏团。毕加索在朋友们的影响下,经常去看他们的演出。一块不大的空场地上,在稀稀拉拉、随来随去的一群人中,这些江湖艺人开始表演了。他们变戏法儿、耍猴子、跑马术。在花里胡哨的节目里,毕加索最爱看的就是小丑的表演了。
厚厚的化妆粉已经把演员的五官夸张成另一副模样,衣帽鞋裤也完全不成比例,五彩菱形的服装,使小丑的形象显得稚拙可爱。再加上那些滑稽的动作,很快便驱散了笼罩在毕加索心头的忧郁。
但毕加索并不醉心于此。他常常绕到场子的后面,在绿荫中,悄悄地观察着这些流浪艺人的幕后生活。他们居住的帐篷已经完全褪了色,有的地方还打上了补丁,尤其是帐篷的底部,已经变得毛毛糙糙的了。
在一面敞开的帐篷里,他忽然发现了那位小巧玲珑、身轻如燕的马术演员。此刻的演员,在马背上光彩夺目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她的金发疲软地垂在肩头,那优美的身段,此刻正袒露着一对不太丰满的乳房,哺乳着怀中小猫似的婴儿。那双精制的软底鞋也不见了,一双赤露的脚,正叉开5个趾头,摊在地上。他心里不禁为这种悲苦一震,移开了目光。
但是,他所看到的其他艺人,几乎都是这种样子。台上,他们精神抖擞,光彩照人;台下,他们则疲惫不堪,四肢无力。他们的面色白中泛黄,目光冷峻凝滞。
看到这些,毕加索明白了,这些以卖艺为生的人与自己,与那些穷画家、穷诗人的处境是十分相似的。在红尘滚滚的巴黎,他们同样受到歧视,受到冷落,他们同样填不饱肚子。
所不同的是,这些人又多了一层浪迹天涯、东奔西走、无家可归的忧虑。毕加索的心被同情和悲悯淹浸着,一种用画笔来反映他们的强烈愿望撞击着他的心扉。他立即在街头树下,用炭笔勾勒起他们。
回到画室,他又拿起油画笔,继续不停地塑造他们的形象。他把自己的情感,自己和朋友们的身影,一股脑儿糅了进去。这些作品,比起前一时期的乞丐的作品,在色调上虽然明快了,但反映的并不是人生的欢乐,仍是一种淡淡的哀愁。
在一系列精彩的作品中,特别受到朋友们喜爱的是《踩球的少女》、《卖艺人家》、《家马里孩》等。
《踩球的少女》画的是一个苗条弱小的少女正踩在一只大球上,她努力支撑着身体,试图保持着平衡。她的对面是一个坐在木箱上的强壮的男人,他正以严肃的目光,注视着少女。画的远景是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眺望着远方,那里有一匹白马正在干枯的草原上觅食。
画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有着鲜明的对比。躯体庞大的男人是以垂直与水平线的静态处理,而少女则以优美的曲线表现动态。庞大与苗条,静的表情与律动的优美,在画面上形成了美的对比。另外,线与面的表现,以及色调上的微妙对比,都是这幅画的成功之处。
《卖艺人家》则描绘了流浪艺人四处漂泊的生活。他们在一个地方演完后,便整理好简单的行装,继续上路,到另一个地方演出。这一群在旷野上歇息的艺人中,有一位身穿红衣服的上了年纪的胖胖的小丑。以他为中心,右边有两个少年杂技演员和一位文雅俏丽的女演员。左边站着一位背向观众的花衣小丑和一个手提花篮的小姑娘。
这幅画虽然没有追求情节,但却反映出了卖艺人家的清苦和孤寂。这是毕加索继《生命》之后,对人生的又一次描写。它也是画家以流浪艺人为主题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幅群像佳作。
这时候,毕加索的画技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已经可以不需要模特固定在一处,一笔一画地摹绘了。他作品中的那些流浪艺人,实际上并没有被请到画室里,而是他亲临现场,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再回到画室,凭着自己的记忆力来创作的。
他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进行创作了。每当他握住调色板,拿起画笔,站在画架前面的时候,他的神情立即变得庄严而神圣,他的精神全部贯注到画面之中,他的心灵唯有正在塑造的对象,周遭乃至世间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同时,他也越来越喜欢通宵达旦地工作。或许这是由于西班牙人的习惯在他身上难以消除。他喜爱这种四周漆黑、万籁俱寂的时刻,喜爱这种人人皆睡、唯我独醒的状态。每到这一时刻,他的灵感就像汩汩喷涌的泉水,他的情绪就像肆意燃烧的野火。
他的许多佳思妙想,就在这一时刻产生了。在这个时期,毕加索创作了一幅著名的人物肖像画《盖·斯坦因肖像》。
1905年秋天,毕加索如约来到寄卖画商克洛维斯·萨戈家里,萨戈说有人来看他的一幅画。他一进门,就看见一男一女坐在客厅里,男的戴金边眼镜、蓄着胡子、秃顶。女的身体强健、个头矮胖、但面容姣好、眼睛炯炯有神。
萨戈对毕加索说:“这是盖图德·斯坦因和列奥·斯坦因姐弟俩。”
毕加索对姐姐盖图德独特的长相发生了兴趣,他问画商萨戈:“你说那位女士能同意做我的模特儿吗?”
盖图德对毕加索的话置若罔闻,她说她很不喜欢《挎花篮的青年少女》,她要去掉少女的两只脚,而只保留头部。这时,弟弟列奥说服了她,才使得毕加索的第一幅作品原封不动地挂到了盖图德在佛勒吕斯街27号的卧室里。
同时,毕加索也成了盖图德的朋友,盖图德最喜爱的两个人就是他和马蒂斯了,她因此还写了《马蒂斯、毕加索和盖图德·斯坦因》的小说。
盖图德答应做毕加索的模特,她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她对“洗衣船大楼”破旧和拥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安静地坐下,聪慧的眼睛看着毕加索在调色。闻讯赶来观看的有盖图德的弟妹和美国朋友安德鲁·格林。
盖图德真实动人的神情在画板跃然而出,旁观者连声叫好,他们高喊:“好了,好了,太像了,停笔吧!”
毕加索使劲地摇摇头说:“不。”接着,他又说:“对不起,你们今天是看不到成品的。”
毕加索一再地请盖图德坐在他的画室里,多达八九次。有一回,毕加索颇不耐烦地说:“我再看这幅画时就找不到你了。”然后就把整个头部涂掉。
几个月后,毕加索又重新拿出来这幅画。他凭着自己深刻的印象再次进行了加工创作,终于将肖像的头部完成了。这次他满意了,肖像的头部具备了轮廓鲜明的雕塑感,尤其是那脸部,简直就是一个雕刻面具。
可是,他的朋友们看到这副表情严肃的画像后,却议论纷纷。毕加索对此坦然置之,他说:“没有人会认为它很像她。不过,别担心,总有一天,她会变成这个样子。”
后来,盖图德·斯坦因特意把头发剪短了,来看望毕加索。画家对她注视了片刻之后,便说道:“还好,我的那幅肖像画没有被破坏。”
时隔多年,这幅画才得到世人的公认,并认为与本人惟妙惟肖,同时,还被大家称为“毕加索的蒙娜丽莎”。
盖图德还促成了毕加索与马蒂斯的相见。一个周末,在盖图德的住所有个画家们的聚会,马蒂斯来了,他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五官匀称,蓄着金黄的胡须。他的年龄不到40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
毕加索的作品曾在1902年跟马蒂斯的作品一同在伯萨·韦尔的店里展出过,但他们本人却没有见过面。
马蒂斯和毕加索有许多地方都截然不同:马蒂斯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争论时竭尽全力要说服别人;毕加索则喜欢守口如瓶、默不作声,从不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
在画风上,他们也是截然相反,马蒂斯追求的是宁静、纯洁、平衡的艺术,脱离那些烦恼的事物;而毕加索则表现出豪放、混杂和破坏的风格,着眼点在于毁灭之后的重建。
他们友谊的基础是两人都非常敬重各自的才华。
毕加索在巴黎住的时间还很短,可他已经完成了很多作品,并且已结交了像阿波林纳、沙蒙、瑞弗第、雷诺等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朋友。
毕加索很喜欢画家阿弗雷·加瑞,他还送给毕加索一把小勃朗宁手枪。后来,毕加索常常把手枪放在口袋里,当听到有人说出藐视他的言语,他就会说:“再讲一个字我就开枪。”并把它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毕加索在其他画家聚居区也有很多同行朋友,而“洗衣船大楼”的每一个房客也都很快认识了毕加索。阿波林纳和毕加索的西班牙友人常在晚餐时不请自来,毕加索和费尔南多经常与他们或其他画家共进晚餐。毕加索的屋里还养着许多小动物:猫、狗、老鼠,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猩猩。
这一时期,毕加索的生活很不稳定。他虽然与几位画商保持联系,但很久都没有作任何展出了。曾经有一阵子毕加索已经欠了颜料商900法郎的账,颜料商因此拒绝了对他的颜料供应。这对任何画家而言都意味着要断炊了,此时温拉德不买他的画,而沙果只能出很低的价钱。这样毕加索就更没钱买画布了,他不得不经常在用过的画布上作画,甚至是画布的背面作画。
1904年至1905年的上半年,经济情况就是这样糟,偶尔卖出的一两幅画换回来的钱仅仅能维持他不挨饿。毕加索的生活挣扎在窘迫中。到了1905年的下半年,在爱情的滋润下,毕加索的创作热情越来越高,画技也越来越成熟了。
《坐着的裸女》、《拿扇子的女人》、《化妆》、《演员》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这时描绘较多的仍然是下层人们的生活,但毕加索已经从充满悲哀的气氛中走出来,画面上的暗色已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玫瑰色和柔和的粉红色。
甜蜜的爱情给毕加索带来了幸运,他的作品也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画价也不断提高。没过多久,人们开始接受“玫瑰时期”的作品,甚至出现受欢迎的程度。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画商温拉德的故事。在毕加索前几次到巴黎时,他曾拿着自己精心挑选的作品到温拉德画廊去卖。
温拉德看了看毕加索手中的风景画,不屑地说,“钟楼画歪了”,将作品退给了毕加索。现在,温拉德主动来到“洗衣船大楼”,并对毕加索说:“听说你有一批‘蓝色时期’的作品,我很感兴趣。”
毕加索和雅各布把他的画全部搬了出来。毕加索有些紧张地看着温拉德,温拉德的目光一下子就被这些画吸引过去了。
他一幅幅看着选着,看得爱不释手,无法取舍。最后,温拉德说:“这些画我全要了,小伙子,我应该付你多少钱呢?”
毕加索只怕要价太高了,温拉德不买了,忙说:“温拉德先生,您看着给吧!”
温拉德给了毕加索2000法郎,买走了他画室里的全部画。
看着卖空了的画室和手里的这大笔钱,毕加索请来了几个好朋友,到饭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然后,他和费尔南多搭上火车回巴塞罗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