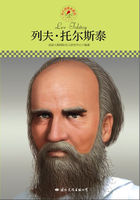这次返乡,使年轻的毕加索更深地觉察到,他的追求与家庭的期望是如此的格格不入,鸿沟已经从裂隙发展到断层,而且再也无法挽救了。
于是刚刚过完新年,毕加索不得不告别这些热情开朗、循规蹈矩的家乡人,离别这块洒满阳光的热土,直奔马德里,再寻前程了。
这次来到马德里,他已经不是一个莘莘学子了,而是一个到过巴黎、颇有见识的成年人了。在马德里,他结交了一个名叫索勒的巴塞罗那朋友,并与他合办了一个刊物《青年艺术》。
刊物的宗旨是宣传现代艺术,报道“四猫”俱乐部的活动。它还鼓舞“为自己理想而感到自豪的新一代起来反抗”,很有些革命的气息。
毕加索十分用心地去经营他的刊物《青年艺术》,他负责所有的插图和广告,广告中还推荐了他朋友的著作《马德里·艺术评论》,毕加索还为这本书画了插图,可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出版。
在毕加索和索勒的努力下,《青年艺术》终于面世了,毕加索在页面的空白处装饰了一些素描插图,图文并茂的《青年艺术》受到了普遍的好评。
就在毕加索全身心投入刊物之中时,由于经费上的原因,《青年艺术》在办了5期之后不得不停刊了。
在马德里,毕加索的生活很艰难,他在哲班诺街租了一间顶楼的房间,此外他只买几件必要的家具:一张铺草垫的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晚上仅靠一支插在酒瓶里的烛光来工作。
他忍受着有限的供水及光线狂热地作画。吃饭自然是既节省又简单,虽然抽烟却很少喝酒,开胃饮料是矿泉水。不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也有极限,寒冷的天气使他那地中海式的活力都麻痹了。
现代主义的气息也渐渐吹到了马德里,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早已接触过它,而在巴黎更是大量地吸收了它,他自己的作品有好一阵子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对毕加索来说,如果巴塞罗那显得土气,马德里则除了普拉多博物馆之外,简直就是艺术的沙漠。
马德里的春天将要来临了。虽然毕加索在马德里结识了不少有情趣的人,因而他也卖掉了一些画。但到了5月的时候,他却放弃了他的《青年艺术》,还有他的阁楼、桌椅。年轻人蒸蒸日上的事业遇到了阻碍。
无奈之中,毕加索决定再赴巴黎。途经巴塞罗那时,他歇了一下脚。加泰罗尼亚的朋友热情而真诚,他们没有忘记毕加索,更没有忘记他那闪烁着天才之光的作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朋友们还为他操办了一次画展。
展品多数是毕加索从巴黎和马德里带来的画作,大多是用蜡笔画成的。其中有《侏儒舞女》。这是一幅猛烈、狂野的作品,构思、着色、下笔都极其精彩,图中那粗鄙、难以名状地畸形女孩,让人乍见之下就兴起一种残酷的感受,但再看一眼就可发现在那明显的苛酷之下,有着深深的同情,这是一种无声的怜悯。
极具分量的批评家尤特里欧,在巴塞罗那的美术评论杂志上刊出了一篇赞美他的文章:
毕加索的作品是异乎寻常的年轻艺术。是他对社会的洞察力、不放过这一时代弱点的眼睛下的产物,表现出美,甚至是丑恶的美,是一种因为画家忠实表现他真正看到的东西所产生的美。
这些展出的蜡笔画只不过是毕加索才气的一部分而已,这位艺术家会引起许多争议,但也会引起所有企图打破既有形象,寻求新颖艺术表现形式的人们的尊敬。
这是对一位不到20岁的画家的极大的鼓舞,但毕加索没有停留下来享受自己的成果。他很少参加自己画展的开幕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在画展中,画家已经把自己赤裸裸地挂在墙上,超出自己的控制能力,并且也不能再改变什么。另外一方面是他得穿上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听陌生人提问:“这幅画你想要表现什么?”毕加索对这一类的事情向来无暇顾及。
毕加索的目的地是巴黎,他要把大批答应过曼雅克的过期画作带去给他,因此只在巴塞罗那作了极短暂的停留。展览会结束后,毕加索便马不停蹄地奔向了巴黎。
到巴黎后,曼雅克邀请毕加索住在克利希大街130号他的不太宽敞的寓所里。他的寓所只有两间房,毕加索在较大的那间住了好几个月。《克利希大街》和《蓝室》就是这一段日子的纪念。
不久,曼雅克将毕加索引荐给巴黎的画商伏拉尔,此人在巴黎画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他是一位伯乐式的人物,识别画才,独具慧眼。许多日后名震画坛的画家初出茅庐的作品,几乎都是首次在他的画廊里展出的。他不但乐意提携年轻的艺术家,而且很热情好客。
他常常邀请年轻的艺术家到他画廊的地下室里,共同进餐。在这间地下室里,来宾可以品尝到西班牙风味的菜肴,还可以喝到他珍藏多年的法国葡萄酒。
而最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们还能见到老一辈的画家和一些有眼力的收藏家,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与这些人交流。因此,在巴黎生活的年轻艺术家都很尊重和热爱伏拉尔。
这次曼雅克协助毕加索挑选了65幅作品,请伏拉尔在他的画廊里展出。当伏拉尔看到毕加索的这些作品时,眼前忽然一亮,他一反自己常有的谨慎小心的作风,满口承诺,同意展出。
于是,毕加索近期的心血之作,便稳稳当当地挂在了伏拉尔画廊的墙壁上。这些作品,既有肖像画,也有山水画,既有室内画,也有街景画。它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年轻的毕加索各方面的才能。
1901年6月24日,这场展览开幕了,这是一个合展,还同时展出了巴斯克·埃乡里诺的作品,他30多岁。而评论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毕加索的身上。
古斯塔维·柯奎欧特是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他在评论上写道:
毕加索是一个美妙的画家,他对所画对象的提升证实了这一点。像所有纯粹的画家一样,他崇拜色彩本身,而每件物体都有它的色彩。
他爱所有的主题,对他而言任何东西都是个主题——花朵从瓶中腾跃的光线,花瓶本身甚至它下面桌子的跃动,还有那飞舞着、充满光线的空气。
这次画展带给毕加索的除了赞美之外,还收获了麦克斯·杰克卜的友谊。麦克斯·杰克卜是一位具有感受力、聪明而又一贫如洗的批评家、诗人和作家。他对毕加索的作品印象深刻,因而想方设法来结识毕加索。
25岁的麦克斯·杰克卜,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是个极具天分的人,吸引人、读书多、非常感性、口齿伶俐、害怕女人。他的父亲是个犹太裁缝。杰克卜在画廊留下一张赞美毕加索的字条,曼雅克知道后,便请他去拜访毕加索。事后他描述道:
跟我一样戴着一顶高帽,被一大群西班牙的穷画家围在中间,坐在地板上边吃边聊。在那些日子里,他每天画两三幅画,他把晚上的时间都花在音乐厅的布景后面,给那里的明星画像。
他们握着手,相互笑了笑,因为语言不通,便又紧紧地握了握手。杰克卜看了看那些画布,毕加索已画了好几卷。随后又出现了很多西班牙朋友。
这时拘谨消失了,有人煮了一些豆子,他们就散坐在一起吃着。晚餐结束时,除了毕加索,其他的人开始用口哨代替乐团,企图演奏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
第二天,毕加索和朋友们结伴回访杰克卜住的小房间。在他们漫长的讨论中,有些人离去了,曼雅克这个翻译也睡着了。毕加索和杰克卜注视着挂在墙上的道弥尔、加伐尼兹和杜勒的木刻。剩下的时间毕加索都在听杰克卜朗诵他自己的诗。告辞的时候已是黎明,杰克卜把道弥尔、加伐尼兹和杜勒的那些木刻全都送给了毕加索。
画展很快得到了评论界的赞赏和一些艺术家的承认。这正是毕加索梦寐以求的。他急于得到承认,急于获得成功,他恨不得让每一个人都知道,画界有个才能非凡的毕加索。
躁动的心,使毕加索变得急不可耐了。可是,上帝没有使他如愿。展品一幅也没有卖出去。当初满怀希望地挂上去,现在又遗憾地全部收了起来,伏拉尔同情地说:“画家连买个画框子的钱也没拿到。”
那一年的冬末,萨巴提斯为了找毕加索特意来到了巴黎。这里的许多事都让萨巴提斯非常惊讶:巴黎一片大雾,昏暗的太阳下,上午10时,毕加索就在车站等他了,平常这个时候毕加索还在睡大觉呢!当毕加索把他带到克里奇大道的住处,给他看最近的画作时,萨巴提斯更是惊讶不已。
他在巴塞罗那所认识的毕加索似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些作品中有一些猛烈的、色彩鲜艳的图画,是毕加索自己的视野和凡·高的融合的产物;一些人像,色彩斑驳得像扑克牌里的一些丑角,悲伤而孤独的人物;另外还有卡萨杰玛斯的画像,有活的有死的,有在开启的棺木边的哀悼者,在一幅《卡萨杰玛斯的葬礼》的巨幅画作中表现得酣畅淋漓。
此外还有一些好像来自另一世界的作品,一幅印象派的克里奇大道,还有几幅令人满意的静物。但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是,属于毕加索的整个世界都渗入了蓝色。
而画商曼雅克却是颇为沮丧,因为毕加索的画风越来越不可捉摸。毕加索从巴塞罗那带来的斗牛画,还有在克里奇大道头一个月的作品都十分令人赏心悦目,这时的毕加索是个可指望的投资者。但是没有人会买这些蓝色的近作。
那时,毕加索身旁有一大群愉快的、可亲的伙伴,但他只可能和麦克斯·杰克卜谈他画里更深一层的含义,这是因为语言的障碍束缚了他。毕加索已经学了一些简单的法语,不过还绝达不到艺术交流的目的。其实对他来说,即使他能讲出流利的法语,但任何词语所能表达的思想也不如一张图画。
在巴黎停留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毕加索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上是一个裹在黑色大衣里的半身男子,严肃的大衣和近黑色的头发和他苍白的面孔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有一圈胡须,一些杂乱的小髯,而他特大的眼睛深深地下陷,注视着远处。这张脸上深深地刻画着磨难、怀疑、内在的冲突以及不快乐。
在谈到这幅自画像时,萨巴提斯说:“他相信艺术是悲伤和痛苦的孩子,他相信不快乐适合于沉思,而痛苦是生命的根本。”
所有看过毕加索这张自画像的人,都对这些话给予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