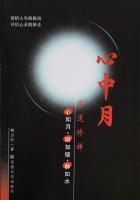一
六月的湘乡,早已进入炎炎夏日。巨大的樟树上,知了开始一声接一声地鸣叫。街道上一片木屐之声,遗老遗少们纷纷走出屋子,在樟树下下棋纳凉,喝茶聊天。女人们遵从着三从四德的古训,轻易不会走向街头,于是,住户人家便打开了所有的门窗,希望尽可能地透进一丝儿荫凉。
在一片深巷里,唯有一户人家大门紧闭,二门紧锁,偶尔会有个把佣人出门进行必不可少的采购,当他们匆匆走出或进入时,那扇大门很快就会关上。即使这样,那紧闭的大门口仍坐着一个高大的男仆,他坐在这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似乎连一只猫儿也休想从这门里钻出来。人们注意到,这高大的门楼上挂着一只略显陈旧的灯笼,灯笼上那个大大的“萧”字显得格外醒目。
毕竟是暑热蒸人,萧府的男仆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未免疲乏,不一会儿,他那只肥大的脑袋便像寺里的鼓棰一样一下一下地点了起来,却又没有一点规律。过来一架黄包车,在这样暑热的中午,黄包车夫也难得揽到一宗生意,于是,黄包车夫便把车停在萧府的门口。车夫显然和萧府的男仆相熟,他一边掀起衣襟擦着汗,一边走向男仆并打着招呼说,老兄今天好差事,怎么当起门神来了?那男仆终于睁开惺忪的睡眼,打了个哈欠说,是啊,今天府里有些情况。车夫兴趣来了,他凑过去说,什么情况,热死人的天,怎么就把个大门关得死紧。男仆扭头从门缝里看了看里面,然而神秘地说,少爷今天早上又被人找回来了,老爷怕他再跑出去,今天又要给他纳一房妾呢。车夫笑起来说,有这等好事,少爷为什么要跑啊?听说少爷一心要做和尚,有这事吗?男仆说,是啊,这少爷也真是的,有这样的艳福却不愿享,却要去做和尚,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属什么的。
两人正在门外说着话,而在萧府里面,却正在上演着一曲“拉郎配”的喜剧。萧家少爷萧岩正被人塞进一间厢房里。厢房分左右两间,左间是他的正室田氏,右室则是刚刚为他纳进的姨太太谭氏。两位夫人虽算不上貌若天仙,但却生得眉目清秀,文淑娴雅,两人中一人出身于名门望族,一人则为小家碧玉。萧岩是在他二十岁时与田氏完婚的,但蜜月刚过,少爷就借故出门求学,结果却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萧玉堂老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听到儿子的行踪,原来他是在南岳的一座寺庙里听闻佛经。此后他总是借故跑出家门,然后就躲在某一座寺庙里听闻佛法。一家人都拿他没有办法。
萧岩是萧玉堂前任妻子颜氏所生的儿子,萧岩生下不久,颜氏就因病离开人世。萧岩一直是由庶母王氏带大,庶母对他虽然谈不上慈恩亲情,但虐待他的事件却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然而萧岩却自幼郁郁寡欢,所读书中,唯对佛经之类有着特别的兴趣。萧玉堂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莫非儿子将来真是做和尚的命?虽然他自己也是一名信佛的居士,但是,做一名居士和让儿子出家为僧毕竟是两码事。儿子连着跑了两次之后,萧玉堂就想,或许出身名门的田氏太过正统,不善风流,因而拴不住儿子一颗心,于是,这次把儿子找回来之前,萧玉堂就又替儿子物色了比萧岩小二十岁的谭氏。比起田氏来,谭氏自然要年轻得多,小家碧玉的谭氏因为少了大户人家的许多规矩,所以性格也活泼得多。萧玉堂想,有了这一房年轻的姨太太,不愁拴不住儿子的心,也不愁自己抱不上孙子。
为了给儿子的厢房降温,萧玉堂让人不断地在儿子的厢房外泼洒井水。太阳终于落下山去,蒸腾了一天的街道也终于渐渐地凉爽起来。儿子厢房里的灯依然亮着,直到鸡叫三遍,灯光这才灭去,萧玉堂这才安心地睡去。然而天亮后,萧玉堂得到一个惊人的报告,儿子萧岩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那扇木格窗户,从后门翻墙逃出了萧府。萧玉堂一阵头晕目眩,一股黑血从口中涌出,接着就昏死过去。
二
萧岩接受了上两次的教训,这一次他准备了充足了盘缠,沿着湘水一直往南走去。一个月后,他来到福建省的福州鼓山涌泉寺,跪倒在常开老和尚的膝下。于是,选了一个吉日,常开老和尚为萧岩举行了隆重的剃度仪式,并赐法名古岩,又名演澈,字德清。
这是发生在光绪八年的事情(1882),德清这一年是四十一岁。
剃度的第二年,德清又依妙莲法师求具足戒,成为一名真正的比丘僧。而当真正走进佛门,尝闻到无尽的法味,德清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出家,真是太迟太迟了啊。当年佛陀为了寻求真理,毅然走出宫墙,于苦行林中六年麦麻生涯,终于成正等正觉,为人天师范,而自己却以最好的年华于俗世中虚度时光。于是,他决定效法佛陀,走入大山,行头陀苦行。
陕西终南山是一座著名的禅宗道场,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希望在佛法的大道上有所成就的人一批批地走进终南山,然后就选择一处山洞,或于一片荒林中结茅安禅,以一种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行,磨砥自己的意志,消除色身的欲望,寻求解脱的途径。
终南山山高林密,洞窟幽深,德清在这里看到一具具跏趺而坐的枯骨,看到一个个在洞窟中禅坐的修道人。这所有的一切,与当年佛陀的苦行林是何等相似啊。他选择了一片林子,然后便砍下芭茅和松枝,为自己搭建了一座小小的茅篷。他又在住处周围栽种了一片洋芋,他将依靠这些简单的食物,支撑自己的肉体生命,度过自己的苦行生涯。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出茅屋的时候,德清为自己崭新的开始而兴奋着。他走出茅屋,但见远处的山崖被层层飞渡的闲云笼罩着,那变幻无定的云雾时而像海浪般扑腾,时而像云絮般宁静。于是,他给自己重新取了个名字:虚云。从此虚云的名字开始打入中国佛教的史册,一代一代的佛教人也就永远记住了这样一个不朽的名字:虚云。
带来的简单食物早已用尽,而地里的洋芋才刚刚露芽。饥饿像野兽一般侵袭着他的色身肉体,他也开始与这不可抗拒的饥饿进行抗争。在那些日子里,他就像一个野人,漫山遍野地寻求着一切可以食用的野菜和野果。有一天,他食用了一种有毒的野菜,全身肿紫,昏迷不醒。他想,这令人憎恶的色身肉体就将寂灭了吧,于是他双腿盘坐,想象着佛国的美好与庄严,进入一种涅槃的境地。三天过后,虚云奇迹般地生还,然而饥饿仍然驱之不去。他从树上一把一把地捋下树叶甚至松毛,就着溪涧里的清水,大口大口地嚼食着。终于熬到洋芋成熟的季节,他数着那些洋芋的棵数,想着如果每天挖出一颗,他仍可以支撑一年的时间。
两年之后,虚云走出了终南山。在山口,他遇见第一个人,那是一个打柴的村夫,那人被虚云的形象吓得一声惊叫,赶紧跑了。也就在这时,他才从溪涧中照见了自己的影子。此时的他乱发披肩,颧骨高耸,双眼深陷,活脱一个山野怪兽,他这才知道,两年的苦行,除了将自己折磨成如此模样,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虚云背着他的行囊,拄着他的禅杖一路向南行走。他来到浙江天台山,拜倒在一代大德融镜老和尚的膝下。当他抬起头来时,融镜老和尚吃惊地看着他说,你是谁,为什么是这种模样?
虚云说,弟子德清,又名虚云,弟子在终南山饥餐松毛,渴饮山泉,冬夏一衲,不蓄余资,苦行两年有余,但却未曾有得,所以弟子今天特来请求老和尚给予开示。
融镜说,你这副模样见我,是想把老衲吓出病来吗?去,先洗澡,再理发,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来见我。
半天之后,虚云果然恢复了僧相,他再次跪倒在融镜老和尚的面前请求开示。
融镜说,佛祖虽经六年苦行,但佛祖最后还是接受了牧羊女的布施,走出了苦行之林。须知我们的色身肉体是因,所谓修行办道,就是要通过眼、耳、鼻、舌、身、意体悟色、受想、行、识、五蕴之苦。没有身体之因,又哪里会有证悟之果?须知你以前的做法皆非正道,从今以往,你须剃发、穿衣、吃饭,保持健康的体魄,过正常人的生活,尔后才可修行办道。
融镜老和尚的一顿训斥,虚云听之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融镜的教海虚云悉皆从之。
三
在天台山,虚云跟随融镜和尚修习天台教观,不久又前往国清寺、方广寺参学,又去天童寺听楞严,于阿育王寺瞻仰佛舍利。在这些年里,虚云的足迹踏遍了中华大地,结识了无数的名僧,从而使自己的道业得到迅速的增长。
光绪二十年(1884),虚云来到扬州高旻寺,参加这里的禅七活动。
佛界自古有“金山的腿子高旻寺的香”的说法,可见这两座禅宗寺庙僧人坐禅的功夫是何等深厚圆熟。高旻寺的禅七一年四季几乎都有,每一期禅七少在四十九天,多则半年之久。每一期禅七结束,均会有一些僧人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启悟。
虚云来到高旻寺后,即刻住进了禅堂。一切的质变,均是由量变开始,就像当年的佛祖一样,虽然苦行林中的修行并未能使释迦牟尼真正开悟,但却为今后的的启悟奠定了基础。经过终南山的两年苦修,再经过这十多年的南北参学,此时的虚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急于求成的修道者了。坐在人头密布的禅堂里,虚云不闻周围的人声,不见四周的人群,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一颗炽烈的心脏在跳动,在思索,在寻找。虚云抓住一个话头:“坐禅者到底是谁?是虚云吗?虚云究竟又是谁?”他就是这样一直穷究下去。以至有一天他在倒一杯开水时被沸水烫着了双手,那杯子掉落在地,随着茶杯落地的一声脆响,虚云忽然感觉到这大千世界豁然开朗,于是,他随口念出一偈:
杯子扑落地,响声明历历;
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
此刻,他的心地一片光明,几十年来所有的往事都在一刹那间涌现在眼前,于是,他接着又诵出一偈:
烫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语难开;
春到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
他走出禅堂,走到这光明澄澈的大千世界,领略这世界所带给他的智慧和愉悦。
光绪二十六年(1900),虚云来到北京,正好这一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带着光绪一行仓皇出逃。虚云也不得不随着逃难的人群从刚刚走进去的北京城逃离出来。逃难途中,虚云结识了不少朝廷官员,不想却为今后开辟佛道打下了政治基础。也正是凭着这些政治基础,虚云在以后的岁月中传承曹洞宗,兼嗣临济宗,中兴云门宗,扶持法眼宗,延续沩仰宗,一生兼挑中国禅宗五家法脉,成为中国佛教史中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