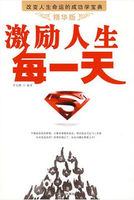一
非写实小说,是相对于写实性叙事习规来分类的。我们研究这一类型,考察其叙事语法的演变,寻找这类叙事作品中所蕴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关注小说家在20世纪被社会、时代等所激发的想象力、创新性以及这种创造的延续和消失趋势,探求非主流的潜在的大众文化心理,应该隶属于小说类型研究的范畴。
小说类型反映着小说艺术发展中那些最持续、最悠久的要素。这些要素通过不断的再生而长存不灭,是小说的生命记忆。为了理解类型,我们常常要追根溯源。在中国小说研究中,小说的分类极其混乱纷杂。早在明代胡应麟就有了“最易混淆者小说也”的感慨。参看胡应麟着《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有关论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在古籍经、史、子、集四大类中,小说因其所具有的一点点史料价值而能够依附于子部或史部。作为正史的补充而自成一家的“小说”,分类十分庞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将“小说”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清代的纪昀在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将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类。后人在形式上还有笔记、传奇、话本、章回等简单分类,内容则有志怪、志人、公案、烟粉、人情等分类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小说”这种文类的认识。20世纪初,小说家也很喜欢给小说分类,“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理想小说”“社会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航海小说”“虚无党小说”“教育小说”“哲理小说”“历史小说”“奇情小说”“神怪小说”“开智小说”“地理小说”“拟旧小说”“军事小说”“婚姻小说”“警世小说”“复仇小说”“言情小说”“种族小说”“国民小说”“家庭小说”“义侠小说”“商务小说”“殖民小说”“幻想小说”“札记小说”“实事小说”“爱国小说”……这些分类有的是杂志的广告技巧,有的是栏目所需,分类标准杂乱,其界定的内涵和外延都很模糊,也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虽然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小说丰富复杂的创作情形,但是这种分类很难反映出小说的叙事艺术的发展变化和类型特征。
最有影响力的分类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明清小说分为讲史、神魔、人情、侠义、讽刺谴责、以小说见才学者等类型的研究,他兼顾了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的标准,而且从整体上把握小说类型的演变,后世研究者少有创新突破。参看陈平原着《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一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但是,要说明的是《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两书是在为小说作史,而不是讲小说分类。书中28篇篇目的分类时而依内容,时而依形式,比如“神魔”“人情”依内容,“拟宋人小说”“拟晋唐小说”依流派,“以小说见才学者”依写作风格,“传奇”“话本”依体裁,“讽刺”“谴责”依审美品格等等。这种分类从讲史的角度来看,兼顾时空,显豁醒目,便于论述,然而如果以此来作为科学的分类则不尽如人意,后人在研究中无法全盘照搬。孙楷第就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分类说明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鲁迅先生小说史略于传奇及子部小说之外,述宋以来通俗小说尤详。……品题殆无不当”,然而“唯此乃文学史之分类,若以图书学分类言之,则仍有不必尽从者。”他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沿宋人之旧”,可是宋代之后小说的发展类型延沿甚广,又不是宋之分类可囊括得了的。小说类型研究本身是一种预设性的理论,用假设的类型标准去衡量复杂丰富的文学现象,先天就是会有困境的。追求纯粹的分类、完整的分类、全面地囊括,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各种有利于描述说明文学现象的分类,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按照不同的研究需要来进行不同的分类是完全必然并且可行的。
近期,对小说类型理论比较关注的有陈平原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第三篇“中国小说类型研究”(1993年)、郑家建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语境》中第四章“小说类型研究:理论与实践”(2002年)等论述,他们对西方和中国小说类型理论的发展及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探讨,从史的角度来把握小说类型,深入到小说艺术表现深层寻找研究的突破口,“即力求使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理论建构为建立中国现代小说诗学提供一种初步的尝试”。关于小说类型研究的成果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是对某一类型或某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的考察,如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1990年)、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1988年)、刘勇强的《幻想的魅力》(1992年)、欧阳健的《中国神怪小说通史》(1997年)、齐裕焜和陈慧琴的《中国讽刺小说史》(1993年)、林辰的《神怪小说史》(1998年)、向楷的《世情小说》(1998年)、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年)、李鹏飞的《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2004年)等着作,还有王达敏的《新时期小说的非现实性描写》等论文。这些类型研究注重的多是主题、内涵、作家作品以及文化背景等,对小说的形式、创作手法等属于小说艺术本身的因素关注不多。
关于晚清这一阶段的小说研究中,有近20种专着。有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袁进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武润婷的《中国近代小说演变史》、方正耀的《晚清小说研究》和颜廷亮的《晚清小说理论》等等,还有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了晚清小说的变革,如袁进的论述很有理论深度;注重了研究方法的使用,如陈平原运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对近代小说的叙事模式的阐释,影响很大。这些研究取得的开拓性成就有目共睹,已为学界肯定。但是,相对于晚清数千种小说这一巨大的创作量来说,这些研究量显然是不够的。在目前研究中得到充分论述的作家不过数十家,论及的作品不过几百种,许多资料还有待发掘整理。晚清小说在数量上的巨大决定了其在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在质量上,还有待于我们跳出传统研究视野的束缚重新认识,发掘出精品。研究现代通俗文学的范伯群先生阅读了大量近代小说之后,在其论着中就提出“现代通俗小说中有若干数量的精品”的观点,可以证明晚清民初的小说在质量上是值得审视考量的。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重点论述晚清小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揭示其所具有的重要文学史意义,试图将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整合起来,梳理出完整的转型轨迹。
如果我们尝试突破阿英、鲁迅、胡适等以“五四”为视角的晚清小说研究理论,从写实与非写实这种形态类型考察小说创作,抛开各种既有的成规思路,以“非写实”这种中国小说自身叙事传统来观察其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的消长起伏,寻觅多年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或许可以比较深入客观地描述出中国小说一脉现代性的形态演变支流,是为本文努力的方向。
长期以来,我们研究者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写实性叙事作品作为主流类型加以提倡,而对非写实的叙事作品关注不够,并且用写实性的叙事习规作为唯一标准来评述各种创作,常常对于非写实的作品隔靴搔痒,不得要领,甚至无法言说。这也是以想象世界为表现对象的科幻、武侠等小说的研究比较冷落的一个原因吧。现今,我们走出了新文学的范畴,把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体文学创作,很多类型的小说被描述、被界定,但是多局限于表层归类而缺乏深入探究。“小说类型研究首先必须根据某种理论原则将作品进行分类编组;但其目标绝非编制分类的小说目录,而是借助‘分类编组’以利于进一步理解和描述小说发展进程。”确实,类型研究绝非为各类小说寻找其家族归属,而是将某一部作品放在具有相似性的同类作品中考察,发现其在传统中的创新性和在这一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中展现的个性化因素,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说明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只有将隐藏在千变万化的故事情节后的具有共通性的叙事语法归纳总结出来,描述出其演变的轨迹,才能正确理解评价这一类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史地位。从叙事习规这一角度入手,可以考察文学本身的传统承传和变化,深入到文化心理、想象资源、美学特质等多种叙事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比较直接地发现小说的创新之处和艺术魅力所在。
二
非写实小说在20世纪初繁盛一时,民国之后渐趋边缘性,到世纪末20年又开始重新兴盛。这种文学叙事习规的遭遇不仅是读者、创作者的功利性选择,也牵涉到小说这种文体在文学结构、文化结构中的作用,是一系列的文学技巧、社会思潮、艺术价值等的选择和表现。这是我们现有的类型理论无法涵盖的。
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示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向于其反对之方面。”参看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有关论述,见:《王国维文艺美学论着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认为小说创作可以针对现实进行想象,以非写实习规描写理想世界。1908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造境”和“写境”,“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同上。这里虽非指小说创作,却提出了“写理想”与“写现实”两种创作方法,所谓造境,就是关注超现实的世界来进行创作,可以说是对应非写实的;而写境,就是客观地描写现实,对应的是写实性的创作。这些论述在理论上对写实与非写实的创作进行了探讨,表现出对这种文学现象的关注。
20世纪小说研究中,最早提到从虚实形态角度分类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在着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谈到小说的吸引力,一是因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人们都希望体验非现实的世界,突破“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而“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所以创作出“理想派小说”,这类超越现实生活的“写理想”的小说,突破现实客观条件的限制进行虚构幻想,应该算是非写实的创作。另一种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人之恒情,欲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这就是“写实派小说”,描写真实的日常生活。“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理想派小说”的创作必然要遵循超现实的幻想、想象来叙事的习规,来创造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才能“导人游于他境界”,这就是非写实的创作;“写实派小说”则明确指出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和盘托出”以引发读者共鸣,达到审美效果。这两种叙事方法大致相对应的就是非写实与写实的小说类型。梁启超在文章中重点论述的是这两种小说“不可思议”的社会力量,从而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主张,并不是要探讨小说叙事艺术的问题。但是,这种观点把小说和现实政治的关系密切化,把小说从单纯的“怡情之品”扩大为社会运动的一方面,无限夸大小说的社会功用,也就导致人们更为关注与现实关系密切的写实性创作。对于“理想派小说”,后人关注十分有限。
此后的小说理论文章,莫不受这篇文章影响。后世小说家及研究者基于同梁启超一样的功利性文学观,让小说负载起济世救国、改造国民的大任,同时还接受了西方文学写实的传统观念,也就更多着力于“写实派小说”类型的创作和研究。于是,关于“现实”的文学观念渐入人心,现实主义的创作兴盛起来。甚至,写实文学被看做20世纪中国文学的唯一文学传统和文学源泉。
其实,当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现代小说的发生时,在新文学写实小说模式尚未成型之前,众多的小说创作在传统的观念下呈现出大量非写实特征,或是用奇幻小说来书写对积弱积贫中国的未来想象,或是用科幻狂想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或是用鬼怪神仙寻求超现实的力量等等,无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在诗学创造上表现出惊人的、旺盛的、成熟的创作力。这种创造力也许来自异邦的刺激,也许脱胎于自为的新意,总之,表现出晚清作家在小说创造上的无限活力和革新能力,也证明了叙述国家政治文学话语的多元性。
晚清传统文学深受域外文学的冲击,汲取了丰富的文学营养,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西方文化的强势促使现代新文学资源主要取自西方而不是中国传统,加上政治话语对文学的渗透,使人们对传统小说不再关注,而重在对欧美近代小说的移植。在文学观念上,新文学家们对中国传统小说进行了清理与批判,黑幕派、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章回体、某生体等等均被斥责,与被视为“不出诲盗诲淫两端”的传统文学密切相连的非写实叙事习规,也就随之渐趋冷落。然而,所幸的是,作家的想象力远超出评者史家的视野,在写实主潮中非写实的功能片段和叙事习规仍旧存在。直至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非写实小说则又蔚然成风。这种创作类型在20世纪小说创作中一直是绵延不绝的。但是,20世纪的中国现代小说已被描述成以写实为基础的一种文学话语,如此,非写实创作将如何定位?曾经被现代写实文学挤压至边缘的非写实在当代文学中竟然成为最具现代性的先锋文学的叙事习规,而且,这种叙事习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始终表达着人类的创造力、好奇心等人性本能。且不说在早期的东西方文学中大量存在的英雄幻想、魔法巫术幻想、武侠剑客之类的小说,单是近几年风靡全球的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的热销和多部非写实电影如《指环王》《骇客帝国》《功夫》等的热映,无不证实着非写实叙事的艺术魅力。
三
我们之所以关注非写实小说,是因为非写实叙事习规始终存在于中国小说的叙事中,而且具有诸种现代性叙事特征,如淡化情节、非理性、轻人物等,呈现出小说艺术亘古的艺术生命力。顺着这一绵延已久的藤蔓,也许可以寻觅到现代小说在尝试、冒险、创新中,从古代叙事之壳中辗转蜕变而有了较为成熟的现代性叙事模式的发展轨迹。当我们把研究视野从写实性主流文学扩展到其他非主流创作现象时,发现晚清众声喧哗的创作在新文学主流文学的挤压下逐渐走向狭隘的路径,成为众声合一的呐喊。而非写实创作是否就此销声匿迹?
不仅如此,我们所看重的还有晚清非写实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创新尝试这种时代精神。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付出血的代价的中国,任何尝试创新的冒险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力气。而晚清非写实小说其想象之天马行空和瑰丽神奇、其叙事的丰富多样、其对中外文学的颠覆借鉴等等无不体现出一种无羁无绊的创新精神。在传统中纠缠的中国小说借助这种文学冒险精神,冲出了古代,走向现代。这种冒险创新的精神正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精神之一,是20世纪文学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而值得我们关注。
但是,这种非写实的创作倾向和描写在研究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着名海外华人学者王德威就曾指出非写实的“科幻小说曾在晚清风靡一时,迄今却仍为文学史家所忽视”。由于现当代文学中“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等文学观念阻碍着这种文学创作类型化趋势的研究致使对这种文学现象的描述很少有人涉及,更不要说对此创作的文本、创作心理、社会背景等进行具体的分析解读。实际上,这种类型研究对揭示现代小说在美学上和传统的关系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呈现出传统小说的美学资源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在怎样的条件下获得创新和转换,可以考察20世纪中国小说在现代性历史叙事背后所蕴含的一系列复杂形式。
另外,通过对非写实小说文本的研究,可以揭示出“现实”这个观念如何进入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现代文学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以此为参照,观察到现代写实性小说的创作得失。“现代小说本身是一种类型,同时它又是在类型开始消灭的时候诞生的。而超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所做的尝试乃是要恢复在此被压抑掉了的诸种类型。”因此,非写实类型小说被压抑又被重新发现的这个过程尤其值得玩味。更为重要的是,在非写实小说的研究中,可以了解中国文学家独特丰富的想象力,感知其艺术独创性和审美魅力,对夸大理论向度而稀释审美性的研究倾向加以匡正。面对当下类型化小说创作潮流,非写实因素日益增强,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着这种创作意识的走向,从而为今后的创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而今,在摆脱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尺度之后,一种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史观使我们重新解读了大量经典作品,更为关注作品的艺术性,感性化地评价和认识,充分展现研究者的主体性。即使这种审美化研究本身是一种为了脱离原有的政治话语而故作的姿态,在具体研究中落实的程度值得怀疑,但却使现代文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切入的角度、使用的方法等都有了极大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对文学审美形式的关注和对现代性的反思下,那些在文学史上被遮蔽的非主流作家逐渐被发掘出来,同属一个文学空间的俗文学和雅文学互动渗透的历史现象被呈现,研究者重新绘出了现代小说发展的多元化格局。这给我们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契机和可能性。研究晚清以来近20年的文学实践,从传统的非写实叙事习规切入,可以避开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单一的所谓主流文学的影响,避免简单化复杂多元的文学现象,揭示其文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和多重现代性追求。这种研究是一种回到小说本身传统的类型研究,是诗学层面的、落实到文本的研究,是探讨小说文本在传统内部之自我改造和发展的诗学规范和诗学理念的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学术研究现状的思考和新的研究尝试。本文力图以此为类型研究之范本,还原文学现场,解读小说文本,以期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现代小说的类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