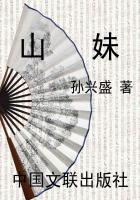诗歌起源的探讨同艺术起源问题一样,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时至今日,用思维与文化的眼光重新考虑这一课题,似可区分出诗歌的二重起源——圣诗与俗诗,分别加以探讨,从而避免许多纠缠不清的死结,使问题逐步明朗化。
简单地讲,圣诗即指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礼仪活动的诗歌唱词,如祭祀歌词、咒词、祝祷之词、招魂曲词等等。圣诗起源之早,当与人类法术思维的成熟和语言的发生同步。各大文明初始时期被各种宗教奉为“经”的诗歌作品,如古印度的《吠陀》和《薄伽梵歌》、古伊朗的《阿维斯塔》、希伯来《旧约》中的《诗篇》、古埃及的《亡灵书》中的诗作、苏美尔和巴比伦文明中的颂神诗与创世史诗《艾努玛·艾利什》、古希腊文明中大部分失传了的诗体启示录据吉尔伯特·默雷(G。Murray)《古希腊文学史》:“这种启示录最初出于俄耳浦斯、缪赛乌斯和巴喀第斯之口。这最末一类久已失传,只留下很少的遗迹,而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诗,则构成我们最初的文学的纪念碑。”等等,便都是因及时见诸文字记载而保存至今的圣诗。俗诗与圣诗相对而言,泛指一切与宗教信仰并无直接关联的民间歌谣、韵语唱词等。俗诗的起源从理论上讲,当与圣诗不相上下,同样以人类语言能力的发生为前提。但由于二者在初民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及地位大不相同,所以早期的俗诗大都因为无法及时记录为文字而湮没无闻了。《诗经》中的“颂”与“风”,大致上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圣诗”与“俗诗”,而“雅”则介乎二者之间。
圣诗与俗诗虽同样古老,但其内容和形式都各具特色,相互之间既有影响作用,又明显地属于不同的思维和文化产物。《诗经》中的《周颂》31篇皆由一章组成,而《国风》和《大小雅》则为多章叠咏体,仅此一种区别,即可看出二者本不同源,似应区别对待。参看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61—62页。圣诗的溯源研究实际上必然属于宗教文化的范围。俗诗的根源则在于世俗文化,尤其是民间的性文化方面。随着从原始到文明的演进过程,许多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对象的圣诗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也就是从固定于仪式场合演唱的歌诗向非信仰的、文学性的说唱诗转变。我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现存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以创世神话和祖先事迹为主题的长叙事诗,似可看做是由仪式性的圣诗脱胎而来的产物,它们同世俗的抒情歌诗并不同源。安德鲁·兰的看法是,应区分民歌与史诗的不同来源,他说:
民歌有长时期和普遍的流传是可以证明的;这些歌的起源,从民众嘴里和心里出来的,同那些艺术诗的起源,由于贵族为得要求一种只有他们能有的那种史诗而生的,可以说是正相反。安德鲁·兰(Andrew Lang):《民歌》(Ballad),家斌译,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编《歌谣》周刊第18期,1931年5月。
按照这种看法,民歌出自民间,反映的是民众的世俗心声;史诗出自贵族,是个人性诗作的滥觞。如果参考当代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安德鲁·兰所区分的诗歌的两类源头实际上正是“圣”与“俗”的区别。
就希腊和印度的大史诗传统而言,《伊利亚特》和《摩诃婆罗多》虽已脱离了宗教信仰的束缚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多少仍具有圣诗的色彩。
与史诗传统相对的民歌或歌谣之所以具有充分的世俗特性,因为它出自与宗教圣事远离的民间下层阶级。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说的正是下层民歌创作的情况,与“美盛德”的贵族宗教诗和史诗显然大异其趣。尽管远古时的情形因无文字记载已无法详考,但是从现代的民谣民谚的产生的分析中多少可以获得一些启示吧。傅振伦先生1925年作《歌谚的起源》一文在这方面先行了一步。文中把歌谚的创作者划分为六类:
1.小学生。如“赵钱孙李,师父捻米;周吴郑王,师父溺床”之类。
2.儿童。如“父十三,母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之类。
3.乞丐。傅氏举出的例子是:“老太太,真有福,抱着孩子他不哭。”
4.说书人。过去把说书人所作谣谚通称为“小段”,如《高高山上一老僧》等。
5.杂耍卖艺者。这些民间卖艺人在演出时口中常有韵语同观众交流。如乡间玩帆船(扮角游戏之一种)的人唱词:“人老了,人老了!吃不动了的多,吃动的少。人老了,人老了!白头发多,黑头发少。”
6.妇女。这一类在数量上颇为可观,例子遍布各种民俗歌谣书刊之中。傅振伦:《歌谚的起源》,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编《歌谣》周刊第87号,1925年。
傅氏这种歌谚起源分类法虽在逻辑上欠严谨,毕竟还是显示了诗歌产生的世俗文化背景的主要情况,对于从“俗”的一面了解诗之构成不无帮助。如他所举出的第6类妇女,作为民间歌谚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以说自古而然。圣诗《颂》的部分中绝无女子创作殆无疑问,然《风》诗中出自女性的作品确实相当可观,从道学立场出发指责“淫风”的朱熹就已意识到这一点,他说“郑风淫”的主要依据便是郑风中多有“女惑男之语”朱熹:《诗集传》卷四,郑风总评。。时至今日,讨论妇女与歌谣之关系的学者已经断言,从歌谣的内容方面判断,几乎半数以上是有关妇女问题的;从歌谣的作者方面判断,也有一半出自妇女。刘经庵先生解释说:
歌谣为什么一半是妇女们造成的?天所赋予妇女们的文学天才,并不亚于男子,不过她们久为男子所征服,没有机会去发展罢了。但是她们的文学天才,未曾淹没,遇有所感,可随时而发……更有些妇女们受公婆的虐待,妯娌和姑嫂间的诽谤,以及婚姻的不满意,她们满腹的冤屈,向谁去诉?她们既不会作什么离骚的词,断肠的诗,所以就“不平则鸣”,把自己的痛苦信口胡柴的歌唱出来了。刘经庵:《歌谣与妇女》,见《歌谣》第30号,1923年。
刘氏还自述他采歌的情况说,他所采辑的《河北歌谣第一集》有三百余首,短者两三句,长者千余言,多半是妇女所说的。这种情形似乎验证了孔子“诗可以怨”的古老诗歌理论。正因为下层人民苦难深重,怨情最多,所以民歌谣谚等世俗之诗多出自他们之口。又由于妇女除了受各种社会压迫之外还要受到男性的压迫,所以怨情较一般男性更重,形诸歌咏者自然占有很大的比例。这种从民俗学考察出发所得出的推论对于我们区分诗歌的二重起源提供了切实的依据,并且对于理解圣诗与俗诗两类不同作者群的性别构成比例,亦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的诗论家们在描述上古诗歌史的时候,也有人已注意到最古的诗集《诗经》中实际包含着两类有明显区别特征的不同作品。如明代胡应麟《诗薮》便指出:
《国风》、《雅》、《颂》,并列圣经。第风人所赋,多本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之词,故其遗响,后世独传。楚一变而为骚,汉再变而为选,唐三变而为律,体格日卑,其用于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则一也。《雅》、《颂》宏奥淳深,庄严典则,施诸明堂清庙,用既不伦,作自圣佐贤臣,体又迥别。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页。
胡氏的这种对中国诗歌源流的宏观把握虽未必完全准确(如认为《雅》诗在后代没有反响等),但他毕竟敏锐地抓住了由《诗经》所奠定的两类题材、主题、风格都迥然相异的诗作线索,并特别强调了俗诗——即《国风》——对于后代诗歌发展的主导和基础作用。近代以来的《诗经》研究可以说大致上都依照着同样一种侧重倾向而展开,即重视《国风》而相对忽略《颂》的部分。从崔东壁的《读风偶识》到闻一多的《风诗类钞》,可以大体上看出研究者们关注对象上的这种偏倾。建国以来又受苏联式庸俗社会学的局限,“人民性”突出的风诗被套说成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初典范,而《雅》诗,特别是《颂》诗,却成了几乎无人问津的“剥削阶级”糟粕。这可真是“圣”变为“俗”,“俗”变为“圣”的历史大喜剧。
当我们把作为文化事项的《诗经》放在人类学的跨文化背景中加以理性透视的时候,不难发现长期被人忽略的《颂》和《雅》竟成了探求“圣诗”发生真相的惟一可靠素材。因此,本书虽也涉及俗诗的发生背景问题,特别是原始性文化与《风》诗的渊源关系问题,但更多的篇幅却用来挖掘与“圣诗”有直接关系的远古宗教文化方面的问题,如中国汉语“诗”概念的宗教学意蕴、诗与寺人制度的深厚姻缘、《诗经》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关系、温柔敦厚诗教与中庸伦理观的共同根基——远古阉割文化、盲诗人诵诗制与周代瞽矇文化的昌盛及其对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等等。这些问题由于过去没有得到重视和研究,笔者的尝试就不乏一定的冒险性和不成熟性。但愿这种斗胆尝试能给沉闷千载的《诗经》研究多少带来一点新的视野和新的思路,有助于对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做进一步的认识。
侯作侯祝,
靡届靡究。
——《大雅·荡》
愿你口说的话,
变为你眼见的现实。
——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