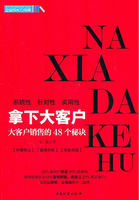中国远古时期的咒诗由于未能得到及时记载而绝大部分散佚无闻了。《诗经》产生的时代距离原始咒诗繁荣期已经相当遥远了,因为这个时期保留下来的作品都已经历了由咒向祝祷的转化或由咒到“骂”的变化,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法术思维符号了。尽管如此,这些变了形的咒诗毕竟多少保存了诗源于咒词或诗言咒的痕迹和功用,使我们可以参照域外的情形做出合理推测。
世界各古文明中保留咒诗最丰富、完整的印度文明为考察诗源于咒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材料。若仅从编定年代上看,《阿达婆吠陀》这部以咒诗为主的诗集在四部《吠陀》中编定得最晚,因为在它问世之前已流行“三重吠陀”(the threefold Veda)或“三重知识”(the threefold Knowledge)之说,拉格真(Zénnaide A。Ragozin):《吠陀印度》(Vedic India),伦敦费舍·安文出版公司,1895年,第117页。《阿达婆吠陀》是在后来(具体时间不详)才被编入圣典之中,成为第四吠陀的。不过,研究者们已经发现,第四吠陀虽然编入经典的时代最晚,但是其中的诗歌作品却绝不是晚出的,它们甚至比四吠陀中编定年代最早的《梨俱吠陀》中的颂神祷诗还要更早问世,因而反映着某些前吠陀宗教乃至前雅利安文化的内容。拉格真先生指出,《阿达婆吠陀》中的咒语(incantations)、符咒(spells)和驱邪词(exorcisms)是最早的诗歌。大自然中的每一种邪恶事物,从旱灾到发烧,以及人心中的恶德劣质,都被人格化并且成为咒术之对象。在这里,崇拜所采用的形式是行咒(conjuring)而不是祷告(prayer),因而主持者是巫师(sorcerer)而不是祭司(priest)。这些作品表现的是前雅利安宗教的内容,那是属于当地土著人的宗教,后被征服者雅利安人所吸收。这就可以解释如下悖论现象:为什么《阿达婆吠陀》最晚成为经典而其内容却又最为古老。拉格真:《吠陀印度》,第118—119页。
人类学家的其他观察也证明了祷词源自咒词的发生学关系。利普斯写道:“祈祷,特别是固定的公式化的祈祷,和古代巫术咒语的关系是显而易见。在西藏喇嘛教中,相信巫术性反复背诵的效果,由此引导出使用经常的祈祷磨,它为了虔诚教徒的利益而转动着‘唵嘛呢叭咪哄’的神圣咒语。这种祈祷咒语有趣之处在于这样的事实,即所用的言词和祈祷者个人心愿已没有直接的联系。祈祷者分明相信,咒语引起一度召来的神祇的注意,神就会自动地关心他的信徒的需要。所谓西藏的祈祷磨就是内有一片纸,上写神圣的言词,借助附加上去的曲柄转动,就能当成祈祷者不停地‘念经’,能毫不费力地重复千次以上。这种装置和原始人舞蹈中所用的拨浪棒停留在同样的水平,它们都是和古老的‘巫术歌唱’相结合。这种祈祷磨有的是庞然大物,在日本它是由一群‘祈祷者’才能转动的,有些大的祈祷磨竟由水力或风力来驶转。”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349—350页。这种巫术歌唱性的咒词与颂神祷词两相结合的混杂形式在古希伯来人列入《旧约》圣典的《诗篇》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实例。如《诗篇》第129首:
……
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愿恨恶锡安的,
都蒙羞退后。
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
未长成而枯干。
收割的不彀一把,
捆禾的也不满怀,
过路的也不说。
愿耶和华所赐的福,
归与你们。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
给你们祝福。《旧约·诗篇》第129首,《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南京,1982年,第715页。
这首诗中前两个“愿”表达的是咒术思想,而后一个“愿”则在于祝福了,可谓咒与祝同在之诗。更为突出地表现了由法术到一神教信仰的演变的一首诗是《诗篇》第83首,相传为亚萨所作,主旨是祷告耶和华,因敌对民族要绝灭犹太人,求上帝施法使之灭亡。这首诗的开篇是典型的祈祷词:
上帝阿,
求你不要静默!
上帝阿,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不作声。
因为你的仇敌喧嚷,
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诈,
要害你的百姓。
在历数了仇敌的罪恶用心之后,诗人又列举了这些敌人的名称:
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
和以实马利人,
摩押和夏甲人,
迦巴勒、亚扪、和亚玛力、非利士,
并推罗的居民。
亚述也与他们联合,
他们做罗得子孙的帮手。
列举之后便是类似施咒之词了,诗人呼告上帝说:
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
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
他们在隐多珥灭亡,
成了地上的粪土。
求你叫他们的首领,
像俄立和西伊伯,
叫他们的王子,
都像西巴和撒慕拿。
……
我的上帝阿,
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
像风前的碎秸。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烧着山岭,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
用暴雨恐吓他们。
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
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
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慌,
愿他们惭愧灭亡。 《旧约·诗篇》第83首,《新旧约全书》,南京,1982年,第687页。
把本诗的咒法同《阿达婆吠陀》中的正宗咒诗相比,我们看到的是以一神教信仰形式加以表现的咒术:对敌人的攻击不是 直接来自诗人的法术语言运用,而是通过耶和华神的中介。这种变更的原因,如弗雷泽等人所揭示,法术所信赖的是主体自身的力量投射,而宗教则把一切希望转托给了神灵。只有在法术信念衰微的情形下,超自然的神力才会取而代之。这时,直接的咒语也就向祈祷方向转化了。借用《巷伯》诗中的说法,只有当诉诸豺虎和有北的咒力不再灵验的时候,人们才会转而诉诸天神(有昊)之力,这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法术思维的自我中心性投射了,主体的愿望必须假借神的意志才能兑现。如上引诗所表现的,欲使敌人灭亡,不是用“胡不速死”的咒语发挥作用,而是用借刀杀人法去祈求上帝、激怒上帝。从“恨你的抬起头来”这样的说法中,似乎可体味出在神与敌手之间挑拨离间的意思。与纯粹自信的咒语相比,毕竟成了狐假虎威一类的东西。
在印度的《吠陀》和中国的《诗经》中倒是保留着一些不假借神威、不祷告上苍的较原始的咒歌,其功用不在于攻击敌人,而在保全自己,尤其是本氏族或家族的生息繁衍。如《阿达婆吠陀》第6卷第17首,这是一种保胎咒,表达顺产的意愿:
像大地孕育一切萌芽,
愿你的胎儿保住,
妊娠期满后生下!
像大地维持森林树木,
愿你的胎儿保住,
妊娠期满后生下!
像大地维持崇山峻岭,
愿你的胎儿保住,
妊娠期满后生下!
像大地维持万物众生,
愿你的胎儿保住,
妊娠期满后生下!用黄宝生译文,见季羡林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9页。
这首诗的咒力来自一个永恒的比喻:大地与母亲。这个与地母观念相通的比喻不仅给咒词赋予了充分的诗意,而且通过类比推理使孕妇获致地母般坚忍不拔的负载承受神力,从而达到保胎顺产的祝愿初衷。
《诗经》中虽无类似的保胎咒,却有祝愿多子多孙的咒歌——《周南·螽斯》:
螽斯羽,
诜诜兮。
宜尔子孙,
振振兮。
螽斯羽,
薨薨兮。
宜尔子孙,
绳绳兮。
螽斯羽,
揖揖兮。
宜尔子孙,
蛰蛰兮。
毛传:“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朱子《辨说》云:“螽斯聚处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为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之比。”其实,这首咒歌同印度人的保胎咒运用的是同一种比喻修辞法,以“聚处和一、卵育蕃多”即生殖力极强的虫类作比,祝愿家族人丁兴旺。并不存在什么妒忌不妒忌的道德寓意。由于印度咒歌用了“像”这一比喻词,使诗旨显豁,而《螽斯》则全用隐喻法,遂为后人的道德化曲解留下了余地。这两首咒歌充分体现了前宗教阶段的法术思维特征,用类比联想催生咒力,而不用祈告神灵之助或上天保佑。《螽斯》在语言形式上也相当古拙,其三言句式显然比《诗经》惯用的四言句式更为古老,成为认识“诗言咒”这一新命题的活标本之一。
把《螽斯》这样的咒词同《雅》、《颂》中大量的祈寿求福于神明的诗句放在一起,其间的差异和界限便不言而自明了。用人类学家的理论来验证这种差别,可以引用恩伯教授的如下一段话:“与超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分类。一个社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乞求、请求和说服超自然物(或力量)代表其利益而行动,或者与此相反,这个社会是否相信可以通过采取某种行动来强迫超自然为他们效劳,便是进行分类的一种量度标准。比如说,祈祷就是请求,而施展巫术就很可能是强迫。当人们认为其行为能够强迫超自然以某种特定的而且是预期的方式行动时,人类学家通常就把这种信念及其相关的行为称为巫术。”〔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5—496页。如本书导论中所述,任何一种巫术都源自史前人类的法术思维,从巫咒行为到祈祷行为的转化是法术思维自我中心性解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