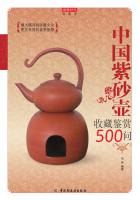魏晋名士谢灵运对曹植极为崇拜,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天下有才华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占一斗,天下人共分一斗。今天的人们看到这句话,难免会心一笑,对这位又狂妄又谦卑的大诗人,产生一种与才华无关的好感。
金庸的朋友兼崇拜者,武侠、科幻小说家倪匡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的作品尽管常令人看到有很多局限,但此人行事却往往透出几分痴气,引人发笑。倪匡曾自撰一联用以“自吹自擂”,却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吹嘘,而是吹嘘自己曾给两个人帮过忙。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屡替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
其实这两件事情,倪匡做得都很不怎么样。替金庸写《天龙八部》,写得一塌糊涂,把阿紫的眼睛写瞎了,幸亏金庸能妙手回春,改成更震撼的悲剧;乱七八糟的天山童姥一段却是无法挽回,至今还突兀地留在小说里。而张彻的电影,可说方方面面都很出众,就是剧本和对白常给人以浅薄做作之感,这也不能不说是有倪匡的“功劳”。
不过,我们看到这副对联,还是会觉得很有趣。倪匡对金庸的个人崇拜众所周知,简直到了奉为神明的程度,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个人站出来说,我来续写!他一定是睡觉太多,把头睡扁了。但这副对联中又不难看出,他对张彻的推崇也并不如何低于金庸。可知他眼中武侠小说的领袖是金庸,而武侠电影的领袖则是张彻。
张彻生于1923年,与金庸同年。后来张彻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虽然生于富贵之家,但童年并不如何幸福。少年时的张彻堪称才子,后来他拍《阿里山风云》,自己谱词作曲的一首《高山青》传唱至今,《金燕子》中萧鹏壁上题诗一段,其词及书法也均出自张彻之手。从张彻留下的文字作品中,也可看出其博学多才,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少年时的张彻还曾有过一段从政经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内任职,二十岁时即被张道藩欣赏,要推荐他进蒋介石的侍从室(蒋的参谋智囊团),但张彻因为不喜政治角斗而婉拒,后来也因此退出政界,拍过《阿里山风云》后,即到香港电影界发展。一开始因为客观条件拍片不成功,张彻遂从头做起,在报纸任职撰写影评,后终得到邹文怀的赏识,进入邵氏电影公司,主管编剧。
张彻在文章中曾经谈及东西方英雄观的差异,说,“譬如在终结自己的生命方面,西方英雄会用最少痛苦的方法,而东方英雄则多用最多痛苦的办法,剖腹,自焚……”张彻的电影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对他所说的这种英雄观的诠释。
张彻电影里的英雄,并没有打不死的,反而是一定要打死,而且,一定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死法,盘肠大战、五马分尸、死后屹立不倒……然而这样的死亡背后,又大多有一个意义存在。如张彻所说,有高尚的目的的牺牲,是为壮烈;肆意的杀戮,则为残暴。张彻的作品,对壮烈死亡的迷恋和渲染,也是其阳刚性格在银幕上的折射。
张彻和李翰祥在邵氏共事时有过一段有趣的故事。张彻刚刚加入邵氏时,在邹文怀手下做事。因为邹文怀和李翰祥不睦,张彻被李翰祥看作是邹文怀的人,也时常受到迁怒。一次即因为一个剧本的问题,受到李翰祥的打压。当时的李翰祥因为拍出一系列卖座片子,在邵氏权高势大,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但张彻的目标很高,就想如果不过李翰祥这一关,以后也会事事掣肘,于是干脆绕过邹文怀,找邵逸夫请辞,后终得认可,李翰祥也只能让步。
早在当年张彻在报纸任职时,李翰祥即已是名震香港的大导演,当时张彻写过一个香港导演系列的文章,曾有一语评价李翰祥,说李翰祥是一代霸才,然而亏在太有算计,“犹如一个锦袍银甲的霸王,腰间却露出半截算盘”。不知李翰祥是否因此事记恨张彻,但今日再看此语,却真是精彩高明的譬喻,可谓一针见血。李翰祥的很多经典作品,本来很好,却往往忽然流露出那么明显的媚俗的东西,这已为今日很多人所批评。而李翰祥也就是因为太聪明,太喜欢卖弄、迎合,没有张彻的力,所以也终究几沉几浮,成就和他的才华不成正比,最后掉进恶俗风月片的蛇阱里不能自拔。反观张彻就不同,他始终在战胜自我,挑战自我,尽管也有妥协,但却从未流俗,才会有一代宗师的成就。
张彻和李翰祥的故事还没有结束。1963年拍过大获成功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之后,李翰祥即退出邵氏,赴中国台湾重组国联,同时带走邵氏大批人才,令邵逸夫十分恼火。而张彻则在1967年拍出香港首部“百万”作品《独臂刀》,同时掀起新派武侠浪潮,亦成为邵氏新的中坚力量。而李翰祥则在台湾呼风唤雨数年之后陷入困境,1966年的《西施》一片虽拍得波澜壮阔,海外一片喝彩,无奈观众却不买账,赔得国联元气大伤。最终国联解散,李翰祥也于七十年代回到香港。
在拍摄了《骗术奇谭》等片之后,极度迷恋大场面的李翰祥又不禁怀念起邵氏那天下无双的大片场来。他有心重返邵氏,听说邵逸夫经常到半岛酒店喝早茶,就每天到那里去等。终于有一天碰到了邵逸夫。在诚恳道歉之后,便提出自己的意向。邵逸夫不置可否,说可以考虑,回去后便问张彻。张彻了解邵逸夫的性格,便说,若觉此人可用,大可不必计较前嫌。于是李翰祥得以重回邵氏。
后来李翰祥开拍《倾国倾城》,想借狄龙演光绪帝,姜大卫演小太监寇连材。因为狄姜二人是张彻发掘的,一直是其“御用演员”,邵逸夫为表示尊重,便问张彻的意见,张彻也表示可以借用。后来二人特别是姜大卫的表演相当成功,而李翰祥从此对张彻完全拜服。后来在一次酒会上,李翰祥主动向张彻敬酒,表示和好。
有这样的经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刺马》等片中,张彻把政治斗争,以及政治斗争对人性的改变拍得如此精彩。他确实对男性社会的特质有很深的理解。张彻在与李翰祥相处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气度,不仅令李翰祥对其由一开始的轻视,到后来的敌对、畏怯。一直到最后的拜服,甘拜下风,就是旁观者,也不免为张彻所折服。
香港才子蔡澜曾经回忆到,张彻的脾气很大,经常在片场骂人。蔡澜看不过,曾负气说:下次再看到张彻骂人,就和他打。又说:张彻从来不锻练身体,肯定打不过我。
这个回忆非常有趣,也可说张彻是作品如人。但张彻其人又是很温情的,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都可以令人感受到他的痴气,甚至是孩子气。张彻对弟子吴宇森的感情,对妻子的爱,都很温馨,很让人感动。
张彻和妻子结婚很晚,因为怕子女没有长成人就失去父母,于是不要孩子。张彻曾说,生平“最爱老婆,次爱拍片,三才爱钱”。曾看过张彻老夫老妻的照相,张彻一代大才,那样一个具有力量感的人,此时也都老态龙钟了,尤其令人欷歔。
张彻当年很喜欢吴宇森,拍片时在片场吃饭。经常会叫吴宇森过来一起吃,张彻身边的人就说,张彻喜欢谁,就会叫谁一起吃饭。
在张彻时代,要成为一个导演是非常困难的。当时的吴宇森尚且年轻,和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很迷茫,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当时吴宇森只想将来做一个摄影师,或者做一个导演,就已经很满足。当时姜大卫等都是吴宇森的朋友,都想帮吴宇森,有一次拍戏时给吴宇森试了妆,想让他当演员,但张彻看到就摆摆手,说,“吴宇森不要当演员,吴宇森适合当导演。”
就是这句话一直鼓舞着吴宇森,并令他获得最终的成功。后来吴宇森被人赏识,请他出去当导演,吴宇森为了这件事辗转反侧睡不着,最后决心要走,留了一封信给张彻,说自己现在已经成熟了,有人请他做导演,是个机会,想出去试一试,就不辞而别。张彻找不到吴宇森,急得要命,后来知道缘由才放心,也不怪他,还写了推荐信给那个公司。
后来张彻逝世,最后想见的人就是吴宇森,但吴宇森赶回香港时张彻已过世,只和王羽、楚原、蔡澜、黄霑、许冠文等一起为张彻扶灵。因张彻无子,姜大卫便作为张彻最喜欢的干儿子为其执幡。吴宇森曾说,一生对不起张彻的事,就是这样两件。
今天还可以在当时张彻的很多影片中的副导演一栏中看到吴宇森的名字。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后来的吴宇森电影中找到大量张彻电影的影子。张彻影响吴宇森的不止是技巧,更多是影片的灵魂。
《英雄本色》的悲壮感,主角失去一切,被人踏在脚下之后仍能振作起来,从头再来,可以看到张彻《独臂刀》的影子,只不过吴宇森的英雄最后仍然敌不过命运而死掉,悲剧感更强;《喋血双雄》中惺惺相惜的朋友情义,有《新独臂刀》和《报仇》的影子;《纵横四海》的角色设计和浪漫情怀,里面有《无名英雄》的影子;吴宇森的慢镜是张彻常用以表现死亡的慢镜的发展和完善,他招牌式的双枪对峙也是张彻电影里以剑对峙的另一种形式。
后来吴宇森在美国拍片,谈到自己在好莱坞的成功时也说,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张彻的话,以西方技巧传达中国文化精神。
但吴宇森和张彻又很不同,张彻很有力量,他的力量属于天生的,生来就是强者。而吴宇森本性里看得出是温柔的,他也有力量,却是后天的苦难催发和磨练出来的,本性里仍然是温和的。张彻少年得志,二十岁就被视为天才,人生基本上也一帆风顺。而吴宇森却不同,他小时候住在贫民区,整日见到的就是殴斗和流血,因为身体弱,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找件东西当武器,因为出门就要被流氓打。每天都是绝望,阴郁,看不到希望。直到有一天,他看了一部电影,《绿野仙踪》。在生活的一片灰暗之中,吴宇森看完了这部超现实的童话电影,忽然觉得,人生虽然痛苦,可是毕竟还有这么美好和纯真的事物存在。
所以后来吴宇森的电影,往往很黑暗,又很浪漫。他电影里的主人公们,在黑暗的时候仍然浪漫,这就是吴宇森的电影动人的原因。
所以吴宇森更浪漫,但有时也让人觉得缺少控制力,最好的作品都是最逆境的时候拍出来的。张彻是愈遇顺境愈能发挥能力,吴宇森则是愈遇挫折而愈能激发潜能。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和个性。
张彻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很深,作品中有很多意味都是从旧小说借来的,比如英雄死后的屹立不倒,相信即是三国故事中对典韦死后良久旁人不敢从其身边经过的描写中化出来的。张彻电影中的很多故事,也是从古代历史或者传说中取材,如《大刺客》是讲聂政之刺韩傀的事迹,《十三太保》是取材自唐末猛将李存孝的历史演义,《水浒传》和《荡寇志》是改编自《水浒》,《双侠》是取材自南宋武林人士救康王的民间传说,《刺马》是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张汶祥刺马新贻一案……而张彻在改编这些历史故事时,也毫不拘泥于原著,往往大刀阔斧地改编,以使之符合其作品的美学与精神。
张彻的作品,尤其强调精神,尤其是一再强调的“悲壮”,以及其所谓“高尚的牺牲精神”。悲壮和牺牲,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是陌生和苍白的词汇,但对于曾经历了抗日战争时代的张彻来说,则是现实和真切的。
张彻是第一个在武侠片中大量使用血袋的导演,作品的格杀场面相当惨烈和真实,往往尸横遍地,血喷如泉涌,以至有批评者戏称其为“蕃茄导演”,指影片流血太多,对社会风气和青少年心理有不良影响。但这在张彻眼中却有不同,他认为,他电影中的死亡,实为一种精神的体现。
张彻说:有高尚目的的牺牲是为壮烈,肆意的杀戮,则为残暴。壮烈和残暴,从画面感上是相同的,都是死很多人,流很多血,但本质上是相反的,分别就在于作者的情怀,他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是以流血为噱头,还是令人看到牺牲的价值。
张彻认为:暴力是人类骨血里与生俱来的元素,但落后的社会阻遏暴力,进步的社会疏导暴力,如体育、拳击、竞技格斗,都是对这种暴力意识的疏导。其实,张彻的武侠片尽管在当时看来过于真实,但骨子里也并不真的血腥,因为张彻所追求的其实更多是美学的意境,将暴力仪式化,而并不是真实的残酷感。张彻的电影也并非赞扬暴力的意义,反而经常是施用暴力者死于暴力。譬如《金燕子》里的萧鹏,就是以暴易暴,最后自己也死于暴力的典型。与之暗合的就像后来李小龙的角色在《精武门》里死掉,观众们很不满,他自己也是如此解释。说凡事必有因果,施暴力者死于暴力。
张彻的电影很多时候强调写意,如其常用的盘肠大战,所谓的腹破肠流,往往都是旁人口中说出的(如《十三太保》),主角只是在腰间缠一红布,代表盘肠大战,其实并不如何血腥,这手法也是从京戏《界牌关》中借来的。张彻本身对京剧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中也常可以看到京剧式的写意手法。张彻电影中的主角,在临死之前奋力杀敌,将死亡的意象不断加强,最终自己也力竭血尽而死的场面,被人称为“死亡之舞”,其实就很有京剧的味道。其中也可以看出张彻将死亡诗化。写意化的意念。
张彻的作品之所以充斥着死亡与鲜血,却绝不会给人以残暴之感,就是因为他始终在表现死亡背后的精神:牺牲的精神,战胜命运的精神。其代表作《独臂刀》,表现的即是一种失去一切后从头开始的力量。徐克也曾坦言被张彻所表现的这一精神感动,才翻拍了《刀》。就是王家卫《东邪西毒》里的洪七,其弃刀用掌的浪漫相信也是从《独臂刀》中得来的灵感。
张彻恐怕还是中国导演中最早令“浪漫”脱离了爱情的电影人之一。通过看张彻的电影,当时的很多中国人都明白了,浪漫并不只是玫瑰,它可以是友情,是搏杀,甚至可以是死亡,吴宇森常说张彻的片子好浪漫,但张彻是从来不谈男女之情的。
古龙曾经为他作品中的女性写过这样一番话,“……她们敢爱,也敢恨,敢去争取自己的幸福,但她们的本性,并没有失去女性的温柔和妩媚,她们仍然还是个女人。女人就应该是个女人。这一点看法我和张彻先生完全相同……”
当年郑佩佩因为《大醉侠》大红之后,张彻找她演《金燕子》。郑佩佩演着演着,发现尽管片名叫《金燕子》,演金燕子的自己却完全沦为配角,变成王羽和罗烈两位英雄恩怨情仇的一个衬托,于是非常的不满。后来郑佩佩老了,成了老婆婆,谈起此事,对张彻还是大有微词。
其实如果她了解张彻的话,就应该早就猜到是这样子了。张彻是不会把女人拍成英雄的。张彻的电影,很多是以兄弟情义作为主线,却没有一部是以爱情为中心。对感情描写比较重的,诸如《保镖》中李菁对姜大卫的倾慕,也仅限于倾慕,类似于欣赏和怜惜,表现的重点仍在男性身上。张彻的电影,有两个场景被人认为可以作为他的理念的代表;一个是《新独臂刀》中姜大卫和狄龙成了莫逆之交,两人大笑相扶而去,姜大卫的红颜知己在一旁嗔怒道:“你们都不理我了?”另一个是《报仇》结尾姜大卫临死前挣扎而出,在幻觉中和兄弟一起欢呼雀跃,却终于没有触到情人。有人说,就好像他死去后是回到了兄弟身边,而不是情人身边。
张彻电影的主角,大多是那些早死的英雄,牺牲于英年。张彻自己却颇高寿,在生命开始了近八十年之后,张彻也等来了他在电影里曾描绘过无数次的死亡。
一代武侠电影宗师,张彻逝于2002年,死前不久曾留诗一首:
落拓江湖一剑轻,
良相良医两无名。
南朝金紫成何事?
只合银幕梦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