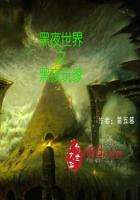大千世界,风云突变,周遭之大,怪事常见。生活在世上,我们是那么的渺小,我们只是一个小旅人。面对熟悉或陌生的人,熟悉或陌生的事,我们永远是主角……
——题记
算错帐的小贩
星期天做完作业,跟我老爸一道去比较远的菜市场买菜。
蔬菜很多,我们挑选也很仔细。
路边一位卖香酥油炸鸭的中年贩子和老爸打招呼说:大哥,只是买菜而已,又不是挑老婆,没必要挑选得这么沉重吧?
老爸尴尬地笑笑说:确实没什么好买的,你看你摊上那些油炸鸭子,不用油炸都被太阳烤得七成熟了,让人一点食欲都没有。
鸭贩子说:这倒也是,不过,我这里还有点“私人珍藏”,看在老主顾的面上,我让给你们吧。
我看看那只香喷喷的鸭子,鸭子也看看我,在我们目光相遇的那0.01秒,我决定买下它。
“老爸,买了吧?!”我开口了。
老爸勉强地点点头。
鸭贩子磨刀霍霍,正准备把香酥鸭开膛破肚的时候,突然抬起头算起账来。
我老爸说,砍好再算也不迟啊!
他没理我们,口里念念有词:1斤8元,三八二十八,一共28元。
老爸准备掏钱,但直觉告诉我有什么地方不妥,复述了一遍才发现问题:3乘以8等于多少?28?
老板很认真地回答:是啊,小老弟,三八二十八!你们父子没学过算术吗?
老爸乐了,被点着的香烟呛得不停地咳嗽。
我也骂笑不得,回头对旁边的菜贩子和鱼贩子:二位叔叔听见了吗?三八二十八!有这样算账的吗?
可那二位贩子和周围的几个买菜的人看看我们,都莫名其妙地报以一阵哄笑。
鸭贩子没笑,仍然一本正经地对我们父子俩说:一共28元,给钱吧!
我一把拖着老爸生气地掉头就走。
刚走了两条街,听见后面有人叫停下,回头一看,是那鸭贩子,他骑着摩托飞快地追来。
我没好气地问:叔叔,你终于算清楚了吗?
鸭贩子抹着汗水说:小老弟,你不知道,如果我不算三八二十八,你老爸的钱包肯定早就飞了。不信,让你老爸摸摸!
老爸一摸自己的挎包,不摸还好,一摸吓了一大跳,上面已开了一条大口子。
鸭贩子苦笑着说:刚才给你们砍香酥鸭时,发现有个贼在划你老爸的挎包,我想提醒你们,但又怕贼报复,只好故意来个三八二十八,好让你们和旁边的人们注意……
从鸭贩子中接过砍好了的香酥鸭,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还是鸭贩子先开了腔,吆喝般地对我们叫喊着:3斤鸡,三八二十八,不过我只收你24元,给钱吧!
老爸笑了,我也笑了。
吓坏了的西瓜
那天,老爸在书房里忙写稿件,老妈上班监管市场,“闲人”的我只好滥竽充数,自个去“金三角”市场买菜。
回家的路上,经过步行街口的水果摊,一个农民模样且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人正站在一大堆西瓜前吆喝,说他的西瓜个个都红透无籽,不熟不卖,不甜不卖。
他那双滴溜溜转动的眼珠一看见我在瞅着西瓜时,便一把拉住我,非要我拿一个回家去尝尝鲜不可。
我这“书生”耳根子浅,耐不住别人劝,再者,也有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西瓜了,眼见这些西瓜的长相和卖相的确不算错,便忍不住掏出钱包来了。
老实讲,关于如何挑一个好西瓜的文章我在书上、网上看了不少,但真正运用起这些书本和网络上的“技艺”却不灵活,既然如此,我便叫那个卖瓜的年轻人给我选一个。他二话没说,随手拿起一个皮色很青的瓜过秤。
我不放心,叫他另外找一个。
他却再三保证道:“都是同龄人嘛,你拿回去,不熟可以拿转来调换!”
银货两讫,我于是抱着那只瓜爬上了家里的二楼上。
老爸见我买了西瓜,很兴奋,口渴的他急着要吃。
我把西瓜洗干净,放在二楼天井周围用水泥做的宽栏杆上面晾干,想等老妈下班回家后一起吃。
可老爸吃瓜心切,从书房里出来,一双渴盼的眼光在瓜上不停扫动,继而那一双刚刚敲打键盘许久的手去抚摸那只可爱的西瓜,“哦呵!”老爸一不小心,碰了西瓜一下,那西瓜咕噜噜地打了个滚,就从宽宽的栏杆上摔了下去,“啪”的一声重重地摔到地上。我马上从栏杆边探头出去,竟然看到天井地面上的那些瓜瓤还是青白色的,只略略带着几缕淡淡的粉红。
我一惊,立马跑下楼去,捡起那几块西瓜,回头去找那个卖西瓜的小贩算账。
他等我说完,冷不了地问了我一句:“哥们儿,你把西瓜抱到几楼上去了?”
“二楼。”我不明白他的用意,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那小贩一下理直气壮,说:“这不就对了么!你哥子想想看,胆子再大的人从二楼掉下来,都会吓得面色发青口唇发白,你把西瓜吓坏了,它咋个不发白喃?”
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预付了车费
欧阳明叔叔是我的邻居。
他原本有工作,辞职后自己干起个体运输,开辆大客车往返在绵阳和家乡小镇之间。
每当我学校放月假到车站等车,他都邀请我坐他的车,而且不论如何都不肯收我的钱。
时间久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于是我老爸老妈每逢他休息时,就买些水果什么的去看看他,算是感谢。
一来二往,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忘年交朋友。
傍晚时分,车子驶出绵阳的车站,路边有个背着书包的小伙子在招手拦车。
欧阳叔叔见了,把车停下,车上的售票员阿芳姐姐问那个小伙子去哪里?
小伙子说了一个地址。
阿芳姐姐头也没有抬,便说:“20元钱。”
小伙子说:“对不起,姐姐,我钱包刚才被人偷了!我是学生啊,现在身上没有钱。但我有急事今天要赶回家……”
“见鬼!没有钱坐什么车?”阿芳姐姐白了他一眼,要关车门。
小伙子一脸恳求:“我到家再给你钱,行不?我家就在马路边。”
阿芳姐姐说:“不行。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还是假,年纪轻轻的,脸皮这么厚,想白坐车呀,没门儿!”
小伙子的脸腾地红了,不知该说什么好。
这时欧阳叔叔从驾驶座上回过头来,对阿芳姐姐说:“让他上来吧。”
小伙子喜出望外,连连对欧阳叔叔称谢。
上了车,欧阳叔叔问他:“你家门前有一座高压线塔,是不是?”
他说:“是呀。”
欧阳叔叔没有再说什么,带上他继续赶路。
大约是夜间11时多,车子停在一个山坡路边的小屋前,小伙子要下车,他还对阿芳姐姐说:“姐姐,你等等,我去拿钱给你。”
这时,欧阳叔叔又回过头来说:“不用了,你走吧!”
小伙子一脸惊诧:“不!我要给车钱的,坐车不给钱怎么行?”
欧阳叔叔平静地说:“不用你给了,你家里的人已经提前预付了车费。”
小伙子一脸的疑惑,阿芳姐姐和我也都是一头雾水。
“提前预付了车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车又行驶起来。
欧阳叔叔告诉我们:“以前我还在跑货物运输,有一天深夜我空车返回时,车开到半山坡就熄火了,水箱里的水烧干了,我到处找不到水,后来就敲开那间小屋的门,屋里出来一个老人,为我提来了一桶水。”我要给他钱时,老人说:“‘孩子,一桶水要什么钱呢?你走吧。路上要小心啊。’”
行走江湖的卖艺小女孩
一日傍晚时分,我所住的居民小区一家餐馆侧的停车场上,来了三个卖艺人:男的四十来岁,正在拨弄一架收录机,弄得一只破音箱“吱吱哇哇”乱叫;女的三十多岁,脸很黑;还有一个是女孩,十四五岁的样子,远远地坐在场边的草地上,头一直低着。
看样子他们是一家三口。
一根系红布的绳子,一块钉了几百只钉子的木板,还有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独轮车,这些道具表明他们是卖艺的。
停车场上竖起了两根对接起来的旧竹竿,竹竿下端绑在一张小方凳的腿上,小方凳上压一大块水泥砖。竹竿的上端横一截小木棍,它的两头挑一对电灯,电线是从附近的一家水果摊位上拉过来的。
天黑了,灯亮了,破音箱叫得更起劲。
观众渐渐多了起来,自然地围了一个圈。
适才变小把戏的那个黑脸女人从场边的草地里拎出一辆独轮车,装模作样地试骑了几下,忽然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引得围观的孩子们大笑。
黑脸女人连声说“不行,不行,让我女儿来骑吧。”
于是,女孩出场。也是黑脸,束一根马尾辫。一件白衬衫束在红色运动裤里,外罩灰色小背心。脚蹬一双白色软底练功鞋。那样子比她妈妈灵气多了。
女孩一上车就围着那张水泥砖压着的小方凳转起圈来。马尾辫跳跃着,两只手臂划动着,稚气的黑脸露出天真的微笑。转了几圈便停下来。
她的妈妈沙哑着嗓子用河南话喊,现在表演“水中捞月”,就是请大家把硬币扔在地上,让她女儿骑在车上把它捡起来。
不一会,就有一元的,一角的,往场内扔。
那女孩又上车了。脸上的表情不再是微笑。她的双眼盯住地上的硬币,转一圈,捡一枚;再转一圈,又捡一枚。车将到,先下腰,手臂只一扫,地上那枚硬币就不见了。
这身手有点像空中老鹰俯冲水面抓鱼,准确而迅速。
观众中有了稀疏的掌声。
女孩的妈妈蹲在场边,手托一只塑料盘子。女孩捡一枚硬币转到她妈妈身边,就把硬币扔进那只盘子,“当”的一声,清脆悦耳。
不断有人往场内抛钱,“当,当”声不绝于耳。
有人同时抛了三枚一元硬币。女孩眼睛一亮,转一圈,“当”一声,又转一圈,再“当”一声。捡第三枚时,她骑过了,没捡成;再转一圈,却抓早了,又没成,手指触在硬梆梆的水泥地上,女孩眉头一皱,额上就见了汗珠;转第三圈,她探腰过度,一下子摔下独轮车。
有观众说“不要捡了”,立即有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抢入场内,捡起那枚一元硬币放入盘子,很虔诚的样子。
女孩的妈妈似乎不领情,却把那枚一元硬币重新抛进场内。女孩又上车,转第四圈,还没捡成。额上的汗珠淌下来。她抬臂一抹,再骑独轮车转过来,终于捡起了那枚该死的硬币。
掌声立即响起来,比刚才稠了许多。
扔那三枚一元硬币的男子,又从上衣口袋摸出一张十元的纸币,小心地放在女孩易捡的地方。
我也拿出十元纸币,打算直接放入那只盛钱的盘子。可是,那样做是否对女孩不敬呢?我不愿让一个本该上学读书,却跟随父母以卖艺为生的未成年孩子的自尊受到伤害。我还是将十元纸币放在了她很容易捡到的地方,并且把纸币折成直角,让它一面贴地,另一面竖着。这样,捡起来或许容易些。
没等女孩骑车转过来捡我放的纸币,我就转身挤出围观的人群。
我不忍心看下去,我怕她为了捡我给的钱而再触疼了稚嫩的手指。
那手指哦,本该的握笔写字的啊……
二流子落选
09年二月放月假,老家的长辈来我家看望婆婆,他们闲聊之间顺便提起了王狗娃。
我跑进书房,打开日记本,王狗娃留在我字里行间的故事又映照在我的眼前——
那年,我老家王家堰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村委会主任,几个候选人先后上台亮相演讲。
末了,村里有名的二流子王狗娃窜上讲台说:“我也要竞选村委会主任。”
王狗娃平时好吃懒做,人前人后口碑不大好,都三十出头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草屋两间。
主持人一看王狗娃上台胡闹,气就不打一处来,但又不便发作,只好问王狗娃:“你为啥要竞选村委会主任?”
王狗娃双手叉腰,理直气壮说:“我也要为人民服务。”
主持人不跟他一般见识,故作一本正经问:“你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
王狗娃说:“为人民服务好哇,为人民服务没有票子可以大吃大喝,没有楼房可以住上楼房,没有轿车可以坐上轿车,我要是干了村委会主任,没有老婆一定可以娶上老婆。”
主持人被王狗娃耍了个脸红脖子粗,便狠声狠气地说:“你竞选村委会主任,原来是有私心呀,像你这种人还能当村委会主任?!”
王狗娃接过话茬说:“村委会主任算什么,村委会主任充其量只能为一个村人服务。不瞒你说,我还想当乡长哩,当上乡长,就能为一个乡的人民服务,要是能为一个县的人民服务,我再苦再累心也甜。”
主持人鄙夷地看了王狗娃一眼:“哼!人民是你服务的么?你把自己服务好就行了。”
王狗娃说:“怎么?难道只有你能为人民服务,老子就不能为人民服务?”
主持人此时有些气急败坏了,便大叫起来:“你,你,你胡搅蛮缠什么?”
王狗娃仍然嬉皮笑脸:“记住,主持大人,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你的专利。虽然我是农民,照样能为人民服务。”
大伙儿好像看了一场喜剧,有人笑,有人叫,有人故意逗混混,“王狗娃,我也要为人民服务。”
……
选举结果当然是那位得票最多的人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王狗娃仅得一票,末了说:“这回是真选呀,今后我保证不做二流子了,老子要干出个人样儿来,让大家看看,争取下次再来竞选。”
这事已经过去几年了,王狗娃虽然痛改前非,也娶了老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但他做村主任的美梦没有实现。
春节前,我与家人回老家祭奠爷爷,又遇见了王狗娃,他对我说:“叔这辈子当不了村官,现在都是大学生来挑担子了哦。你好好读书,将来实现叔的理想吧?!”
我听罢这话,望着一脸苦笑的他,只得毫无意义地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