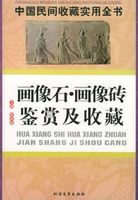一提起李四光,我顿时就要从他那光彩夺目的生命光谱中抽出四道光来!
第一道,救国之光。这位十六岁时由孙中山先生亲手接纳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始终牢记先生的嘱咐:“你要努力自学,蔚为国用。”先后到日本、英国去学习造船、采矿和地质,全是为了“把开采祖国宝藏的钥匙拿在自己手里。”
第二道,真理之光。“拿自己古代遗留下来的证据做老师,在这里找真理。”这是李四光的座右铭。他从东亚山脉构造型的实情出发,证明不能套用适用于美国西海岸边缘山脉生成的“大洋造山论”;还用他所开创的地质力学揭示了地壳构造各种形态的奥秘。
第三道,冰川之光。洋人说,中国在第四纪时没有发生过冰期;可是李四光早在1921年就在太行山麓发现了冰川的漂砾和冰川条痕石,之后又发现了冰川U字形谷。
第四道,石油之光。洋人还说,中国贫油——1914年美国人克拉普在陕北一连打了七口钻井,口口都是干井;而当时李四光却在欧洲宣称:新华夏系的沉降带中含有石油。他为“打井不见水,引水无水源”的河南密县找到了一千多眼井,被老百姓夸为“真正的风水先生”。
可是,你可知否?李四光还有“第五道光”呢!
日前,在去唱片室的路上巧遇专攻中国现代音乐史的陈聆群君。在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他突然用神秘的口吻在我耳畔咕哝了一声:“你知道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是谁写的吗?”“是不是马思聪?”我犹豫地猜测道。
“不!”他狡黠地笑了笑,“是李——四——光!”
然后,他得意地从公文包中小心地抽出一张五线谱手稿,那是首小提琴独奏曲,眉端工工整整地写着曲名:《行路难》(1920年作于巴黎),作者是“仲揆”——聆群君不等我发问就抢在我前面说,“仲揆”不是别人,就是李四光!
陈君卖完“关子”,就将他这次“勘探经历”徐徐道来——去年3月,他为编纂出版《萧友梅选集》一事,专程到北京去探望过萧淑娴女士。萧告诉他:李四光曾作过一曲,可在二叔(萧友梅)的遗物中找到。陈君回沪后,用考古的精神翻遍图书馆的资料,结果在一包学生的文稿中发现了此一遗物。这位“音乐勘探家”欣喜若狂,当即函告萧淑娴,在伊人首肯后,此事就成为1991年度的乐坛佳话了!
我捧着曲谱仔细端详。全曲有头有尾,层次清晰,中间还有转调呢选最可贵的是,乐曲立意深邃——行路难,行路难,地上地下都布满了看不见的“黑洞”。我不禁想起李四光在1942年为悼念他的学生和好友朱森所写的一首五言诗:“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森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行路难——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个“大概括”。但是,中国的第一首小提琴曲不是来自中国的“音乐之父”,而乃出于中国的“地质之父”之手这一史实,不也正是当时一代知识精英才华出类、修养拔萃的一个“大概括”吗?顺便提一句,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冰女士也还曾为沈心工的词“对镜自照”谱过一首重唱曲呢!而像李四光、许淑冰那样既放射着“科学之光”,又闪耀着“艺术之光”的“知识伉俪”——如梁思成与林徽因,钱学森与蒋英等,在“五四”后的中国知识界中是不乏其人的!我非九斤老太,也不希望一代不如一代,但却委实怀疑我们目前这种“单向偏才”式的理工科教育体制,能不能培养出李四光那样的具有立体型知识结构的大科学家?晚年的玻尔深为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分裂而忧心忡忡,认为这是“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裂痕”。并提醒人们要“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因为那是达·芬奇的时代,是人类自身统一、完善和成熟的时代……
说到玻尔,就会想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过:“我的科学成就,许多是受音乐的启发而得到的。”1912年8月的一个早晨,他独坐在钢琴前,阵阵琴声从他指尖涓涓流出——但那天弹的乐曲与往日不同,休止符特多。因为,他在边弹边思考……半小时后,他突然处于“顿悟”状态,丢下钢琴,一头扎进顶楼的工作室;一个星期后,满脸惨白的爱因斯坦重新回到钢琴室,颤巍巍地拿着几张稿纸对妻子说:“就是这个!”——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广义相对论”!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说,他发明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是受了他家乡巴伐利亚民歌“和谐曲”的影响;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则说:“音乐常常迫使我紧张地思考我正在研究的问题”,“失去音乐可就会失去幸福,甚至还会影响智力。”我在这里,绝非鼓吹音乐万能,而只是希望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光谱中,也能多闪出几道光束!五光十色才成画吆!
对了,得再“倒叙”一下李四光大名的来历——李四光本名李仲揆,1902年他十四岁时到武昌城去考“官学”时,一走神,竟在填写报名单时在“姓名”一栏中填上了年龄:“十四”。他情急智生,将“十”改成“李”,变成“李四”;然后一抬头,突然望见大厅正中挂了一块横匾,上书“光被四表”四个大字。啊!有了,有了!“‘四’字不动,下面再加上一个‘光’字——李四光!对呀!四面光明,光照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