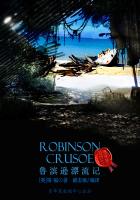小坛在床上躺了很长的时间,她很想自己一直躺在那里。到后来,她也清楚自己的身体都已经完全好了,她还是躺着。她开始注意着这个陌生的奇怪的男人。她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感到他是一个憔悴的中年男人,一个神情很忧郁的男人,一个漠然的男人,一个和她过去看到的男人都不同的男人。他长得很有男子气,脸上是一种温和平缓的神情,特别地进入了她的感觉。她很想抓住他,她感到自己遇到救星了,他看她的眼光让她感到他是看上了自己。她清楚这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有钱人,辨别有钱人和没钱人也是她的一种特长了。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那种有钱人。白小坛接受的观念中,很少有善恶和好坏的,只有有钱和无钱的区别,只有有权和无权的区别,只有有势和无势的区别,只有强硬与软弱的区别。她被他的眼光看得有点发毛,那眼光一直看到她很深的地方。她有点怕这眼光。但他的神情和举止使她对他产生了一种求救感。她想到他大概会留下自己了。她只想着要摆脱那个半老头,那个半老头让她有一崐种身处地狱的感觉。她甚至想到过死,她是过一天算一天,生病躺倒床上时,她就决定不想再跟着半老头。她有点装病,一半是病,一半是装,她也不知自己如何装下去。看到秦泰春,她想着愿意留下来为他做任何的事。留下了以后,她又有点担心着他眼光后面的东西会爆发出来。慢慢地,她注意到他很奇怪。她总是注意着身边的人,她被转手卖给了许多的人,她要见貌辨色以使自己不要被打骂,这养成了她注意人的习惯。她几乎不敢相信他会对她这么好,对她这么尽心,似乎不是他买下了她,而是她买下了他。似乎她越是躺在床上,他就越对她好,他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并且有些喜欢这样做着。她甚至想到他大概天生有想侍候人的僻好。她见过了许多的男人,那些人中,多有很奇怪的僻好的。她乐得让他这么做着。有一次,她实在熬不住,见他不在,就下床自己去拿了一些东西来吃。她其实很能吃的,以前的那些买了她的人,都为了她的能吃,而骂过她打过她。她既然是躺在床上的病人,自然不敢吃得太多。她不想一下子让他变了脸。她有点提心吊胆地去偷了肉饼子来吃。他这一次做的肉饼子实在太好吃了,她站在桌前狼吞虎咽地一下子吃了很多,几乎忘了秦泰春的存在。当她感觉到秦泰春走过窗子,就要进门来了,她赶忙地跳上床去,她注意到自己吃的碗边还沾着饼屑,她的鞋有一只斜翻在床的另一边。她躺在床上尽量装得自然地看着他进门来。她装得很好,她早已习惯了装。他似乎一点没有注意到她的神态和做法。他甚至没有看她。后来,他对着她的眼光一点也没有变化,还是那么静静地,带着一点体贴和关心。慢慢地白小坛不再怕自己起身的事了,她经常起身来找东西吃,她甚至感到他的东西都做得多了一点,留着让她在他不在的时候起身来吃的,只是不说明了。于是,这以后,经常是到他一离开她,她便起身来活动,做自己想做的,吃自己想吃的,一到他走近门时,再躺回到床上去,也不再躺得那么着急。
如果按白小坛原来接受过的观念来看,她躺着有吃有喝,有人侍候着,那就是享福。那么这个阶段,她是实实在在地享福了。她一下子享了福。对着这个使她享了福的男人,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她注意着他,她不知他的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有时她会想到许多不好的结局,她想了很多很多的叫她身心害怕的结局,也许把她卖到什么地方,卖到最使她痛苦的地方。那个半老头曾经流露出这种意思来过。只是到处传说社会要解放,要废除女人卖身的这一行了,所以妓院都不再卖买女人了。要不,也许她早就进了那里去了。有一段时间她对自己说,也许对着这半老头,妓院也并不可怕。那么现在还会有什么更使人痛苦的呢。也许卖过哪个痴呆的老男人,也许要把她带出国做什么试验,也许他会等她身体好了,再来享用她。他一定有着不一般的男人变态肆虐的毛病。男人的毛病是很多的。她把所有能想到的恶果都想到了。最后白小坛想着,对今后一切她都难以避免和抗拒,她只有在承受那结果前,让自己快快活活地享受一下。
到后来,白小坛自己也感到无法再这么装下去了。她要做一点什么,她还是会动心思的。她动足了心思,要做一点什么。在转手之中,她也总是动着心思,为自己求得一点什么。她心存害怕。他越对她好,她就越害怕。她总是想着最可怕的结果。盘算了好几天,她衡量了最可怕的结果,认为那结果不可能发生在这男人身上。她也就打定了主意,她用眼光迎着他时,带着那女性的媚态,带着那女性的娇笑,带着那一点说不清的女性的味儿,那味儿怎么动用,她也是在现实中被教会的。她用那眼光和笑意迎着他时,他却有点避开着她。他注意的眼光移开了,身子还有点颤动似地异样变化。白小坛有点弄不清了,她不知这个看上去并不显老的,神情特别的,和她所见过的那些男人都不同的,文文静静的,装着那么多书的男人,如何对她的眼光和神情会是这么个反应。她真摸不清他。越是摸不清,她心中就越存害怕。
白小坛动了心思,决定再试一试,再走一步。有一个晚上,他照例坐在了她的床边,看一会书,又朝她看一看,再静静地看一下书。她突然向他要一杯水喝。他端过水去的时候,她向他伸过手来,被子向下滑了半截,她便显露出她半个光着的身子来,胸脯是白白的一片。她只是伸着手,似乎脸上还带着一点羞涩的红。她伸过手去碰到他的手时,她就抓住了他的手。她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她的口中爽性就带着那一点轻轻的昵语声,嗲嗲的婉转的声音,嗯得弯柔的声音,女人特有的那种味儿。他似乎一时楞住了,只是看着她的脸,并没注意到她的下面身子和她的声音。她爽性向前一点,抬起身子来,她的身子除崐了腿都裸露出来了,她还把他的手向身前拉着,再一声嗯了一声。她的身子就快过床伏到他的身子上来了。
秦泰春突然手一挥,他的劲也许大了一点。白小坛的身子一晃,冲前要向床下倒去。秦泰春这才反应过来似地,伸手托住了他。白小坛一时有点恍惚,不知他会怎么样,她根本没想到他会这么对她。她有点害怕地颤抖地看着他,又带点娇情地哽咽。他轻轻地扶着了她,随后又轻轻地抱住了她。她伏到了他的身上哭了起来,她几乎是嚎啕地哭起来。她嘴里说着什么,说着什么一些听来的那种场合下常说的浪言浪词。她的身子也在他的怀里扭动起来。她想着她应该把这一切都做完,再等着那最后的结果。她这时想到他也许是个没有用的男人,只有着一种男女间的欲望。但她要看到这结果。秦泰春这时却按着了她,他的力气很大,他用嘴按着了她的嘴,他用他的身子按着了她的身子,似乎不想让她说,不想让她动,似乎又是对她的说和动的反应。她越发想说,越发想动,而他的劲也越来越大。最后,他呼应了她的动作,开始有点生疏,但后来他做得很好。他用他的手,用他的嘴,用他的身体每一个部位,都做得很好,虽然很稳重,很老式,但一切都很好。她再也没想到,他会做得这样熟练,这样好。使她生出迷惑和晕眩来,使她生出一种迫切想要的欲望,她的身子很激动地自愿地呼应着,从身子到内心都是热热的,她还没有这样感受过,因为过去的一切她都是被动的,带着被羞辱的。这以后的日子,他还是以往那样对着她,夜里他还是独眠,让她睡在那张大床上。第二天白天里,她有点害羞似地想起床,已经瞒不住了,她不能装病了。她也一曾想着为他做什么,但她敏感地发现他希望她还是那么躺着,他愿意做着一切,让她看着。她想他也许喜欢这么干着,这使她实在想不清那是为什么。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了。她想不清,也就不去想了。
那以后的日子里,白小坛的心放下来,她想着这就是她的归宿了。她不再顾及到他的神态,不再偷眼注意地看他了。他就是那么个人。他似乎对她着迷,是对她这个人着迷。他是被她迷住了。她也弄不清自己怎么使他迷上的。他就是迷一个病歪歪的女人,他大概就是愿意为一个女人做事。她自己大概是很漂亮的。有一次,她偷拿了他的一些钱,偷偷地去买了化妆品,悄悄地梳妆打扮起来。她内心感觉中是很喜欢化妆的。因为那是有钱人家的女人才能做到的。那天她故意在他的面前显着自己化了妆的脸,当他看到她的脸时,他的神情就象那天面对着媚情挑逗时一样避开脸去。她几次想问一下他,她化妆难道不好看吗。但她没有开口。她从他的神情反应中,知道他并不喜欢,她感到很扫兴。她对他还多少有点小心翼翼的,她便把那些化妆品收了起来。她不再做什么努力。她慢慢地也清楚了,他就想看着她本来的样子,看着她静静的不说话的样子,看着她默默地躺在床上的样子,看着她对着他眼光的样子。她觉得这一切对于她是很简单的,不过她慢慢地觉得实在没有意思透了。她还是认为这个男人有一点毛病,这一切都是他的病。她被他买了来,也就只有应着他的病,顺着他的病。
白小坛从床上起来了好些天,他还是让她歇着,不让她做什么事。他问着她要吃什么,他想着要为她做什么。那是一个冷天,她有一次鼓着嘴唇说她想吃鱼。他也就出了门,也不知他到哪儿去转了多大的一个圈,居然弄回来了一条鱼。看着那一条还在绳上晃动着尾巴的鱼,白小坛突然想笑,那是高兴的;突然想哭,那是激动的。她的神情肯定有一些变化,很想向他扑过去的。但秦泰春一看到她的神情,便移开脸去。她想到,他也许还是不高兴看她的这种神情,也许他忙了这么一大会,心里不快活。她就咬咬嘴唇,不再说话了。饭桌上,秦泰春看着白小坛把一条鱼都吃了下去。她吃得很开心。她尽量掩饰着自己高兴的吃相。但她太喜欢吃了。每一顿的吃饭,对她来说都是一种庆典。她以前常常是挨着饿的,慢慢地,她在秦泰春面前不再掩饰自己的吃相。她知道自己的吃相很难看,那个半老头曾经为此骂过她,也动手打过她。但秦泰春并没有讨厌的模样,似乎比看到她化妆和看到她浪情要好得多。慢慢地白小坛也清楚了,他只须自己很自然随便地。白小坛也就不再太顾及他的情绪和他的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