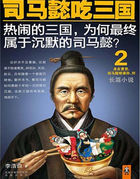考完试的小雪,又经常出进在我家院中,先在我母亲的房里坐一坐,便进里院去见秦泰春。天热时,两人在门外的院廊里摆着两张椅子,坐谈着。原先他们俩在一起时,常会听到小雪的笑声,这次以后,小雪的笑声似乎少了,常常是默默的没有什么声音。似乎秦泰春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对坐着。
往往是我从报馆里一回来,小雪很快就说她要走了。有时我硬拉着她再坐一会。我谈报馆里听到的一点社会报道和我对时局的看法。我没有改变对社会的关心。这些日子里,一直没有人来和我联络,仿佛一切联系都已经断了。也许我的行动,和秦泰春联在了一起,显得有点捉摸不透。我很想向秦泰春叙一下,话已到了嘴边却还是咽了下去,我得严守着秘密,虽然面对着的是我的挚友,虽然这秘密的根也许永远地断了线。因为我想到了黄花归姐,我想到了黄花归姐和秦泰春的关系,我想黄花归姐肯定是试过秦泰春的,他却没有进入这秘密中来,肯定黄花归姐是有她的看法的。只是断了线的我总想有一个人诉说一下。有时我怕独自面对秦泰春。秦泰春对政局的判断和对社会的判断,总是带着悲观的看法。他看了太多的政治的腐败。小雪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经常是静静地听着秦泰春说话。在小雪的身上反映出的是一种古典式女性的那种娴静和温柔,对政治的一面她是不关心的。在她的眼神中,只是看到对秦泰春的一种单纯的注视。
那段日子里,小城发生了一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户人家的男仆和那家人家的小姐偷偷地相好了,消息有点走漏,男仆被解雇了,小姐却跟着他出走,带着了她所有的首饰金银。主家脸面大丢,就以拐骗罪告到法院,于是这桩案件弄得整个县城都沸沸扬扬的。报馆对这件事是最积极的,连篇地采访了男仆和小姐,也采访了主家,听说小姐的父母都病倒了,由小姐的哥哥出面来说话,最初是告那男仆强奸后胁拐,自然城里对男仆是一片责骂。后来报馆采访到了崐小姐,她说到了自己对男仆的一片春心,说到了自己的一片孤独。于是公众舆论翻了过来,对小姐和男仆的爱情进行了同情。报纸上报道就热烈了。这一天登载了京城里的一位知名人士的文章,文章就这件事,谈了人权的意义和社会的发展。一个小县里的报纸能登到京都里的大人物的文章,这还是第一次,报纸印了近千份,报馆里的员工都外出卖报。我到午后两个小时后,卖完了报,不用再回报馆,就回家来。
走进铺门,热天里,铺里生意清淡,走进家里,到处都是静静的,母亲的房间里门关着,还都在休息。我也就放轻了脚步,走进后院里去,走到秦泰春住的房间,在窗口处就看到里面秦泰春和小雪的身影,两人贴得近近的,依偎在了一起,小雪面对着秦泰春,望着他,她伸出手来往上轻轻地抚动着秦泰春的头发,秦泰春还是带着他习惯的笑,任由她的带着爱意,又带点怜惜般的抚动。
一瞬间中,我不知如何是好,心里的感觉也凝住了似地。我站立着,想看又不想看,想弄出一点声响来,又怕屋里的小雪的窘态,也就悄悄地退出步子,走回到前院去。独自站在前院的枇杷树荫下,静一静有点乱的心。我所见的这一切,是我从秦泰春和小雪的最初相交时,就早已想到了的结果。我还是有点恍惚和不宁,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儿。小雪的影象总是在眼前浮着。多少回我感他们两个人在相爱又会感到他们之间有着相隔。特别是为小雪,我总是做着旁敲侧击的努力,现在这一切应该说是我的努力的结果,可我还是感到一种莫名的说不出的滋味。
小狗子从铺子里进来,他大概是想进里院去拿什么东西,我叫住了他。我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问着父亲,问着母亲,问着家里的事。他应着,有点神秘的样子,伸着手指着里面对我说:
“雪小姐来了一刻了。”
“是吗?”
我大声地说着话,和小狗子一起进后院去。刚过母亲的房间,见小雪从里面房间出来,她朝向我的眼光中含着那点朦胧和迷糊,红红着脸,但又显得镇静地走近我,叫了我一声。我却觉得有点窘,如是平时,我是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的。见小狗子走离开了一点,我不知怎么地想着一句话来,轻轻地在小雪耳边说。
“雪妹,怎么我一回来你就要走了呢?”
“我……来了有一刻了。”
我看到了还是飞红着脸的小雪,我看得出来,她努力想做出没什么的样子来,却还是难改她的窘态的红脸的习惯。
“雪妹不会这么坏吧,有了秦哥就忘了英哥了。”
我内心很不想开玩笑的,但不知怎么嘴里还是说着。看着小雪低了点头的窘态,心里又有点不舍,觉得玩笑过了。
小雪抬起头来,她的眼光中带着一点果敢,似乎一下子沉着起来。她朝我微微一笑。
“不管怎么说,英哥总是英哥,秦哥也总是秦哥。”
说着,她就出去了。她的话似乎是很自然的,却又象含着一点东西。我想小雪是单纯的,她的意思应该是很明白的,也是很简单的。也许是我把她的话想复杂了。
走往前铺的小雪的身影,很优美的女性的步态,象踩在我的心上。
又过了两日,我回家来时,在母亲的房间里,见着了小雪,母亲正和她谈着一件绣品。她们的面前放着了好几件织品和绣品,看来都是一一欣赏过来的,谈过来的。母亲似乎和小雪谈得高兴。
“好了,你们去玩玩吧。”
小雪在母亲面前显得往常那样,安安静静地,应着母亲的话。我默默地站立了一会,母亲象累了似地,对我说。
于是,我们进里院去。小雪默默地走在了我的身边。我想到了昨日我回家也见到小雪在母亲的房间里。我心里有了一点什么感觉。我想到了那日我见到的小雪和秦泰春两人的样子,敏感到了一点什么,也就想到小狗子带点神秘的样子。
秦泰春却还是习惯的样子,看到了我和小雪,放下手中的书,默默地微笑崐着。
很快,我找个借口出来,到我自己的房间里去,让他们两个在房间里,但是小雪很快也就走了。
那日晚上,父亲在饭桌上要了一点酒。母亲吃了饭离桌了。我和秦泰春也倒了酒,父亲难得喝酒,我们陪着他。我们三个喝着谈着,谈得顺畅时,父亲就问到了秦泰春的婚姻,也就说到了小雪。
“小雪是个好女孩,我是看着她长大的,文静温柔,也大方,知书达礼。我多少是把她当女儿的。泰春你和英儿是知已朋友,在我家这段日子,我也是看着了的,我把你也当做了自家的侄子。你和小雪有了接触,多少也是有了解的。现在婚姻讲一个自由,我这个做老辈的只是串一个线。你要是同意,小雪那边家里的话我去说。前两日,我见了小雪父亲,他谈到见过了你,印象不错的。那边也就小雪一个女孩,自然把女婿是当儿子待的。”
听着父亲的话,我心里感到高兴。看着秦泰春,想这一件好事总算落实下来了。我的预感总觉得他们的事会有波折的,母亲那两日的做法似乎是有意拦着小雪和秦泰春单独接触,使我隐隐不顺的预感变重了,但现在从父亲的口中谈来,似乎一切都不会有什么阻碍。他们两个已经相爱,秦泰春是单身一人,现在小雪这一边也有了这样的话。小雪这样美丽的女孩,又是秦泰春的救命恩人,在秦泰春的口中,也是很满意的。我是很清楚他们的感觉的,我想着这好事就要成了。
看来似乎我的预感有点莫名其妙。
没想秦泰春却是沉吟着,默默地饮着酒,没有应声。
“泰春你若已另有姻缘,不妨明告。”
父亲说着。我一直望着秦泰春,这时很怕他突然顺嘴编个什么话出来,便开口说。
“秦兄的情况我是明了的,他何曾有什么联姻之说。”
“那么或觉着意中有所不适,也可明告不妨。”
父亲的话还是那么彬彬有礼,熟悉父亲的我,却感到父亲的话音中带着了一点不快。明摆着这样的一个好姻缘,再加上也清楚了他们两人的关系。连我也不明白秦泰春如何一时没应声。
“我清楚秦兄对小雪还是深怀好感的,两人情爱已好,相亲相近……”
我替秦泰春说了一句。父亲移脸朝我,皱着了眉头。
“到底是你还是秦春他回话?”
我这时才想到,我几乎是要代秦泰春应下了这门亲事。我不知为什么急等着秦泰春开口,又似乎怕着他开口。我这样代话,便显得有点硬拉秦泰春应这门亲事了。好在秦泰春说话了。
“伯父好意,泰春深感。在这段期间,深受伯父高义相留,林兄是义友,自不及多说,而伯父伯母乃至一家的错爱,泰春一直感到深恩无以为报,我已把此地当做自家,一天天地沉迷下去,再加上小雪姑娘常来相伴。小雪姑娘冰清玉洁,娇美单纯,体察温和,是女中难得的好女子,泰春能得此姻缘,本应一口应允,求之不得的。若说有意下不适的,乃是泰春自感自身不祥,虽出身有微名之门,却自幼丧父去母,门庭冷落,身世多舛,且加上泰春乏才,不善理家,才使家业荒芜,又泰春天性淡泊,致使一事无成,命运飘泊不定,落拓无羁,常在杯中酒内沉沦,常与声色中落脚。有时自己思定,乃是一个末世败家之人,一个声色犬马之人,一个命不济行不定之人。就是对小雪当有一点心意,唯怕难配,也怕这一生难给她带来幸福,反让她多受苦难,便是泰春之罪了。”
秦泰春的一番说,父亲一时有点瞠目,不知说什么为好。他朝秦泰春看了一会,而后笑着。
“泰春你何出这一番自贬。你在我家多时,我们也常相谈,看你腹中经纶,不是无才之人,谈吐中多怀善念,不是强横之人,行动举止皆很沉稳,不是轻薄之人。这就是一个不错的人了,我览世也多,也难得见着你这样的年轻人了。至于家世的沉落,名家自是名家,这一点只是小雪侄女难配你,至于命运沉沦,我也知常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苦尽甘来,祸福相倚,以你之才,说不定哪天便有飞腾之时,正因为这种种之虑,我才开口相联,想讨一杯喜酒喝呢。”
秦泰春一番话时,我便觉着他的一种心情了,确实说的是一番实情。别人不清楚,我心里是很清楚的。听到父亲的一番话时,我又觉得父亲从没有过的深明大义。我觉得他们的话都很有理,我反而感到没有什么话再说了,只是默默地望着秦泰春。
秦泰春又往嘴里倒了一杯酒,我清楚他的酒量,平时从没有醉的时候,这次是他伤后第一次喝那么多的酒,眼见着他眼中也带着红意了。
“伯父,你容我再想想,我的心乱得很……”
父亲两掌轻合,摇了摇。说:
“终身大事自然应慎重。”
“不过,伯父,有一点我绝对不说假,泰春我要虑的绝不是自己,并不为自己考虑,而确确实实虑的是小雪。还望伯父明察。”
父亲望着秦泰春,点点头。我觉得心里松了一口气。然而我还是真真切切地觉着那预感。依然心里悬着一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