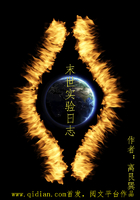我溜出了刀子家的院子,胳膊下夹着鞋子。主麻已经礼完了,男人们正迈出寺门,白花花的帽子像开在旱地里的花。头顶的阳光分外烈,满世界铺满了银子一样的光,眼睛也没法睁了。刀子老汉的拐棍声又响起来了,他扑通扑通跋涉在滚烫的浮土里,像走进了无边的泥坑,艰难地拔着步,毕竟是准备活二百岁的人,性子刚硬得惊人,不惧怕被尘土呛死,也不在乎什么肺气肿,再旱的年景也挡不住他活二百岁的劲头。我看着这个老汉一天比一天稳健,刚硬,明显一时半会儿出不了什么差错。这可急死人了,我等不及了,主要是满山洼的庄稼等不及了呀。我怎么才能再次溜进刀子老汉的家呢?
只能等下一个主麻日了。刀子老汉眼看就要回来,我急惶惶溜回了家。
到了下一个主麻日。我们的庄稼又熬煎了整整七天。是在骄阳的烤晒下一分一秒熬过来的。小刀送我的带蝴蝶的鞋子已经穿在脚上过了七天。鞋子穿在我脚上,不大不小,正好合脚。母亲听了我的叙述,像听见了天方夜谭一样,吃惊使得她的眼睛,久久大睁着。她真的没法相信,那个瘫子,会做这么好看细致的鞋子。女人们纷纷涌到我家,在亲自看过,并仔细捏一捏我的鞋子后,她们才相信小刀的事不是我母亲在开玩笑。这个小刀啊——她们感叹。
一夜间,我们庄里娃娃大人的脚上全穿上了小刀做的鞋子。娃娃们互相评比着他们的鞋子,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瘫子小刀做的鞋就是比自己母亲做的好看。男人们也这样认为。甚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自己婆娘,今后再不细心做鞋,就休了她,专门找小刀做鞋。一时间,女人们顾不得为持久的干旱发愁忧虑,纷纷做起了鞋子,仿照小刀做出的样子裁,剪,粘,糊,缝,绣花边,结麻花扣子。做鞋的间隙,有女人头靠住树干,幽幽地叹气,说你们说这个人咋做的,这么难的活计,女人也做不好,他会不会是个女人身子,惹得大伙笑。
穿了小刀鞋子的人,从自家拿出一木升子粮食,什么杂粮都行,只要是五谷,送到刀子老汉家去。小刀说了,他要靠自个儿的手养活刀子老汉。老汉养活了自己半辈子,现在土埋到脖子底下了,他得尽当后人的孝心。大家乐意穿小刀的鞋,愿意拿出粮食去换。这些年里,刀子老汉一直由大家帮衬过日子,在意识里,那爷儿两个早就不是外人了,倒是小刀,大家多年的养活没有白费,他原来是个有用的人。
小刀病了。以前小刀肯定病过无数次,但从没有这一次受人关注。这次得的是大病。大家挤进刀子老汉的家,纷纷去看小刀。小刀乱麻一样的头发被几个女人剃掉了。她们说这辈子没见过男人留这么长的头发,乱得像鸡窝。连同头发一起纷纷落下的有厚厚的污垢,污垢里满是乱跑的虱子。有女人拿破布擦拭生锈的轮椅,说等小刀好了要推着他四处走走,透透风,叫日头晒晒。小刀新剃的头皮还是很白亮的,像刚出锅的圆馒头。有女人拉着小刀硬给他换衣裳,衣裳下露出黑紫的烂肉。小刀的身子是烂的。双腿尤其烂得厉害,肯定是烂了几十年,口子都黑透了。娃娃们看见哇哇地吐,恶心得不行。小刀看见了挤在娃娃丛里的我,给我挤出一脸笑来。我发现这回他的笑不是嘻嘻嘻的,而是有些疲倦,有些力不从心的味道。
我等了八年,我知道你们会来的,他说。这回他没有对着我一个人说,而是对着满屋子的人说的。小刀还想说什么,又好像很疲惫,闭上眼睛喘气。
女人们为小刀换了干净的衣裳,还把炕上的破烂收拾了一下。扫了房顶的拖毛尘,给地下洒上水,彻底清扫了一回,扫出的尘土足足装了半背篼。收拾完大家要走了,小刀睁开眼说等自己好了,一个一个上门去给嫂子们磕头道谢。女人群里发出哗啦啦的大笑。大家七嘴八舌说你就快点好吧,我们可等着呢。最好这几天你连腿子也长好了,不然可怎么磕这个头呢。
女人们终究没有等到小刀上门磕头道谢。正午热得要命的时候,小刀突然断了气。刀子老汉跌跌撞撞跑出门叫人,消息把大家吓了一跳。几个女人不相信,跑进家里亲自看了,才相信刚才还和大家说笑的那个人真的不在了,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样也好,这么干旱的年景,活着确实是大家的累赘。可是,有个女人带点傻气地说他走哩咋不跟我们打个招呼,悄悄就走了,我还想向他学个鞋样子,看来没法学了。
天气又热又干,埋体一天也不能多留,大家商量了一下,当下就叫人去集市上扯来白孝布。下午,小刀的坟挖好,就把他送进了土里。小刀留下的鞋样子各式各样,大小齐全,女人们每人挑拣了一些拿走了。大家觉得小刀无常得真好,什么人没连累,大旱的年里,也不用人为他操心了。
送埋体的下午,我混在人群里。我知道这是我进入刀子老汉家门最后的机会。上回我爬过的流水洞口,刀子老汉回来就发现了痕迹,叫几个年轻人帮他搬了块大石头堵上了,并到处宣扬说有贼惦记上他家了。还说贼肯定是欺他家老弱病残,才大白天上门来。他可不是好惹的,这把老骨头还硬得很哩。大家当笑话传说老汉的话,我也跟着笑。但我明白,没有事由,再也不能进刀子的家了。
送小刀的人来了不少。大家都懒懒的,显得心不在焉,有气无力。趁大家心不在焉的时候,我溜进高房子,盖碗就在桌子下。没有人注意我,我把盖碗揣进怀里就出了门。大家的注意力在别处,不然是很容易发现我的诡计的。我微微弯腰的样子一定像个大肚子的女人,像那棵怀着穗子的麦子。
我上了山。山顶上,有一堆我早就拾来的瓦片,各色各样的瓦片,在日头炙热的光照下,热得烫手。为了这些瓦片,我最近总是魂不守舍,母亲骂我整天迷迷瞪瞪的,把魂丢了一样。其实我在找瓦片。我把能走到的地方全找了,白的黑的淡蓝的浅黄的,只要我们这里可能出现的瓦片,我几乎找全了。我甚至找来一个女人扔掉的尿盆上的一块带花的粗陶片。只要是带花带草带虫带鸟的瓦片,我全找。然而,经过艰苦的寻找,我才发现,我们庄子里的人活得有多么简朴,大家几乎全用一种白色的略显粗糙的碗吃饭,这种碗是货郎子拿到门前来叫卖的,大家用钱买,也用破纸片旧鞋子烂铁旧铜换,还可以拿女人的长头发换。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刀子老汉家有个白瓷盖碗。其实这不重要,盖碗大家还是买得起的,老汉们普遍喜好用盖碗喝茶。可是,我发现大家的盖碗上不是描一朵花,就是一竿竹子,还有的是一座山一道水,偏偏没有蝴蝶,没有展开翅膀飞翔的蝴蝶。我找来的瓦片上找不到希望中飞翔的蝴蝶。
刀子老汉居然收着一个有蝴蝶的盖碗。初次看见这个盖碗,我就惊呆了。这不是我苦苦寻找的东西吗?碗身上的那只蝴蝶,那张开翅膀,做着飞翔动作的淡青色的蝴蝶让我日思夜想。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所有能想到的法子,我几乎全考虑到了,就是没有办法叫刀子老汉把盖碗送给我。那个老汉一向以小气出名,就是大人去求,他也未必肯答应。况且他最讨厌娃娃了,见了我们,老远就挥着手,赶苍蝇一样,说嘘嘘嘘——嘘——嘘嘘。我们就得老早滚开,再纠缠他会抡起拐棍,毫不客气地砸到头上来。
恳求是没有用的。我决定偷。三要不如一偷嘛。终于让我得手了。不知道老汉事后发现了会气成什么样子。对着盖碗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空旷的山顶上,大风裹起我的笑声,消散到四面八方。没有人知道我做了贼,没有人知道我做贼是为了什么。
我把盖碗打碎了。粗瓦片砸下去,发出清脆的令人心神摇曳的碎裂声。只留下蝴蝶完整的身子。剧烈的阳光下,蝴蝶的神情显得疲惫,慵懒,好像它一直沉浸在一个悠长美丽的梦里,踟蹰留恋着,舍不得离开。它还在保持着飞翔的姿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其实是很累的。刚才的碎裂声也没能惊醒它。我抡起胳膊,右胳膊向前,左胳膊朝后,身子微微下蹲,攒力,使劲,呼的一声了,瓦片飞出去了,蝴蝶带着一股劲风飞向山下。我闭上眼,瓦片上的蝴蝶最终会落到哪儿,我不去追究,也不留恋。
大旱的正午,找一片蝴蝶瓦片,扔进山下的尘埃里,就一定有一场大雨落下。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我一直找不到蝴蝶瓦片,我很想问问别的瓦片行不行,可我想了很久,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说的话。我扔了很多花瓦片草瓦片虫瓦片鸟瓦片,雨都没有下来。老天保佑,终于让我找到了蝴蝶瓦片。
忽然觉得很困乏。干完了忙碌已久的事,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
——我等八年,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一定会来的。
——美丽的雨水。
远山弥漫在淡淡的尘烟里,好像画里画出的风景,居然有一些美的意思在里面。
山顶上刮过一阵风。不用抬头看,我知道是西北风。古老的忧伤的西北风。
原载《作品》2010年第5期
点评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古老的圣经名言,放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城市生活里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然而尽管形式转换,故事本身却没有多少变化:人性与人性,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纠缠挣扎的本质仍有着惊人的相似。
《蝴蝶瓦片》是一个农村的故事,是一群有着宗教信仰的人的故事,也许他们不如城市里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更懂宗教,但却比任何人更接近宗教的本质。信仰宗教的人并不觉得那是信仰,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听阿訇念经,无论是敲木梆子还是顺应时代潮流换成喇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主麻日要去听的。当你信仰一种信仰的时候,你是不需要解释的。
这个故事并不是直接讲述宗教,但笔触却始终如此。生活就是这样,庄稼人爱粮食,需要雨,主人公相信蝴蝶瓦片祈雨的魔力便寻找它,瘫子的鞋子就是那样的美丽,这一切代表着什么又意味着什么,对相信着的人并不重要,所以作者也并不解释。小说的字里行间有一种粗犷且亘古不变的力量——属于生活的力量。庄稼人忍受着煎熬,但并不称之为一种精神。他们不需要名词、形容词来定义,占有生活,他们拥有生活本身。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如果你忘了生活该有的模样,可以借助蝴蝶瓦片的力量去找寻。
(崔庆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