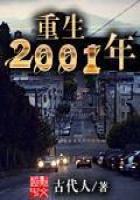“屁!”冯年说,“老子想坏都没时间学。要赌没钱,想嫖,就算有钱,我他娘的也没时间啊。一天站下来,口干舌燥,躺到床上我都忘了自己是个男人。半夜三更我还得对付那根银光闪闪的链子,我朝哪儿坏呀我?”
我说:“郑马猴又不知道你苦大仇深。”
“我想起来了,郑马猴年轻时整出了不少花花事。”行健把最后一张牌亮出来,是张黑A,又让他给逃了。“别看他长得寒碜,就是有本事走到哪睡到哪。听说还得过花柳病,天天晚上得坐澡盆子里用药洗上半小时。他是怕年哥跟他争澡盆子哈。”
“放你娘的屁!”冯年骂他,“老子三十年了,一套原装的男科!”
我们都笑起来。是啊,我们的冯年哥哥已经三十了。要在花街,早已经是打酱油的孩子的爹了。
冯年三十,所以冯伯伯和冯姨着急。谈婚论嫁,年龄从来都是大问题,都一把年纪了你还怎么拖?越拖越没市场了。关于市场,冯年肯定比我们懂。这也是他焦虑的原因之一。生活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辈子是清清楚楚地看得见的:我们在重复上一辈乃至上上、上上上一辈人的生活。前前后后的人基本上都这样过,都得这样过,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撞上奇迹的。冯年不可能永久地留在北京,他明白以他的才华、能力和运气,自己必定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一样,只是赶紧埋头吃两口青春饭,然后推饭碗走人。他还赖在北京,都是给年轻闹的,年轻似乎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骗骗自己也好。但是现在,婚姻大事临头,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三十岁也不算年轻了。但他不甘心。一看见他每天把自己弄得西装革履、人模狗样我就知道,他不想就这么放弃,虽然眼下也看不见转机和希望。
“除了老总和副总,”冯年在我们的屋顶上悲哀地说,“全公司我年龄最大。”他很纠结。
郑马猴的猴耍得好,花街上的孩子都喜欢看。我们经常跟着他走乡串户地跑,他耍到哪我们跟到哪。他能让猴子数数、分辨红豆和绿豆,甚至能让猴子围着一个女人转上三圈判断出她结没结过婚。他让猴子在不同季节穿不同的花衣服,那衣服妖娆冶艳,穿上后猴子显得十分淫荡。普通的骑车、倒立、敬礼、作揖更不在话下,据说他还曾训练猴子当众手淫,当时男人给他鼓掌,女人向他吐唾沫。耍猴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记起来了,郑马猴的猴戏结束后,也是把猴子随手往身后一甩,猴子就挂在了他的后背上。不同的是,他系在猴脖子上的是一根五颜六色的花布条搓成的套;此外,这还是他猴戏的一个重要环节。小猴子会在他后背上一个鲤鱼打挺翻上主人的肩膀,然后手搭凉棚,像齐天大圣那样向观众们敬礼。到此,猴戏才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冯年看的猴戏比我多,他比我们都大。但他一点都想不起在噩梦之前,起码来北京的六年里,他曾在什么时候回忆过郑马猴的猴戏。从来没有。
“那你最近看过猴子没有?”行健问。
“两年前去动物园,见过几只猴子。”
“这就对了!”行健说,从床底下的纸箱子里摸出一本书,《梦的解析》,一个叫弗洛伊德的洋人写的,已经被他翻烂了。他抖着那本书用教授的宏大口气说,“年哥,你压抑了。要不是那事儿上压抑了,就是那几只猴子勾引起你的某些说不清楚的回忆。”
“别张嘴闭嘴那点事儿,成不?那都是两年前的猴子!”
“这个弗什么德的说,吃奶时候的事都有影响,何况你才两年。年哥你绝对压抑了。那点事儿多重要啊。”
行健攥着那本书当然离不了那点事儿,他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当黄书看的。如果不是隔三差五能看到几句刺激的,谁有兴致看一个外国人唠唠叨叨地解梦。
这事最终也没弄明白,冯年照样做噩梦。为了避免噩梦,他想了很多招,比如熬夜,熬到走路都能睡着的时候再睡。没用,只要睡着了,连个过渡都没有,跺跺脚就变成西装革履的猴子。我说过没有,六耳猕猴也穿皮鞋?鞋面用金鸡牌鞋油擦得溜光水滑,苍蝇站上去都得跌跤。他还试过喝酒,醉得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是宝来,但是一躺下来,梦里的六耳猕猴还叫冯年。第二天一早找我跑步时说,他被链子勒得酒都吐不出来了,只好咕嘟咕嘟再往回咽,胃装不下,他被活活胀醒了。他还想过用别的梦把六耳猕猴挤走,夜就那么长,做了这个梦肯定就没时间做那个了。白天他就反复地想一桩稀奇古怪的事,希望夜里能换个内容;周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但要盯着一件事往死里想,时间和强度都得跟上,比上班还累,而且也只是偶尔才奏效,他觉得太划不来,苦成这样不如死了算。只能放弃了。
冯姨又在电话里催我了,她找不到冯年,干脆守在我家等我电话。上次冯年打了个电话回去,留的活话,“先处处看”。挂了电话就没跟人家联系过。冯姨在电话里说:“屁话,还处处看!一条街上长大的,谁头上有几根毛都一清二楚,处个屁处!你让那狗东西现在就给我回话!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我拿了鸡毛当令箭,又屁颠屁颠地跑到海龙,在他公司门口喊:
“冯年,现在,立马,赶紧,立即,务必!”
这一嗓子坏了事。当时冯年正在向一个客户推销佳能相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那家伙马上就要动心,我来了。等我传达完冯姨的指示,那人已经向另一个店员咨询了,然后冯年眼睁睁看他从同事的手里买走两部单反相机。下了班他直接奔我住处,劈头盖脸一顿骂:
“让你别去公司你非要去!到手的两部单反没了!”
我没理他。至于么,不就两部破相机,我还一肚子牢骚没地儿发呢。虽说我跑哪都是跑,可那中关村车那么多,空气质量多差啊,肺被污染了我找谁去?再说,冯姨跟黄鼠狼似的,见天就坐我家等电话,我妈都急了;她一来你就得陪着,除了纳鞋垫别的活儿都干不了,我们家就三口人用得了那么多鞋垫么?冯年的火气让宝来都看不下去了。以我对宝来的了解,凡是宝来说不好的,肯定有问题;凡是说宝来有问题的,那人一定有问题。
“年哥,我们都是为你好。”
冯年翻两个白眼,长叹一声,像气球被扎了个洞。“算了,跟你们也说不明白。”
把相亲弄得像受难,我们没能力明白。后来他在屋顶上跟我们玩捉黑A,输了喝酒,酒至半酣才结结巴巴道出实情。其一是,他真有点喜欢郑晓禾。他高她三届,念高三时没事就往初三教室门口跑,装作偶然路过,慌里慌张地朝郑晓禾脸上看几眼。现在想起来还脸红耳热,要不早打电话回绝了。其二是,他们公司要在朝阳区开分店,准备挑一名经验丰富、性格稳重、业绩突出的员工去做分店长,这两个月的销售业绩作为重点参照。冯年前两条都没问题,只要眼前能够立竿见影,就成了。偏偏这是多事之秋。据说那两部相机加配件,销售额近五万,一个月也难得抓一两条这样的大鱼。
“哦。”我说,“真是不好意思。”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冯年抱着酒瓶子像唱卡拉OK,“下个月就三十一了。来的时候我跟自己说,三十岁还没头绪就回家,妈的结婚、生孩子!来,兄弟们,干了!”
第二天早上他没跑步,睡过头了,洗漱完就往公司跑。夜里依然梦见被甩到耍猴人的后背上,银白的链子扣进了肉里,要把他血管和气管割断。
接下来他跑步时断时续,状态也不是很好。我能理解他的难过,夜里没睡好还得花体力去跑步,搁谁也受不了。我甚至还做过一个和他相同的梦,梦见自己也成了一只六耳猕猴,身上穿的是夹克、牛仔裤和运动鞋,被人吊在身后。我想我要憋死了,我想我的脸一定肿胀得像只大红南瓜。醒来后我为冯年哥流了两行眼泪。但我只梦见过一次,而冯年每周至少三次,一次比一次暴烈。
我们决定为冯年出点力,四个人家底子全端出来才凑到三千块钱。宝来说,有总比没有好。托行健的一个朋友去海龙,单找冯年,买什么都行,只要能把三千块钱花掉。那哥们儿去了,问哪位是冯年。一个同事说,冯年生病,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那哥们儿回到我们住处,很生气,逗我玩哪你们?让我屁颠屁颠地去放空枪!
行健说:“生病了你怎么不吭一声?”
“我哪知道他生病?”我说,“最近他又不是每天都跑。”
米箩瞪大眼,说:“会不会那啥了?”
“哪啥?”
米箩摆摆手:“没啥。瞎说着玩。”
我和宝来相互看看,站起来一起往外走。
隔两条巷子,推开院门,冯年的房门敞开着。这是傍晚,天从上面往下暗,房间里昏沉沉的,没开灯。我被烟味呛得咳嗽起来,冯年坐在破藤椅里抽烟,烟头像细小的鬼火在闪。我打开灯,看见他头发支棱着,眼窝深陷、胡子疯长,一看就是个资深失眠者。他只穿着贴身的秋衣秋裤,西装和领带扔在床上。床上一片狼藉,刚搬完家似的。
“我正打算找你们,”冯年说,用夹着香烟的手在房间里漫无边际地划拉一圈,“我今晚的火车回家,你们看看这屋里有什么用得着的,随便拿。”
“年哥,你这是哪一出?”我尽量让声音放松下来。
“没什么,就回去看看。”他说,“我坚持了两夜,一个梦都没做。夜里我就想事。我想清楚了,该找个好女人、生个孩子了。”他开始咳嗽,一连串的动静,眼泪都带出来了。他用床上的白衬衫擦眼。他把一个信封递给我,让我有空的时候去一趟海龙,把信交给他公司的经理,让同事转交也行。
我和宝来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来,从他的烟盒里抽出中南海烟点上。抽烟有害健康,它让我们继续咳嗽。宝来觉得灯光刺冯年的眼,把灯摁灭了。我们都不说话。
临走的时候冯年指了指衣橱,犹疑地说:“西装,你们谁想要?”
我们俩一起摇头。
第二天我去了海龙。副总在,他拆开信,刚看完,又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进来。副总说:“黎总,没必要找冯年谈了。他辞职了。”
“刚刚?”黎总拍拍后脑勺笑了,“他妈的这个小冯,真会挑时间,那换人。命苦不能怨政府啊。”
出门的时候遇上铁岭来的那个女店员,她说:“呀,这不是冯哥的小老乡嘛。你咋来了呢?冯哥呢?呀,那烤地瓜老好吃了。谢谢啊。”
我对她笑笑,问:“你做过穿西装的噩梦吗?”
“你说什么?”
我知道我问得很古怪,语法上也有毛病。她是一个每夜睡得香甜的人。
我说:“没什么。”
原载《花城》2013年第3期
点评
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续写城市底层小人物们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有同情,有怜悯,有审视,也有批判,表现出了坚实的现实主义底色和人文关怀意识。这个短篇也延续了这种创作倾向,续写城市繁华背后青年人生存与生活的尴尬处境和因理想折翼所引发的精神上的进退两难心境。
作为万千京漂者中的一员,冯年的遭遇颇具代表性。他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西装革履,外表光鲜,行色匆匆,但本质上,他不但遭受生存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也遭受心理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不但因为他曾经拥有的年轻人的理想、抱负,在漂泊几年之后,仍然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性,更是因为他长期的工作压力、无成就感和居无定所的无根感,让他深深地感到了城市的冷酷和人生的无奈。他终于打包回故乡了,听从父母的召唤,娶一房媳妇,也未尝不是另一种幸福生活的起点。但是,这种从起点来到终点,又从终点回到起点的人生模式,总让人感到无以言说的伤感和无奈。
六耳猕猴是一个富含多义的小说意象。《西游记》中的那个六耳猕猴,其生前的能力又何其了得,而最后也终于被如来佛祖制服。他是一个没有靠山的草根人物,被孙悟空一棒打死,也只能说,他命该如此!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死于悟空棒下的能有几个?活命者无非出身好,有众仙家的保护而已。这样看,冯年的来生前世似乎也与六耳猕猴的遭遇有某种相似性,他梦里时常出现的这种形象与其身份构成了隐喻关系。冯年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草根,除了个人玩命地奋斗之外,没有捷径可走。他梦中映现出的被困、被锁、被勒的境遇是对其生存压力和心灵困境的直接反映。他最后离开这个城市,也是命中注定的。
口语、俗语、流行语夹杂运用,人物仿佛在我们周围,故事仿佛就是昨天的事。文末“我”和那个女店员的对话也别有新意,“你做过穿西装的噩梦吗?”这不仅暗喻冯年,也指向当下众多的京漂者,只不过,这个结果有来得早的,有来得晚的,如是而已。
(张元珂)